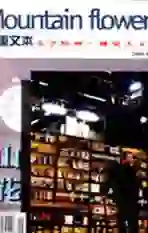穿梭
2004-04-29丁丽英
丁丽英
父母总是要我回家睡觉,哪怕第二天早晨脸不洗、牙不刷地离开也好,他们觉得这样能使家里人气旺一些,不至于两人大眼瞪小眼,影影对吊,自从我哥哥一家去了美国,老俩口越发觉得留在身边的我,这棵永远不见发芽的“独苗”,有必要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对他们表示孝敬。因为长到三十几岁,我还从未对家里有过贡献呢!
我的房间在新村的另一头,不算太远,十来分钟的路程,当初买下来也是考虑到经常可以上他们那里去揩油,白吃一顿晚饭什么的;如果他们有紧急需要,我拖鞋不换也能立马赶去帮忙。可惜没有买着同一号头的单元,那样的话,邻居就能经常看到一身睡衣睡裤的我,穿梭往返于楼梯和过道了,同时,母亲那催促吃饭或拿东西的大嗓音也必定随处可闻,那会使我非常难为情的。
现在,虽然少了这种麻烦,但我仍然感到不方便。我得穿戴整齐跑到家里去睡觉。途中要经过两所幼儿园,一所托儿所,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职校和一所养老院;还要经过四家便利超市,几家杂货铺,几家餐馆、发廊、干洗店、棋牌室等,以及一个菜场,三个垃圾屋,六个垃圾筒;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小公园,里面不光绿化搞得好,还安置了不少健身器材,来此锻炼的人成了最大的景观。两个小公园之间有条长而曲折的小路,小路的两头被带转门的铁栅栏封死,设了警察的岗位,自行车自然无法通过。也就是说,要想不绕道,整段距离就得靠步行来完成,且要受到警察目光的盘问。于是,那张床就显得相当遥远了,怎么说好呢?简直像被安置在一大片长满庄稼的农田中间,你根本找不到快速通达的捷径。每当困意上涌,我不得不靠毅力克制住,费力地睁眼,抬腿,直到进了家门,然后又是换鞋,脱衣服……
正式躺下时,往往又睡意全无。我感到既疲惫又难过,做起不愉快的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老人,很孤独,见谁就跟谁抱怨,靠眼泪逼迫子女看望自己;恳求他们留下,给他们吃好东西,给他们钱,诱惑他们住在家里。有时,我又意识到我不可能有孩子,于是,有关养老院的噩梦又会紧跟而上。那地方总是显得拥挤而龌龊,光线仿佛电影院,气味如同病房;我得忍受同屋人的咳嗽声,呻吟声,失禁的大小便的臭气,还有,眼看着有人死在眼皮底下,第二天早晨护土来换床单,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新来者照样入住。
这就是我的老年。我好像已看到了前景的可怕,醒过来总是一身冷汗。眼下,我也是这样被惊醒的,不过另有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似乎是为了加强戏剧效果。我闭着眼睛拿起了听筒。
“喂?”我的声音微弱到了极点。
“阿伟,怎么还不来睡觉?”
我听出是母亲,便感到奇怪,就说,我不是正在家里睡觉吗?
只听母亲笑起来说:“那么,你以为我们又是在哪里呢?”
她说我多半是昏了头,连呆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了,要不然,她猜我又像往常那样,睡着了:“那可是要着凉感冒的。快点过来睡觉吧!”
她为逮着我而庆幸。
我没有吱声,费劲地想了一会儿,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身首何处。这儿,我的房间里有只长沙发,却没有床,主要是我不敢买,怕的是父母知道了又要不高兴,会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然而就算是长沙发,就算我靠在上面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听音乐,花样换来换去,弄不好也是会睡着的。自从工厂倒闭后,我整日里无所事事,除了多睡以外,还能干什么呢?
我睁开眼睛,打哈欠,想法抠出鼻孔里的脏物。母亲却在电话那头舒了一口气,对无疑站在身旁的父亲说,这下可以放心了,他在,并没有出去。接着传来父亲佯装恼怒的声音,“快,那叫他快回来,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是啊!阿伟,听见了吗?我们等你都等得困死了,要睡着了,快点回来吧!”
没办法,我只得拖着晃晃悠悠的脚步回了家。
灰暗的客厅里,父母披着睡衣坐在电视机前等我。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得极低,几乎听不见,好像那是一台专门用来观察宝贝儿子的监视器。好像他们日复一日地孵坐在它的跟前,就是为了能够从荧光屏那淡蓝色的光线中辨认出儿子的身影;看他如何在阔大的新村里低头赶路,又如何巧妙地绕过灌木、草坪、和迷宫一样的小径;一路上他哈欠连天』、动作不断:一会儿踢小石子,一会儿又爬到健身器上去,把双腿像剪刀似地剪来剪去。那种健身器有着可笑的名字——太空漫步器,当你的两条腿交替晃开时,远远看去,就像一只机械玩偶在匣子内荡秋千。他们好像受到了蛊惑,以为这样紧紧盯住荧光屏,就能使儿子避免可怕的魔法,不至于突然从视线里消失。当然,他们窥看的时候从不交谈,身体的姿势也不变,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而房间里的家具用品也都跟着凝固起来,一次立体的大停格。直到儿子安全地出现在面前,这才猛火熔薄冰,忽地一下觉醒,动起来,同时尴尬地说:“哦,你总算回来了!”于是电视机也响了,灯也亮了,空气中的杂音也大起来了。
“阿伟,你让我们等得好苦!”母亲眼泪汪汪地迎上前,似乎要将手中的空气高高地捧到我的面孔上来。父亲晃了晃脑袋,耸了一下肩,装成不屑一顾的样子说:“热水器还没关呢,赶快洗脚,睡觉!”
直到我将两只脚都浸没在盆水之中(这下总算走不了了),他们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彼此交换一下眼神,心满意足地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去睡觉。
第二天早晨醒过来,我听见窗外繁忙的鸟鸣声,天空蓝得扎人。唉,我感觉自己又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应聘的工作没有一个有回音,表格却要不断地填,交上去。接下来总是这样——等消息,毫无希望可言。
我起床,穿好衣服,坐在床沿想心思:我又老了一天。这时,母亲敲开门,蹑手蹑脚地出现在房门口。
“嗨!狗得猫腻!”这是她去美国探亲学来的惟一一句英语。
“妈,早!”我懒懒地应道。
“瞧,春天多么舒服!”她的头发剪成齐耳的童花式,头发底边露出两小瓣可爱的耳垂子,上面缀着碧绿的饰物。穿的衣服以前也没见过,估计又是新做的。“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做梦没有?”她问。
“没有。昨天我睡得熟,什么也没捞着做。”我回答。
“怎么样?还是回家来睡得安稳?”母亲不由分说下了结论,一边卖弄地玩起脖子上的真丝围巾一角。虽然戴着真丝围巾,我注意到她的身上却穿着短袖衬衫。
“喏,这倒不一定。”我说着站起来,走到厕所里去小便,关上了门。这时,母亲站在厕所门外,嘴唇贴住玻璃移门向我大声说:
“为什么不搬回来?”
见我没有回答,拇亲又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阿伟,我和你爸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这个意思,你最好搬回来住,怎么样?”
我拧开水笼头,故意让水声大得盖过母亲的嗓音。母亲气馁地离开了,磨砂玻璃上留有一圈水蒸汽。我用毛巾擦了擦,擦不掉,是在反面,就不去管它。对有些事我也渐渐学会视而不见了。我继续刮我的胡子。剃须刀的嗡嗡声像苍蝇在我周围飞翔,我开始显得烦乱,急于想离开,躲起来。
父亲却在客厅里拦住了我,他说:“阿伟,我看你还是开酒吧吧,上次你堂姐的建议是可以考虑的。哦,一间能够打麻将的酒吧,听上去多好啊!既中西合璧,又老少皆宜。不光可以娱乐百姓,而且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他的装束也过于整齐,领带西装,缚带皮鞋,谈话因此变得越发正式了。
我漫不经心地说,不是我不考虑,而是我没法考虑。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梳好了头发。
“您没听堂姐说,最少要十五万?”我补充道,一边把梳子上的几根头发吹下来,“您知道,那可是一大笔数目呢,我是出不起的。”
“钱的问题,我看不大,总是可以解决的嘛!”母亲加入了进来。我发现她还化过妆,涂过口红的嘴巴说起话来显得格外有发言权。
父亲附和道:“你妈说得对,钱的事总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你想不想开酒吧。”
我说:“酒吧,我当然想开,可是关键还是要有钱。我根本没有钱。”这时我已经把脚伸进鞋子准备出发了。
母亲一步跨到门口,用身子拦住去路,说:“不,你有钱,我们知道你是有钱的。”
我说:“什么?老妈,您别逗了,要是有钱,难道我自己会不知道?”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父亲说,“好啦,钱暂且不去说它了,我倒要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开酒吧,还有,开酒吧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爸,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关键还是钱,而我没有钱,真的,不开玩笑,我每个月领失业救济金的,你们不是不知道。”
母亲说:“可我们知道,酒吧,只要你想开,还是能够开的。”
我说:“那太不可能了吧……莫非你们想来投资?”
父亲说:“No,No,我们不投资,可是我们有良策。”
我说:“什么良策?”
母亲诡秘地说:“那你就不要管了,只要你到时不反悔就行了。”
我说:“反悔什么?我可什么也没有答应过啊!”
父亲避重就轻地说:“是啊!只要你真的想开那间打麻将的酒吧,我们自有两全之计。现在,你可以走了,晚上再告诉你。”
“为什么现在不说?有什么可保密的?”我撇着嘴,终于将鼻孔内的脏物抠出来,用小手指指甲弹掉。
“不可以,不可以。”父亲的嘴里发出呜咽声,低头将脏物觅到,用餐巾纸粘起,扔到垃圾篓里去。他突然转变了话题:
“是啊!你知道吗?你身上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干净,因此很难想象你能独立生活,自成门户……”
我疑惑道:“难道因为这个,你们才不把实情告诉我?”
“别急,待你晚上回来,一定告诉你!”母亲说。这时她替我打开房门,将我轻轻地推了出去。
我只得向他们道别,下了楼,心想他们今早可真反常。反常的老人的春天!等我拐到楼房正面时,看见他们站在阳台上朝我挥手。母亲还摘下了真丝围巾,拿着它上下舞动,那副认真的模样,你还以为她在抖落床单上的皮屑呢。
“今晚回来睡觉,可别迟到啦!”母亲的声音特别响。
十五分钟后,我开始爬另一座楼梯。喏,是五楼。我想,应该画一幅漫画来总结自己眼下的生活:一个矮个儿面前树着好几把人字梯,每个梯子下面分别挂着几个牌子,上面写着“工作”、“钱”、“梦”,还画着一个姑娘。那画的意思想说,原本垂手可得的东西,在他,却总是要经过一番周折的。主要因为这个人一向脾气温和,缺乏主见,喜欢随波逐流。一句话,他完全是自作自受。
我有点嫌恶地打开了铁门,接着是房门锁。就在这时,有人胳肢了我一下,我吓得双腿发软,忍不住笑起来。转身一瞧,原来是隔壁家的老头,他正拄着一截木棍准备下楼去。
“您吓死我了!”我厌烦地说。这种突然袭击已经不止一次了。有一回他蒙我的眼睛,叫我猜他是谁;还有一回,他用一根肮脏的竹杆敲我的胫骨,说是要矫正我的罗圈腿。什么话?我很恼怒,但看在邻居的份上,他又是老人,就都忍住了。
“您再这样,我可是要生气了。”我说。
老头却涎着脸,嘻嘻乐道:“不会吧?我看见你正笑着呢!”
我跺了跺脚说:“那是被您吓出来的。瞧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不正经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真让人受不了。”
“这叫‘笑一笑,少一少,谁说年纪大的人不能开玩笑?”老头故意用木棍重重地戳着水门汀地面,使它发出“咚咚”的声响,接着,他攀着扶栏艰难地挪步下了楼梯。
他七十多岁,矮个儿,很丑,脸孔长得像烘山芋,一条腿还有残疾。当我刚搬到这儿时,他就向我介绍说,他是工伤,五八年,在造船厂,一大块打造甲板的
钢板压到了身上。“结果,你瞧,”他在楼道里拦住我,向我示范说,“我命大,死不了,可是这条腿再也弯不了了,活像一条桅杆。”瞎,真好笑!他用桅杆来形容他受伤的腿,好像那条腿比正常的要来得细长,我马上联想到黄色段子里的第三条腿,据说有些人的特别长,足以从裤脚管里拖出来。我略带苦涩地想,那可是一个男人所能拥有的全部幽默了。
我无言地踏进了房间,反锁上铁门。
“嗨!你每天来这儿干什么?睡觉吗?”老头问,他在楼梯拐弯处停下来,歇歇脚:“告诉你爷娘去,年纪轻轻的,整天没事干,闲着,晃着,不学好!”
我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没好气地说:“神经病!”
我悄悄地在沙发上躺下。我需要静静地思索问题。没工作做的这些天,我养成了大白天胡思乱想的坏毛病,一会儿想自己,一会儿想别人,兜了一圈,最后总是回到自己,因为我能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只要想像别人一辈子忙这忙那,挣钱吃饭,生儿育女,睡觉做梦会有什么结果,就能明白自己忙这忙那,挣钱吃饭,生儿育女,睡觉做梦会有什么结果。肯定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从这里走出去时,我会不会已经成了哲学家?
到了晚上,父亲对我说,世上没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向我详细比较不同地段、不同房型的不同房价。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看,我那套旧单元最多值十四万元,再扣除房产置换中心的中介费,各种手续费和税金以外,净到手最多十二万五千元。而且拿到房产置换中心去挂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有人来买。现在,隔壁人家有意搞基本建设,看中了我那套单元,主要原因是,他家孙女大起来了,原来的房子不够住,需要扩大住房面积。我那套房子又在贴隔壁,正好!大的仍然儿子一家住,小的买来老人自己住,彼此有个照顾。而且他出价十五万。你想啊,十五万呐,这下你开酒吧就有启动资金了!
“什么什么?等等,我可没听明白。”这时室内光线暗淡,我的脑子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点来点去点不亮,嗡嗡直响。实在是心乱如麻。
只听父亲又说了:“你还不明白?你的运气好,隔壁人家要高价买你的房……”
“原来你们给我出的就是这主意?让我把房子卖了,开酒吧?那我住什么地方?”
母亲说:“你完全可以住回家里来嘛!那是我们多年的愿望,你也用不着每天来回跑了。你想,光回来睡一觉,就走,这样也未免太不讲人情啦!”
父亲补充说:“而且,你每天回来睡觉,你那里的房子不是闲着,利用率不要太低噢?!”
母亲又附和道:“我看你隔壁那老伯也可怜,身体不好,有残疾,还天天受儿媳的气。如果把房子卖给他,也算积了德,做好事,成人之美……”
父亲接上去说:“是啊!再说,现在委屈一些没关系,等开了酒吧赚了钱,再去买房子也不迟……”
他俩越说越起劲,你一句我一句,围着我团团转,根本没我插嘴的机会。父亲仍然西装革履,母亲仍然是短袖加真丝围巾。瞧他们这架势,好像非要把我说得赤身裸体——完全缴械投降为止。我感到口舌干燥,呼吸不畅,试着想发声,不想话语却哑在了喉咙口。接着,睡意滚滚涌来,鼻孔也像被什么异物塞住了,我感觉没了退路。
“住嘴!”最后我不得不跳上椅子,恶声吼道,“不管怎样,房子我是不卖的!”
突然他们停了下来,好像我无意中按错了什么开关,把他俩都钉在了半空。只见他俩惊恐地看着我,空气变得像一根电线那么安静,又像一根电线那么危险。
我金鸡独立,尴尬地支撑着,直到四肢不住地哆嗦,可是没有人来理睬我。
不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动了起来。他叹了口气,剧烈地咳嗽,身子如同飞翔中的风筝;然后他又趔趄地跑到柜子那里,跪下来,拿出多年不抽的大前门牌香烟,胡乱往嘴巴里塞。而母亲碎步跟上,假装没看见我,不情愿地划着火柴,神情专注地帮他点火。
“你们怎么了?倒是说话呀!”我焦急地问。
父母踌躇着,抵抗着,他们的身影在烟雾中渐渐变大,变得朦胧,可疑,好像两座随时会移走的山峰。
“晚了,”父亲无力地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房子卖掉了!”。
“今天签的合同!”说完,母亲哭泣起来。
后来,我感觉自己在奔跑,道路在我脚底下飞速地后退。我跑过了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职校和养老院;我跑过便利超市,杂货铺,餐馆,发廊,干洗店和棋牌室;当然还有菜场,这会儿它打烊了,卖鱼的柜台上躺着无家可归的人;当我跑过垃圾屋时,原本—点没注意到那是一座漆成绿色的垃圾屋,是刺鼻的臭气提醒了我;而那两个小公园里空无一人,月光下,灌木形成古怪的影子,这些影子甚至比灌木本身更浓更密,不时会从里面蹦出一只乌鸦什么的,冲你凄惨地叫着,我吓得不敢停留半步。当我赶到我住的地方时,左邻右舍大都已熄了灯,可我不管这些,隔壁老头家的门,是被我硬敲开来的。
出来见我的是老头的儿子,大约四十出头。我以前见到他从不和他打招呼,因为我猜他多半瞧不起我。他在我这样的年纪早已成家立业,而我仍然光棍一条,现在又下了岗。没料到老头的儿子态度倒十分温和,声音也亲切可人,并不因为我打搅他们的睡眠而生气,而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我,这么晚了,找他父亲有什么事?我由于激动加上奔跑和爬楼,一时气急答不上话,他便好意地拍打我的背部帮我舒通,一边说:
“有事请慢慢说,不急,不急。”他老成的语气使我羞愧难当,后来他又说,过道里的灯坏了,不得不弄出很大的响声才能激亮它,还不如进屋说话,我更是死活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我站在漆黑的过道里,把他父亲买房的事向他简要地说了一遍,又鼓起勇气,开始向他全家表示歉意,因为我家又改主意了,房子不卖了,刚签的合同看来得取消。
“买什么房?什么合同?”他不解地问,一边用力跺脚,以便过道灯亮起来。在我看来,他跺脚好像意味着他很生气,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
“买我这间房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惊讶道。
老头的儿子疑惑地朝我摇了摇头:“你说买房的事,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我说这就奇怪了,明明今天我父母和你父亲签了买卖合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头的儿子叹了一口气,说,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他父亲患老年性痴呆症,经常会干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所谓买房大概也是他臆想出来的吧。
他的神情开始变得悲哀,缺乏自信。早知道如此,我遇见他时肯定会和他打招呼的。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他柔声说道:“我家从来没打算买房,也没有钱买房。如果他真的背着我和你父母签了什么合同,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要知道,我父亲得的是老年性痴呆症,完全没有自控能力。不过医生说了,他的症状还算比较轻的呐!严重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他问。
我只能回答没有。于是老头的儿子继续说:
“有些人会把大便当作钞票藏在饼干盒子里。十分地可怕!你父母怎么样呢?他们身体好不好?”
“很好。”我回答。
“我是说,有些老人虽然表面看上去很健康,其实已经得了痴呆症,别人不知道,我父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症!”
“你的意思是说,我父母也有问题?”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我只是说现在这种病很常见,不稀奇,说不定就挨到谁的头上……”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过道灯又灭了。这回轮到我跺脚了。我不断地跺脚,一下,两下,样子显得愚蠢。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因为我惦记着过道灯,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灭了,要不然眼前会是一片可怕的黑暗。但是灯还是灭了,任我怎样跺脚都不亮。
“诺,那就这样,再见吧,替我向你父母打声招呼!”老头的儿子回屋,关上了房门。
“好的,再见。”
我在黑暗中又站了一会儿。我想起我父母一直在打听隔壁家独居老太的情况,只要她一死,房子就可以出售了。但直到现在,老太太仍然活着。她很顽强,已经九十多岁了,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却惟独没有死的症状。看来,只要她霸占隔壁的房间一天,父母就得忍受寂寞一天,而我,得每天回去陪他们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