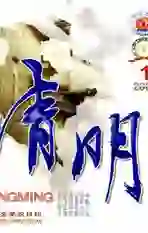现实存在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平台
2003-04-29黄佳能
黄佳能
尽管《清明》并没有刻意张扬一种浮泛的创作口号,但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引导创作的明确意识。在我看来,用“现实存在主义”来概括新时期《清明》小说大抵是恰当的。这个“口号”当然不是《清明》“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清明》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办刊思想和作为这种思想载体的作品中自然得出的结论。而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只是“现实存在主义”的合理延伸和深化。
需要明确的是我这里提出的“现实存在主义”并非是现实主义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拼合或叠加。“现实存在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它在表现现实的同时,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存在”的内在肌理,使其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现实和表现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局限;现实是“存在”的根基,“存在”也更多地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内涵,具有浓厚的东方意味;这种东方意味的社会语境是“市场经济冲击下正在转型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提出这个容易遭到非议的命名,主要还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一触摸时代的“阵痛”
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一直是《清明》的主打戏,不管其他文学期刊如何变化,但推出有分量的中篇小说参与文学精神建构一直是《清明》不变的追求。《清明》每年的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权威杂志转载率在全国同类期刊中也是不多见的,也因此扩大了她的影响。这些中篇小说尽管风格各异,但它们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平民性,这是《清明》中篇小说有别于同类期刊中篇小说的特点之一。2002年,《清明》共刊发中篇小说26篇。这些小说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但它们都掷地有声,从不同的角度锲入社会的敏感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社会转型导致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文学尤其是小说如何面对这个群体、关心这个群体、反映这个群体,成了新时期小说不可回避的一个迫切问题。可以说正是文学真正地关心弱势群体最有力地彰现了现实主义的品格。2002年的《清明》中篇小说首先关注的便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韩旭东的《流泪的冻土地》(第1期)以青年农民三、二涛、红莲等在东北这块冰天雪地琐碎的打工经历为叙事支点,整篇小说在浓浓的乡愁情结中,以清新朴实的叙述将这群打工者平凡、平庸的原生态生活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小说中的马师傅给他们在冻土地的生活增添了亮点,但这种有限的温情很难抚慰他们受伤的灵魂。那么,谁来抚慰他们的创伤呢?如果说三们在冻土地上的创伤是因为他们迁徙到一个与故乡近似的生存环境,那么急剧膨胀、灯红酒绿的城市能否兑现打工者的梦想呢?文星传在《半个月亮爬上来》(第2期)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小说中,要征服城市,扎根城市,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但她没有学历、没有专长,连打工的资格都被一些都市人的条条框框所剥夺。但她并非一无所有,她年轻、她漂亮,更为重要的是她有一双会“放电”的眼睛并借此征服了城市。作家并没有谴责她的“堕落”,而是以她寄居的大杂院为中心层层剥离了她尘封的内心世界。对生活她有美好的向往,但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她对城市充满恐惧;对爱情她有热烈的追求,然而爱情在功利的城市中显得太虚无——她与萨克手辉之间的爱情轨迹,像城市上空美丽的流星,只能徒增她对城市的恐惧。因为恐惧,所以挣扎。作为一个孤身闯荡城市的弱女子,她没有足够的资本与生活进行肉搏战,她的主动“堕落”中隐含着无尽的辛酸和难言的痛楚。不单她的爱情,就连她的青春也会在城市中香消玉殒。与马师傅一样,大杂院中的温情也同样因为缺乏物质的支撑遭到无隋的解构。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还有李志邦的《风月无涯》(第2期)、李肇正的《陆先生要恋爱》(第3期),它们对感上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的情感关注视角独特,令人深思;钱玉贵的《城市》(第1期)则把下岗工人王小保一家的赤贫生活与官僚、大款等的奢逸生活和腐化堕落等进行了“无声”的对比,近似于戏谑调侃的笔触倾诉的却是时代的阵痛和弱势群体生活的凝重,从中我们能真切地聆听到小说家沉重的叹息和真诚的忧思。
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触摸时代阵痛的另一个维度是反腐小说。反腐小说是近年来兴起的一股小说“冲击波”,这股冲击波的源头当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像《十面埋伏》、《国画》、《大法官》、《黑洞》、《绝对权力》等相对成功的反腐小说在读者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同时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粗糙也受到评论家的质疑,有人甚至把它们纳入了“新闻小说”的行列。2002年《清明》中篇反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有反腐小说的局限。
肖仁福的《官帽》(第3期)、孙志保的《干事的日子》(第6期)、叶向荣的《爆炸》(第6期)、郭牧华的《制造典型》(第5期)、李春平的《落红无数》(第5期)等小说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反腐”。《制造典型》与《官帽》具有相似的叙事风格和运思模式。前者叙述的是唐城市有名的“三玉”——宣传部副部长罗红玉、刘村镇党委书记张明玉和文化局副局长李子玉合谋制造刘村镇先进典型,并以此为政治资本分别得以升迁的故事。农民上访事件变成了“三玉”的政治阴谋;后者讲述的是楚南市计生委副主任方宏达和计划统计科科长杨青玉因官场失意,利用新任主任张思仁和组织部副部长吴早生联合造假为吴早生老婆谋得第二胎生育指标将后者拱下台的故事。虽然方宏达最终没有能如愿当上主任,但小说中青工宁建军上访同样被方宏达所利用。两篇小说一个是制造“正面典型”,一个是制造负面“典型”,小说中的“三玉”和方宏达都深知官场之道,但他们对官帽的追求却与众不同。“三玉”的“年轻有为”和方宏达的“老谋深算”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孙志保的《干事的日子》很容易使人想起新写实小说诸如许辉的《夏天的公事》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像何申、谈歌、关仁山和刘醒龙等以县乡镇官僚为叙述主体的小说。小说将大学生、镇组织干事四海置身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一心一意要实现他的组织委员的梦想,为此,他要千方百计讨好上级,但镇财政困窘,数月没有发工资,他无钱贿赂;他只好千方百计做好工作,并把这些工作成绩“划归”上级,并得到了上级的“空头支票”;他无法养活老婆孩子,家庭生活不和;他行贿的手段太次,结果弄巧成拙;他想在昔日情人面前取得情感的慰藉,最终被戏耍得体无完肤;他不满乡镇干部的弄虚作假,向媒体举报,最终在换届选举中,他不得不“高风亮节”,声明“退出”。四海最后从情人的楼梯上“像狼一样大叫了一声,滚了下来”意味深长——四海爬起来以后,会“成熟”起来的。四海的逃跑让《干事的日子》超越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新写实同类小说的局限,从《黑白道》、《温柔一刀》到《干事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出孙志保小说中的文化意味、生命哲学愈益成熟起
来。
表面看来,《落红无数》叙述了被现任瑶池市市长罗达钦开除公职和党籍的商人李梦泽向罗达钦复仇的故事——李梦泽回来投资、与罗达钦女儿谈情说爱乃至做爱都染上了复仇的色彩。这其中又穿插了打工妹刘小样与罗达钦、青年农民张山虎之间的爱恨情仇,这就使得小说极富故事张力。但在与罗达钦的斗争中,李梦泽超越了个人复仇的狭隘心理,他对罗达钦腐化奢侈生活的揭露和杀害张山虎暴行的愤慨已经成为正义对邪恶的审判。这种审判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反腐小说的粗鄙化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当下性意义。与《落红无数》相比,《爆炸》的情节并不曲折,但《爆炸》中的吕天范却是当代反腐小说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人物形象。吕天范是南渔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省劳模。他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愿住大房子,即使结婚也用自行车去接县城里最漂亮的新娘。他的一切全部与工作联系了起来,在外人眼里他是个百折不扣的真正劳模。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爬上县长的宝座,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老婆肚里的孩子、甚至写匿名信揭发南渔县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他这样做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因为这些因素成了他升迁的绊脚石。他的“廉洁”和反腐全部是给自己升官铺路。这样的人物形象与大量反腐小说中的腐败分子迥然不同,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叶向荣的另一篇小说《卸装》(第1期)中离任的金枝局长的烦恼,同样耐人寻味。陈应松的《晚年》(第4期)以一群退休的老干部视角来审视腐败这块毒瘤,并深刻地揭示了权欲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和扭曲。
二打磨思想的锋刃
仅仅触摸时代阵痛并不能体现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它把阵痛置于中国当代现代性话语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深层的透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是,中国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它的重要表征之一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必然从整体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并凸现出过去隐藏在“底层”的观念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强烈地冲击大一统的传统社会和文化格局。这个现代化过程既与西方文明进程有相似的一面,但因为中国特定的东方文化的浸染,又使这个现代化本身打上了中国人所固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裂变模式。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现代性建构中的两维一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程度远远要小于西方,因而在现代性的建构中,更多地体现为用审美现代性为物质现代性提供精神资源和价值支撑,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互补和互动的关系。这种良性的现代性建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减弱了现代化(物质现代性)过程中衍生出的矛盾对人的心灵的伤害程度。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具有独特的东方色彩的“现代意味”形式,从而使重铸人文有了坚实的基础。
关注弱势群体和反腐小说虽然展示的是转型期社会的“疼痛”和矛盾,但这些小说并非把人导向绝望。透过叙事的迷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家主体精神的高扬和清醒的批判意识。《晚年》中的老年人的反腐,落得妻离子散,并以失败告终。但“我将活下去,看那些人的下场”,昭示的却是饱经风霜的老人对时代的坚定信念。“我”和伙伴们虽然人微言轻,但“我”经历过无数的世事,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捕捉到历史的真相。《落红无数》中的刘小样能够揭发罗达钦,并拒绝李梦泽的恩惠使李梦泽的反腐有了坚实的基础。《半个月亮爬上来》中大杂院的温情令人感动。《制造典型》、《干事的日子》、《官帽》、《卸装》、《爆炸》等小说叙述了官僚们的腐化堕落和对权力的贪婪追求,但作者成功地避免了为发展经济而牺牲道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局限,而是把人性的丑恶和时代的发展与文化的渊源结合起来,探讨腐败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剥落了蒙在腐败毒瘤上的历史灰尘,在欲望化碎片图景的缝隙中植入意义,在对弱势群体真挚细微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对腐败等丑恶现象进行不动声色的批判中张扬了作家的主体精神,彰显了道德、正义、崇高等被后现代主义小说所解构的“宏大叙事”。而这种张扬本身又并非单纯回归传统的“巨型神话”。它们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思维,把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等人文内涵与对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欲望图景的审判融为一体;把欲望的碎片进行艺术的放大和夸张,在碎片与碎片之间巧妙地设置艺术空白,让这个空白去承受道德重建和重铸人文的艺术使命,从而介入当下,参与建构具有中国艺术思维、心理情感肌质等特色的现代性话语,以此唤醒后现代语境中的人们“对彼岸的记忆”。
当然,我们所提及的反腐和关注弱势群体并不能概括2002年《清明》丰富多彩的中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样是《清明》介入当下的一大支点。史生荣的《5号病》(第1期)和《学者》(第4期)虽然也如当前大多数新儒林小说一样展示了后现代语境中的高级知识分子追功逐利、庸懒无聊的生存图景。但小说塑造了两个脚踏实地、对科学和事业执着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世纪之交的文坛恰如一缕春风扑面,体现了作家的勇气和良知。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不少见,因此周剑松(《5号病》)、朱涛(《学者》)形象并非小说家的独创。但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深刻地把握了敏感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社会的尴尬,小说家把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干事业的周剑松和朱涛的“迂腐”与或不学无术、或追功逐利的学痞的“风光”进行对比,从而把笔触深入到了学术腐败和科学体制等影响中国学术和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但小说没有落人“问题小说”的“圈套”,而是通过知识分子敏感的心灵之镜折射出对这些问题的忧患意识,在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图景中建构现代性话语的坐标。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沉浮是现代文明程度的表征之一。因为现代化最强大的动力无疑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现代化的步伐。但科学技术在推动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过程中,也加速了人的制度化和物化过程,必然会冲击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道德准绳、理想追求等价值坐标,导致现代性话语的分裂,审美现代性便肩负起批判物质现代性的艺术使命。其实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爱恨交织”、相生相克,就像一对爱着的冤家,彼此不可分离,但同时也相互“埋怨”。从这个意义上说,《5号病》与《学者》显然是“问题小说”所不能比拟的。
能够代表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艺术境界和思想高度的还有舟扬帆的《我们同学宋元明》(第3期),小说以独特的方式对超稳定的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惰性进行了解构。邓芳的《快乐时段》(第6期)诉求的则是网络“悬空”了人的情感和道德问题;蒋法武的《颠倒》(第4期)让我们看到了“文革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朱飞燕的《找个理由嫁出去》一(第2期)叙述的
是母女之间的“姐妹情结”,直抵女性解放的深层问题;石钟山的《我们连队》展示了当代军人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与他的代表作《父亲进城》(《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样,从人性的视角进入了军人的内心世界……
三探掘“存在的矿藏”
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在介入当下、重铸人文的基础上,总体上表现出对人的精神“存在”的浓厚兴趣。它们所呈现的是在转型期社会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悬浮”状态,“柔性物质”是这些小说真正的韵味之所在。探掘“存在的矿藏”使现实主义获得了新质,这实际上也昭示了中国当代小说生存的新的可能性。
《我们同学宋元明》叙述的是宋元明从被同学冤枉“选”为小偷到蜕变为真正小偷的过程。小说在机智、质朴的叙述中揭示了民族心理超稳定结构中的负面效应对人性的扭曲。小说最精彩的当属同学“选”小偷的情节。同学们仅仅是因为宋元明的“脸红”便惊人一致的把“选票”投向了宋元明。作为投票者,这种方式只是为了他们自身从偷窃事件中抽身而出,事件本身在他们的记忆中将被时间抹去。但它却给宋元明年轻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以至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和情感世界。当班长胡若兰把情感的天平倾向他时,他因为自卑而心生恨意,使相爱的两颗心成为没有交叉点的平行线。同学们看似偶然的投票中折射出的是民族文化中的惰性超强的腐蚀力,即使教师也不可避免。同学们的“想当然”其实只是积淀在他们心里的文化惯性所催生的思维惯性使然。这种惯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怀疑、甚至斗争。宋元明在后来的偷窃行为发生在旧的价值观念正在解体的社会转型期,而他心灵的阴影却是他从少年时代带来的,物质的高度发展非但没有救赎他的灵魂,却使他迷失了方向。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中,宋元明除了要面对技术对人的灵魂的挤压,还要承受文化转嫁给他的历史重负,“腹背受敌”的宋元明只能任灵魂走上流浪之旅。
《流泪的冻土地》中的三、红莲躁动的灵魂并没有在冻土地找到归宿;墨生的《黄氏先生》(第4期)中的“我”更没有在大山深处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半个月亮爬上来》中的艳在喧嚣的城市中迷失了情感的方向;《城市》中的各色人群只是在城市的缝隙中透支生命和挥霍欲望;《官帽》、《落红无数》、《干事的日子》、《爆炸》、《制造典型》等小说把人性的脆弱和文化劣根性的“坚挺”进行了深层的透视;朱涛和周剑松等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灵魂在欲望的碎片中游弋;黄惟群的《寻》(第2期)中的“我”对精神乌托邦的寻找只是徒添空虚和烦恼。抽去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等角色标识,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幅中国当代芸芸众生灵魂流浪的图景;但这种流浪的意象又不同于卡夫卡、加缪等西方存在主义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精神的“荒园”。黑色是“荒园”的主色调,它诱惑流浪的灵魂走向悬崖的边缘,阉割了灵魂救赎的可能性;而上述小说中的流浪意象要更为复杂,一方面它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惰性与现代化思维冲突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中国人的生存意识裂变期的体现。农耕文化和庙堂意识根深蒂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翅膀下它们获得了寄生的枝头。市场经济斩断了“枝头”,它们便四散开来寻找新的栖息地,欲望的舞蹈乃是它们无法栖息的拙劣表演,这种瞬时性的表演注定是宿命的。农耕文化所衍生出的天人合一观是中国人固有的生命观,现代化过程所伴随着的物化、技术化和制度化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他们在物化的世界中感到无所适从,生命在冰冷的世界中显得渺小,固有的价值观和心理情感结构在瞬时性的“消费快餐”中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位置。渺小的生命在技术化的社会中左冲右突,碰壁受伤的是中国人的固有的生命意识和文化传统。但同时,农耕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人的坚韧品格和顽强的生命力舒缓了中国人在转型期社会中灵魂和情感流浪的痛苦,使人的现代化有了基础,成为可能。这种独具东方意味的存在主义心灵图画把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建构导入了一个较深层次——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人的灵魂寻找诗意的栖居地。
这种对唤醒“人们对彼岸的记忆”的书写方式既是作家对时代深切感受和忧患意识的文本化,也是《清明》重铸人文的办刊理念的生动体现。为了真正实践她的理念,《清明》和《安徽文学》在2002年推出了“文学与道德纵横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以此追寻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文学的意义和文学何为等焦点问题。在第4期的“编者按”中,《清明》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重建人文的执着追求——“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比起经济领域,在世界一体化的本世纪中,我们在文化和道德建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大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变动,给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惑,而作为观念的文学,也越来越倾向于对世俗欲望的展示,越来越丧失其社会批判的锋芒和道德理性。文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政治和社会关怀之上,文学是否还负有道德和人性关怀的责任和使命?……为重整情感秩序、营造文学的道德氛围,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彼岸的认识。”这似乎是对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的生动阐释。
不过,2002年《清明》中篇小说表现出的“现实存在主义”特征,并没有完全成熟。现实和存在在某些作品中还没有真正融为一体,有的作品还打上了观念痕迹。但毫无疑问,它反映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上一种新的发展倾向。现实存在主义不会像新时期流派和思潮游戏那样昙花一现,因为当代中国文化或文学思潮的更迭和嬗变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为物化的人们提供精神资源,这种资源需要积累,它不可能在“流派或思潮快餐”中得以完成。“现实存在主义”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商标”,也没有刻意“做广告”,但它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流派思潮“褪尽繁华”后所显露出的质朴秉性,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情景、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心理结构相互碰撞的产物。它能够在中西文化、历史和现实所交织的立体空间中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并在完善中添加新质,扩大其自身的包容性和诠释能力。这需要作家、媒体和读者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