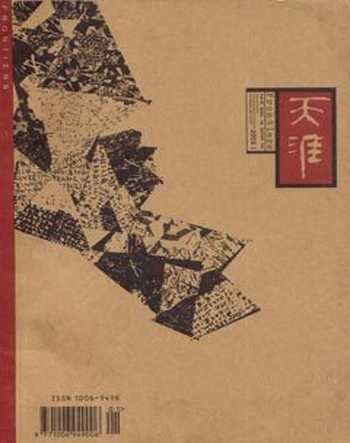文化研究的陷阱
2003-04-29薛毅
薛 毅
旷新年先生一向嘴辣。他的批判似乎总是无法用一种和缓的、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方式进行,而总是那样恶声恶气,尖厉刻薄,似乎非要把对象赶尽杀绝不可。我曾对他戏言说,他是被网上的许多人吊起来打的人。至少,很多人一说起旷新年,就会产生一个红头发绿眼睛的魔鬼形象。不过,也正如鲁迅所说的:“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这种“恶声”在中国文坛并不多,像旷新年这样单枪匹马横冲直撞地捣乱一下,也不至于引起名人所担心的“地震”吧。
不过,这回旷新年似乎有点过分了。他阅读一位大学生所写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吊带衫》,而戏仿此文,敷衍了一篇把文化研究“恶毒攻击”为吊带衫的文章。这不免让人误会他是向这个学生发难。杂文笔法擅长借题发挥,擅长击鼓骂曹,有时也难免伤及无辜。即便伟大如鲁迅的杂文,也颇有“不讲道理”之处,以至于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抓住不放,更何况旷新年辈。旷新年这篇文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阅读,第一个角度是结合《视界》第七辑的几篇大学生的论文一起考虑,第二个角度是从文化研究的一种趋向和陷阱来看。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从前者来看,旷文问题颇多,从后者来看,旷文的棒喝并非无益。
结合大学生论文来考虑问题,并不是要说明旷新年故意和大学生纠缠不清,而是要考虑当下的文化研究的具体状况。那些大学生的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倪文尖博士开设“文化研究”选修课程的成果。我为倪文尖课程的成功而高兴,这不是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而是由于倪文尖先生有效地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由此让青年们努力重新思考制约了他们的文化是一些什么东西,让他们能客观化地思考原先不假思索就认同和拥抱的大众文化。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一大积极因素就是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编码—解码”、“文化霸权”、“镜像”,诸如此类的词语在这个场合组合而成的思维方式,用来重新解读当代文化,其实也意味着重新解读“自我”,把自我从文化控制中解放出来。这是扎实而艰苦的工作。它所挑战的对象是当代被产业化了的所谓大众文化。据说文化产业在当代世界的利润仅次于航天工业。而依照德里克的说法,中国正进行着第二次“文化革命”,这第二次“文化革命”比第一次文化革命,规模更大,也更有效,它借助于电视、广告、报刊,借助于消费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强有力地铸造了年青人的心灵和生活方式。当代学界如今还在为第一次文化革命争论不休,而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所言甚少。文化研究理应对此发言。
但是,旷新年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文化研究的陷阱就在于,它所挑战的文化产业很可能把它收编进来,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特殊部门。旷新年戏言道:“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是‘妾身未分明。‘待晓堂前拜舅姑,画眉深浅入时无?”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需要与当下社会有更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据守在大学围墙内。这个位置应该是对大学体制化的反抗,借此重新建立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但很可能换来的是臣服于大学体制与市场社会的双重规范。在大学中它傲视其他学科,因为它是与当代社会不隔膜的,能获得年青人的欢迎;在社会上它对流行文化品头论足,又以来自大学“出身高贵”而自居。在这两方面施展身手,拓展一个新的空间,演出一场由挑战而招安的知识分子喜剧。文化研究的“小资化”倾向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前些年,詹明信的一本《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被小资们解读成后现代入门书。如今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几乎是小资化了的波希米亚人的必读书了。文化产业用出版、报纸的提供来收编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又对文化理论作无害化处理。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人一面大讲福柯,一面高声斥责鲁迅;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一面以本雅明为祖宗,一面非难马克思主义;我们会见到很多人一面批判大众文化,一面运用大众传媒炒作自己。就像女性主义在当代会堕落成为女性展露自己的隐私而获得男性的青睐一样,文化研究的堕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旷新年的判断:“文化研究是如此感性和性感,是一种如此感性和性感的研究方式,它抚摸当代花天酒地灯红酒绿莺莺燕燕莺歌燕舞的感性生活最柔软最敏感的部位。文化研究深入夜总会、招贴画、同性恋、俱乐部、酒吧、广告、时装、旅游以及眼花缭乱颠倒众生的消费文化和多姿多彩不断翻新的流行时尚。文化研究好像是一位风姿绰约、顾盼生情、千娇百媚、人见人爱的小家碧玉,风情万种,光鲜闪亮。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经意间,文化研究已经被收编为父权秩序中的一位姨太。”
为什么是文化研究,而不是其他东西会提供小资们撒娇和向上爬的场所?为什么文化研究会如此自如地把福柯之类的理论作无害化处理,能把“颠覆”演变成“游戏”,能把政治斗争转化为文化臣服?我以为,这和文化研究本身的缺陷不无关系。文化研究过分把自身限定在大众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上面了。它不自觉地把这两者与社会政治相隔离,仿佛它们是自足的一样。它也过分强调所谓“日常生活的微观反抗”,而丢弃社会政治的整体化视野。所以,在文化研究中会出现费斯克之流,似乎逛商场而不买商品,就是文化反抗。这种不是市侩的市侩主义倾向,与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世界看成世界的全部,把自己的苦恼匿名为人性的苦恼,把自己的局限看成是人类的宿命,把外在于自己的政治斗争看成是危险的领域,是相契合的。所以,在我看来,文化研究需要重新考察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像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样。而从雷蒙德·威廉斯、汤普森等这些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法兰克福学派诸如霍克海默尔、阿多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研究和批判与社会整体的巨大关联。这是一笔很好的遗产,如今的文化研究太倚重罗兰·巴特等的文本主义理论,这是令人不安的。在泛文本主义的潮流中,罗兰·巴特的理论由“再政治化”的努力,已经被修改成“去政治化”的言谈了。
薛毅,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无词的言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