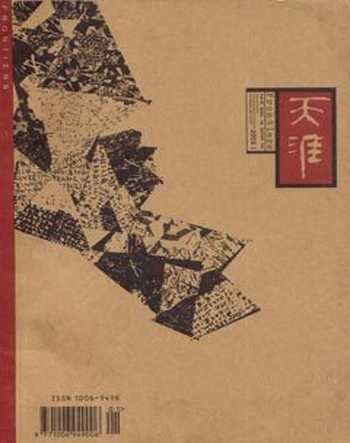树之祭
2003-04-29刘爱萍
两年前,我住在清华东路临街的一栋老楼里。窗外是一条幽静的小路,路两旁长满高大挺拔的白杨。这些树大概有十几年的寿命了,它们舒展着手臂和腰肢,笔直地冲向蓝天。无论春夏秋冬,清晨,总有一群不知名的鸟儿飞落枝头,啾啾喳喳地唱歌。风吹来的时候,树枝儿就应声起舞,树叶儿的沙沙声和着鸟儿欢快的啼啭,传递着日渐稀薄的乡村的气息。这和谐的自然的乐声把故乡般的宁静和祥和传进我的小窗,时常我会因了这窗前的林梢,想起我那“殉树”的老祖母。
我的家乡在秦岭的林海深处,村人对树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安徒生说: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死者的灵魂,故乡人却说:善良的人死了灵魂就住在树上,永不消散。山风吹来,林梢像海浪一样哗哗作响,村人们就会说:那是善良的灵魂在为我们祈福呢。童年的记忆中,老祖母常揉着腰腿对我说:奶奶怕是要上树了!那时我还年幼,不太懂老祖母的话。后来长大了一点,才知道故乡人把“去世”称为“上树”。
八十年代中期,故乡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些人,他们在开满野花的小河旁建起了国营林场。每天早晨,那些“公家人”就带上大锯上山了。他们是文明人,抽着“带把”的香烟,砍树的手上戴着白手套。他们常到我们这些山民家里置办些鸡蛋核桃之类的山货。有时候赶上饭时,纯朴的村人也留他们吃饭。每当这种时候,老祖母总是把拐杖顿得山响:这都是些烧山毁树的土匪啊!你们还给他们饭吃?!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的大锯,更何况一个去日无多的山野老妪。一辆辆的卡车开进山了,一车一车往外运着上好的木材。几个月里,我家门前那座昔日郁郁苍苍的山包就变得像个癞痢头,裸露着烂糟糟红褐色的伤疤。在那座山被“剃干净”之前,我的老祖母迫不及待地“上树”去了。也许是担心晚了,她就没树可上了。为了避免没树可上的悲剧,她有意无意地摔倒在家门口的石板台阶上。大概为自己终于抢到一棵树,感到心满意足吧,她的遗容祥和而宁静。她善良的灵魂依附着大树就永远不灭了。
十多年后,清华东路老楼里,无数个风清月明的夜晚,我关了灯,敞开窗,听风儿穿过树叶的美妙乐声,仿佛看见栖居在树上的老祖母慈祥的微笑。树叶沙沙响起,我就闭上眼睛,灵魂通过风与窗外参天古树上的老祖母会合,我用秦岭山民的方式怀念亡灵。能够在这座老楼里夜夜安眠,是因为窗外小路两旁那些茂盛的大树,这些树连着故乡的林海。
但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却让我悠长的乡愁无处寄托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像个披着隐身衣的巫士,隐身衣的袍角掠过的地方,很多东西会在一瞬间消失得无从找寻。那是一个清晨,我被一阵凄绝的鸟叫声惊醒。窗外天色微亮,却已是人声鼎沸。推窗望去,一群头戴安全帽的人正大声吆喝着从卡车上往下搬笨重的金属工具。天大亮的时候,马达轰隆隆响起来,吵得我心烦意乱,尖利的电锯声仿佛要把耳鼓膜刺破。那些高大挺拔的白杨树轰然仆倒,我把手放在胸口,发现自己已没有心跳。我关闭窗户,捂紧耳朵。没有了树,故乡一下子远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根的豆芽。
下午,他们结束了对树的杀戮。回家的时候,那条曾经幽静的小街,突然陌生得让我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地上躺满老树的残肢断臂,那些曾经寄托过我乡愁的大树没有了,大树被砍掉胳膊的地方裸着暗褐色的疤,往外渗着粘稠的汁液,老树疼吗?我的牙齿打颤,手指发抖。倒下的老树在哭泣,那疤痕里渗出的分明是它最后的眼泪啊。我回过头,我宁愿绕远路回家,也绝不走那条残败的近路。
树失去了生命,鸟儿失去了家园,在树倒下的刹那,依附在树上的灵魂们魂飞魄散。我再也听不到自然的乐声,没有了树的传递,我再也感觉不到栖居在树上的老祖母的半点气息。我再也找不到她。
依着没有树的窗户,我欲哭无泪,我的怀念和那些树一起被齐根锯断。窗外光秃秃的小路,如同故乡那座如今已变成一堆巨大沙石的山,没有一丝生机。
不久,我就搬家了。
刘爱萍,现居北京。身份、著作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