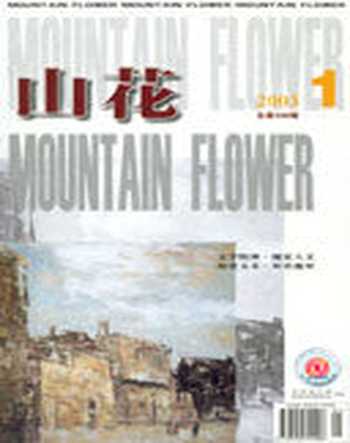找条回去的路
2003-04-29贺奕
贺 奕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似乎已经全无可能再重回我和李冯作为大学同学,由无数次熬夜、精神迷失和感情用事堆砌起来的氛围里了。印象中,他从化学系转到中文系,是在二年的下半学期。那时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服,看人的眼神冷漠中带一份嘲讽,再加上时常背吉他在楼道里进进出出,以致我暗暗认定,这不过只是个想摆脱掉理工科的学习重压,来文科中混口安逸饭吃的家伙。即便后来了解到他有一个被视为神童的过去,即便某天听他亲口说到,他已经在日记本上开始尝试起零散的写作,我还是对他是否在为自己的优游度日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深表怀疑。
“你写的什么?日记吗?”
“不,我想学习写作……将来当一名作家。”
他的理想,或者说我们共同的理想,其实并不新鲜,反倒更像是从当时已经渐近尾声的八十年代继承下来的一件遗物。我们和其他几位也打算投身写作的同学一道,以近乎秘密结社的方式组织起一个更热衷于空谈和争执的文学小组。我们甚至搬进一间寝室,共同起居作息,每到月末忍饥挨饿,于放纵沉沦中思考道德救赎,并把一本本页角翻卷的书传来传去。与我们的逃课、考试舞弊及其他一系列的恶作剧同出一辙,我们通过不太正当的途径得到了当时南大文学社的一期出刊权。李冯就此写出了他第一个真正成型的作品,我记得题目叫《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登在文学社这期印制粗糙、油墨不匀的特刊的头条上。虽然难免有欠纯熟,但许多方面已经显露出日后李冯小说的典型气质。
那以后大学毕业,我们各散一方。李冯留在南大上研,之后回老家广西谋到一份教职。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从前设想中那条坎坷多舛的文学之路,竟然在他脚下变得出奇地平顺。作为对敷衍了事地应付他所学的古典文学专业的弥补,他专心致志地把写作的重心放到对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解构之上,写出了《孔子》、《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以及《十六世纪的卖油郎》等作品。随着这些作品被各大文学期刊接纳,他也很快被引为所谓新生代作家的代表者之一。至此,似乎可以为他下一个定论了:是的,他并没有拿自己像梦呓般说过的那些话不当回事情。
然而,李冯不满足于让自己个人事业的篇章以这种既定的方式续写下去。一九九六年的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准备辞去工作,到北京当一个职业作家。当我还在为电话里那个久违的声音备感困惑时,他本人已经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现在我面前了。如果说几年未见,他身上有些方面已经起了一望而知的变化,那他眼光中闪烁的神采,还是把我又一次带回到他背地里在日记本上写写划划,同时对别人信誓旦旦的从前。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当真拿出了一个“文学青年般”的干劲。在北京劲松租来的一套四壁空空的单元房里,他摆上一张从二手货市场买来的色泽灰暗的电脑桌,期待着寂寞、冥想、窗外的喧嚣和每天自做的三顿饭菜能为写作注入新的灵感。一些周末,我斜穿大半个北京去探望他,发现他为图简便,饭桌上的主菜总在两三样原料之间来回变换,不是出自菜市场绞肉机里的肉末,便是切得形状不一、厚薄各异的香肠。另外,他端上的米饭也颇不同凡响,我吃完以后,脉搏曾狂跳至每分钟一百二十下。后来一看米袋,方知该种大米原产东北某监狱,显然是其中饱含的孤苦与仇恨在我肠胃中爆发出来。自然,看到当时的李冯吃完以后毫无异状,反倒精神焕发,我对他与这种大米如此投缘并不感到惊奇。有时候翻开桌上的杂志,看到目录上有他作品的标题,正待找到去读,却被他制止:“这个就别看了,下次等我写出好的……我要重新开始……”这话的语气怎么那么熟悉。
一晃又是好几年过去。时间,连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朋友,再次为李冯抉择的结果做出了见证。他在北京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因为出任电影《英雄》的编剧,获得了比他单纯作为一个作家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也就是说,今后无论他在纯文学领域里再做多大的努力,也很难见得就会比他目前获得的更多。如果他从此放任自流,那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加阻止。作为朋友,可以寄希望于他的只是,他最初那份理想的成色,并不会因为些微世俗的成功而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那批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们整体上陷入颓势、才华萎谢、斗志消弥、不思进取、开始变得庸庸碌碌的今天,我在李冯身上看到的那种对文学绝对价值的笃信不疑,那种持之以恒的创作热忱,便显得弥足珍贵。
对他而言,写作不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只是要一次次地回到当初那种为精神找寻出路的苦闷与迷惘之中,一次次地重新开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