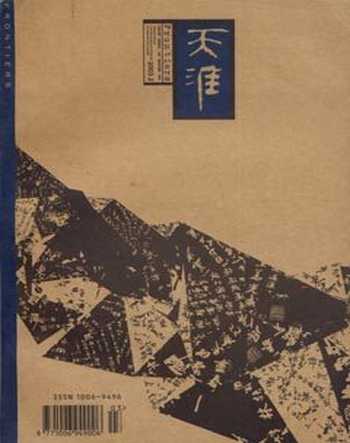全球化:文化的解放
2003-04-29巴尔加斯·略萨秋风
巴尔加斯·略萨 秋 风
[西班牙]巴尔加斯·略萨著
秋风译
对全球化的最有攻击力的批判一般并不在经济问题上,而是跟社会、伦理特别是文化相关。这些观点在1999年西雅图的骚乱中凸显出来,而在达沃斯、曼谷和布拉格不断回响,这些抗议者说:
国家边界的消失及由市场联结为一体的世界之出现,对地区和民族文化及传统、习俗、神话等等决定每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东西是致命的打击。由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抵挡不住发达国家——更具体地说,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的文化产品的入侵,而发达地区则不可避免地受控于大型跨国公司,因而,北美文化最终将强加于世界,成为整个世界的标准,而消灭多样文化之似锦繁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不仅仅是那些弱小国家的人——都将丧失其文化身份和灵魂,从而形成二十一世纪的殖民地——新的帝国主义文化规范所塑造的还魂尸或拙劣模仿(zombies or caricatures),挟其统治整个星球的资本、军事实力和科学知识,将把其语言及其思考、信仰、享受和梦想的方式强加于他人。
臆想的未来世界将由于全球化而丧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及正在遭受美国文化侵犯的梦魇或反面乌托邦,已经不是那些怀恋马克思、毛泽东、切·格瓦拉的左翼政治家们独霸的领地了,这种由于对北美巨人的深仇大恨而激发出的胡言乱语,在发达国家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也随处可见,并且左、中、右政治势力在这一点上都出奇地一致。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法国。我们看到,那里的政府不断发起各种行动,以捍卫法国的“文化身份”不受臆想的全球化之威胁。一大堆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都惊慌失措,以为曾经孕育了蒙田、笛卡尔、拉辛和波德莱尔的国土——一个在时装、思想、艺术、美食等等一切精神领域都得风气之先的国家——将可能被麦当劳、比萨饼、肯德基炸鸡、摇滚乐、饶舌音乐、好莱坞电影、牛仔裤、旅游鞋、T恤给侵占了。这种恐惧感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向本国电影工业发放大量补贴,强制要求电影院必须放映一定数量的本国电影,限制进口美国影片。也是由于这种恐惧感,导致地方市政当局发布规定,对商家字号等在招牌上使用英语予以重罚(不过,如果你漫步巴黎街头就会发现,人们并不把这种规定当回事)。也是这种恐惧感,让抵抗垃圾食品的农民十字军战士荷西·波维(他曾攻击法国麦当劳店)成了法国大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最近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则让他更为声名大振。
尽管我相信,这种从文化上反对全球化的论点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还是需要洞悉深深地潜藏在其背后的无可置疑的真相。我们将要生活的新世纪比起二十世纪来说,可能更少独特性,也更少本土色彩。过去曾经赋予人类各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节日、服饰、习俗、仪式、典礼、信仰正在趋于消失,或者仅仅局限于很少地方,而很多社会则抛弃了这些东西,采用了其他更适应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东西。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这种变化进程,只是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不过这种变化却不是源于全球化,相反,它是导源于现代化,全球化只是其结果而非原因。当然,这一进程确实令人悲伤,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消逝,的确令人伤感怀恋,尤其是我们舒舒服服地站在目前很优越的立场上看,那些逝去的东西蛮有娱乐性、原始性,色彩也很丰富。然而,此一进程乃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现代化使多种形式的传统生活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种种机遇,使一个社会向型构为一个整体迈出重要的一步。正因为此,当人们拥有可以自由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有时会毫不迟疑地选择跟他们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传统主义者正好想反对的东西,即选择现代化。
反对全球化、赞同文化身份的论辩,表现了一种没有历史根據的静态的文化概念。有哪一种文化是一直保持其同一性而不随着时间而变化?这种静止不变的文化,我们恐怕得到那些生活在洞穴中、崇拜雷神和野兽、很小的、很原始的巫术社会中才能找到,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原始性,它们越来越容易被文明人开发利用,从而逐渐消亡。而其它文化,特别是那些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和有活力的文化,都已经演进到这个阶段,它们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两三代人的生活,这种演进在法国、西班牙、英国这样的国家再明显不过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广泛深远,假如普鲁斯特、洛尔卡,或者维吉尼亚·伍尔芙再生,恐怕也认不出这就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国度——而社会的这种变迁,他们的贡献也是有份的。
“文化身份”的概念是危险的。从社会的立场上看,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可疑的、人为的概念,而从政治观点看,它则威胁着人类最宝贵的成就:自由。我不否认那些说着同样语言、出生和生活在同样的地域、面临同样的难题、遵行同样的宗教和习俗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品性。然而,集体这个大分母,永远都不能准确地界定每个个人,它只能消除构成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彼此区分的大量独特的性格和特性,或者将其轻蔑地视为次要的层面。同一性(identity)的概念,只要不是将其专门用于个人意义上,就那必然是化约主义和非人性化的(reductionist and dehumanizing),是从集体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抹杀人类全部的原创性和创造精神,认为人类无非是在传统、地理环境和社会压力影响下的产物。相反,在我看来,真正的身份来源于人类抵制这些势力,运用他们自由的发明创造活动抗拒其压迫的能力。
“集体性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是民族主义的基石。而在很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看来,即使在最古老的社会中,集体性身份也绝非事实的真相。共同的风俗习惯对于一个集团的防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集团内部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之要求释放的冲动,也总是非常强烈的。当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动的时候,个体之间的差异总是超过集体特性,个人不再是集体的无足轻重的简单元素而已。全球化把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自己的动机、通过自愿行动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扩展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公民身上。现在,公民们不再像过去以及现在的很多地方那样,只能一味地屈从于那种使他们陷入无可逃避的集中营的所谓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乃是透过语言、民族、宗教及他们出生之地的习俗而强加于他们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必将广受欢迎,因为它显著地扩展了个人自由的范围。
一块大陆,两个历史
也许拉美最集中地表现着试图建立集体身份的技巧和荒谬之处。什么是拉美的文化身份?什么东西可以包容在这样一个内在一致的信仰、风俗、传统、习惯、神话的统一体中,从而可以赋予这一地区以单一的个性,独特的和不可改变的个性?在知识分子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的论辩——有些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的历史被篡改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曾在整个大陆引起反响的西班牙语学者与土著人之间的斗争。
在何塞·德拉里瓦·阿吉罗、维克托·阿德雷兹·贝隆德及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等西班牙语学者看来,拉美的诞生,有赖于地理大发现和大征服,有赖于整个大陆改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及皈依天主教,从此以后,她才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班牙语学者并不是看不起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文化,但他们却认为,这些文化不过仅仅构成了社会和历史现实的一个层面而已——还不是主要的一层——只有在感受到了生气勃勃的西方的影响后,才完全形成了它的个性。
另一方面,土著则满怀义愤地拒绝承认欧洲人给拉美带来了任何好处。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身份可以从西班牙统治以前的文化和文明中找到自己的根和灵魂,而在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及建立共和国之后,这些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则受到暴力的残酷压制,受尽了诋毁、压迫和边缘化。按土著思想家们的说法,正宗的“美洲人的表达”(American expression,这是何塞·莱萨马·利马一本书的书名)就体现为,在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土著的语言、信仰、艺术、大众文化等等中抵抗西方文化的压迫,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思想流派中极为著名的一位历史学家、秘鲁的路易·瓦尔加西尔甚至主张,教堂、修道院等殖民主义的建筑遗产,都应该焚毁,因为它们代表着“反秘鲁”的文化,它们是鹊占鸠巢者,是对质朴的美洲身份的否定,这种身份只能到土著文化之源头那里找到。拉美最具原创性的小说家何塞·马里亚·阿盖达斯在一本非常微妙而充满激情的道德宣言性小说中,描写了安第斯地区印第安盖丘亚部族为生存而抗争的壮丽史诗,而西方人则曾对这一史实进行了压制和歪曲。
西班牙语学者和土著人都炮制出了连篇累牍的辩论文献,也创作出了极具创意的小说,然而以今天的观点看,他们都一样地是宗派主义者、化约主义者,一样是错误的。拉美文化广泛的多样性不可能套进他们造出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紧身衣,两者都难免种族偏见之嫌。在今日时代,谁敢宣称只有操西班牙语者或者只有印第安人才配合法地代表拉美?然而,今天,仍然有人凭借某些理由而鼓动政治和知识上的狂热,试图伪造和孤立我们独特的“文化身份”。企图把一种文化身份强加于某人,无异于把他锁在牢笼中而否定他最珍贵的自由——自己选择干什么、怎么干及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拉美并非只有一种身份,而是有多种文化身份,没有一种可以宣称自己比别的文化身份更合法或更纯洁。当然,拉美包含着前西班牙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及安第斯国家,这种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力量。然而,拉美也是操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们的世界,他们的传统也在这块大陆上出现并繁衍了五个世纪之久,决定性影响了这块大陆当代的形貌。拉美难道不也依稀有几分非洲的样子吗?非洲人不也跟歐洲人一起来到我们的海岸?非洲人的出现不也在我们的肤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社会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塑造了拉美的文化、种族和社会的成分,把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文化联结在一起,我们有如此之多的文化身份,没有一样可以说自己是根本性的。而此一现实,与那些民族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其实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这也是极佳的信任状,得以使我们感觉到自己就是生活在这一全球化的世界上的羽翼丰满的公民。
本土声音,全球回响
恐惧这个星球会美国化,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妄想狂,而非现实。当然,毫无疑问,随着全球化,英语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用语言,就如同拉丁语在中世纪的地位。英语的地位将继续上升,因为,它是国际贸易和交往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英语的发展必然就以牺牲其它语言为代价?绝对不会。事实上,恰恰相反。一个国界消失、彼此越来越趋于互相依赖的世界,将激发新一代人类学习和模仿其它文化,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业余爱好,而是出于一种需要,因为能说多种语言、能在不同文化之间进出游刃有余的能力,将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举西班牙语为例。半个世纪前,讲西班牙语的人是一个内向的社会,我们只能在自己传统语言划定的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今天,西班牙语获得了活力,兴旺发达了起来,在五大洲到处开花结果。仅在美国,目前就有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讲西班牙语的人,知道这一事实才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和戈尔在选战中,都不仅要用英语,也得用西班牙语。
全世界有多少男男女女为了应付全球化的挑战而拼命地学习日语、德语、汉语、粤语、俄语或法语?幸运的是,这种增长趋势将不仅限于未来几年。正是因为这一点,捍卫我们的文化和语言的最佳途径,就是推进它们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繁荣昌盛,而不是天真地坚持把它们隔离起来以使之免受英语的威胁。那些做如是想的人们嘴里来来回回不离文化,然而,他们的言论可能被那些无知的人用来掩饰其真实的意图:民族主义。如果说,对普遍主义的文化倾向还存有什么争议的话,那是因为民族主义者企图将其狭隘的、排外的和混乱的看法强加于文化生活。各种文化教给我们最应该记取的教训就是:文化不需要由官僚机构或什么委员会来保护,也不需要将其禁锢在铁丝网后面,或者为了维持其生存和生命力而用海关将其与世隔绝起来。恰恰相反,如此这般的努力只能使文化枯萎,甚至使之凋亡。文化必须自由地生长,不断地与不同的文化进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革新、复兴,使其演进,并适应滚滚而来的生活潮流。古代拉丁人没能灭绝希腊文化,相反,希腊文化的艺术创造性和思想深深地渗入了罗马文明,由此,荷马的史诗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才得以传遍整个世界。全球化并不会使本土文化消逝,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框架中,本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和值得保存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这种局面已经在欧洲各地开始显现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那里的地方文化正在富有活力地再度复兴。在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时期,地方文化受到压制和否定,而只能秘密地存在。随着恢复民主制度,西班牙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被释放出来,可以自由地发育成长。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地区,本土文化非常繁荣,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地区。其它地区也很繁荣。当然,我们万不可将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地方文化的复兴与那种对自由的文化构成严重威胁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1948年,T.S.艾略特在一篇很著名的随笔《文化定义随谈》中预言说,人类未来将经历一次本土和地方文化的复兴运动。当时,他的预言可谓相当大胆。然而,全球化似乎将使他的预言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现实。我们应该为此高兴才是。小规模的、本土的文化的复苏将使人类的行为和表达具有充分的多样性,而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为了创造所谓的民族文化身份而曾经对此竭力予以消灭。民族文化经常是用血与火铸就的,禁止教授和出版一切方言,也禁止遵循一切与民族国家视为理想的宗教、习俗有所不同的宗教习俗,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强制性地把一种主流文化强加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从而无法公开地表达出来。而与那些担心全球化的人们的警告相反,全球化并不容易彻底地消灭文化。一种文化,只要它的背后有丰富的传统和足够的人们哪怕是秘密地遵行,那么,这种文化即使很小,也不可能被消灭。今天,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弱化,我们正在看到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被边缘化、曾经被迫沉默的地方文化又复苏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星球上壮阔的交响乐中表现出了富有活力的生命迹象。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西班牙知名小说家,其最新作品是《山羊的聚会》。
秋风,自由职业者,现居北京,有译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