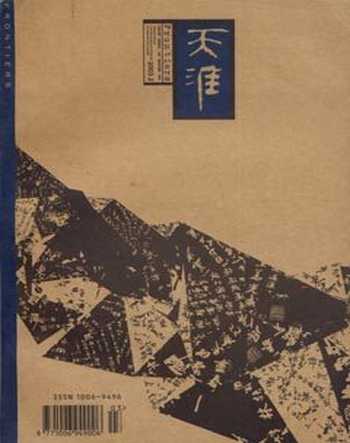虚度时光之后(小说)
2003-04-29安托万.佛楼定林惠娥
安托万.佛楼定 林惠娥
[法]安托万·佛楼定著
林惠娥译
当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将离开,迷燕和得地。他们将一去不回,他们将消逝。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不断地提醒我,而且几个星期以来,那焦虑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晚上,就像我们都死了之后的每个晚上一样,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一动也不动。我身上的床单很重,我的心怦怦跳。我一定是在睡觉的时候喘了气,好像在遥不可测的地方刚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立刻想到迷燕和得地,在那里,他们因为年纪大了而被人弃置在那个特别区里。自从我上回春天的一个晚上去探访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最近这几个月来是怎么过的,他们。
那之后,每次想到迷燕和得地,我内心就会起一阵晕眩。一团强烈的空虚的感觉从我肚子下方逐渐地扩大,在我的胃和心之间缠绕着,不断地折腾我。我常常又看见迷燕和得地,两人并立在隔离营的一间破旧的小屋的前面,挥着手默默地道再见。那间破旧的小屋子和其它的木棚屋子之间隔着一片小桦树林,看上去像一间林中小木屋。路上长满了草和旺盛的禾本科植物,好像只在梦里才看得到的那种草尖茂盛的绿茸茸的植物。我也挥着手,走了。草闻起来湿湿的,带有发霉的干草味,还有蜗牛和蜜的味道。草高到我的髋部,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之后,他们的医生,狐克死,给我打了电话。是梦界吗?迷燕和得地情况很糟,不得不将他们转到隔离所。今年冬天将是他们最后的冬天了。
这个消息真叫人受不了。迷燕和得地就像是我的养父母。在我死后,他们接待我,并且教導我如何克服对所谓的生存之路的反感,这条路在死后附加的漫长的部分更加荒谬。他们协助我对付我那漠不关心和软弱的倾向。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可能连幸存的力量都没有。我会在营里可怜兮兮地漫步游走,愚蠢地喊叫着,而脑子里既想反抗又空洞无比。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世界。
“之后呢?冬天过了之后呢?嗯?……”
我嘴巴说着话,可是它宁愿大声喊叫,或者呕吐。我开始跟医生讨价还价,好像他拥有神秘的力量。
“他们一旦住进隔离所,也许可以再多留一年,不是吗?再多留一两个冬天,……不是吗?”医生没有试着掩饰他被我的话所激起的愤怒的轻蔑。我们之间一直存有敌意,甚至在我们两人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在党里属于敌对的派别,而且,从前在国内内战气氛之下,我们天天互相辱骂彼此伤害。当他太太哑丝谜娜·狐克死为了跟我在一起而离开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哑丝谜娜和我,我们是一块儿被枪毙的。狐克死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但是我相信他绝不原谅我。
梦界,不要唉声叹气。谁也不能永远幸存着,总有终点站,那就是隔离所。
我们当然是彼此憎恨对方。可是,我们曾经为了相同的古老目标而积极战斗,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属于同一个互助组织,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在这个组织里不算什么的。狐克死在那个互助组织里占有一个战略位子,因为他是拘卡笆基金会某个部门的主任,就是迷燕和得地最后去的那个特别区。迷燕和得地没有要求任何特别待遇,在党的历史档案中,他们没有资格刊登一张他们的放大照片,他们与我们其它的人一样,默默无名地英雄般壮烈死去,但是我知道狐克死有办法运用他的职权,让他们在拘卡笆基金会的生活不那么悲惨。
“您可是有办法给他们找到别的去处,而不是囚禁在隔离所里。”我吼着说。“我提醒您,他们是组织的成员,有权获得您的协助。”
狐克死说,梦界,我已为他们尽了力了。如果他们逐渐退化,一天不如一天,这不是我的错。
“什么尽力了?他们逐渐退化,怎么会呢?”我的反驳惹火了狐克死。
于是他说,您自个儿来看看吧。隔离所的门会为您打开,让您自个儿看。我会指派人接待您。除非奇迹出现,迷燕和得地是活不了的。他们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梦界,这是一般的过程。我承认面对这样的事,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对狐克死说,他的解释无法令我满意,而且他不需要提起他的无能。我已经跟他太太充分地讨论过了。
狐克死很生气地说,梦界,不要把哑丝谜娜·狐克死跟这件事混在一块儿谈,毫无关联。假如您够勇敢的话,倒不如亲自来察看事情真相。
“为什么?够勇敢的话?什么?”我结结巴巴地说着。
狐克死说,一旦进入隔离所,就跟其他的病人没什么两样了。
“您意思是?”
“对您是同样的,您一旦进入隔离所,很可能有危险,您会退化。”
“没关系,我要去。”我答应了。
我语气很肯定,一点也不惧怕。我向来什么都不在乎,除了对迷燕和得地的命运。我如果进入隔离所,不是要向狐克死证明我不是懦夫,不是的。我那样做是要安排迷燕和得地逃出隔离所。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尽我一切力量让他们再幸存一段时间。
狐克死说,梦界,您知道那终将结束,谁也没办法留住他们,您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我摇摇头,对狐克死说他从来都不懂得如何留住任何人,连他太太也留不住。
狐克死吼着说,不要把我太太跟这件事混在一块儿谈。
他的声音渐渐变干了,他可真是受不了跟我谈话。
我挂了电话。
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田野里没有任何动静。月亮闪耀着。我立刻动身。
去拘卡笆基金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直达的路线,而且在满月期间上路的话,还得预期会碰上额外的难题。路上确实有不少阻碍。我迷了几次路,最先在干枯的森林里迷了路,随后在水灾为患的幽暗深邃的森林里迷了路,后来在荒凉的城市里、在废墟堆中、在忽明忽暗的隧道里迷了路。我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一个人,甚至当我反向穿越重重人潮的时候,一个人也碰不到。我一再地被刮伤被弄脏,当我一个月之后终于进入了特别区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发臭的破烂的衣服。我来到距离特别区外带刺铁丝网的围墙一百公尺远的小沟渠中,疲惫不堪,几乎无法再往前走,便坐在两块石头之间,打算在树下睡一觉,好让体力恢复。
我觉得自己没有走出梦乡,这是个极不舒服的感觉。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样叫我高兴。疾病侵蚀着一棵棵冷杉,它们的树枝在寂静当中断裂而发出噼啪声,泡状的树脂逐渐地流失。在刺铁丝网之后,圈围动物的栅栏已经生锈了,里边已经没有动物了,除了地上一些食尸者所留下的乌鸦的残骸。一股臭药水味在空中盘旋着。月亮在贴近山顶之处凝住了,就不再移动了。
休息了半天之后,我来到隔离所的入口处。
“狐克死指示要接待我。”我说。
守卫人员们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我包围起来。
月亮连一寸也没有移动。草地上和隔离所入口铁大门的支架上都沾有露水,露珠闪闪发光。我不太确定眼前的夜景是真实的或者是在梦中,我在那个情境里扮演了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访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在小沟渠中醒过来,收拾了我所有的东西(一瓶水、一包已经打开的干肉饼、一本迷燕和得地上次向我要求带来的医学词典),并且在穿越了圈围动物的栅栏之后,进入拘卡笆基金会。但是,我同时怀疑,也许这些记忆都是虚假的。
守卫人员拦住我,把我的袋子抢走。
“狐克死肯定跟你们提过我,我叫作梦界。”我强调说。
守卫人员用暧昧的语句交谈了一阵子,动作很粗暴。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按照规定搜查了我的袋子。其中一个守卫强迫我四肢分开,靠在墙壁上,他拍着我外衣的口袋,拍着我破烂的长裤裤脚,又拍着我腋下的衣服,同样是破破烂烂的。
“我要见狐克死,”我无可奈何地说。
有人把我的头压在墙壁上,要我闭嘴。我的嘴所贴着的水泥发出恶臭。
守卫人员把我身上唯一的一块美金没收了(那是我留着回程时候用的),他们也没收了那本我想送给迷燕的词典,当我开口要抗议的时候,他们用手和乌鸦的残骸刮了我一个耳光。之后,他们把我拉进狐克死的办公室里。
狐克死只给了我很短的时间,说他在别处还有一个约会。我既认不出他那肥胖的身体,也认不出他的脸。他像一只蜷缩在椅子上的干瘪怪物,他外衣下面的双肩极其可怕地突出着。我们最近几年来都是用电话联系,所以我并不惊讶自己很难认出他。而我同时又确定,那人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助手或他的替身。我们的眼神没有交会。所有的灯都关掉了,所以看不清楚。他办公室的门没有关上,为了让里面不至于完全黑暗。外面,已经天黑了。
我站在昏暗当中。他没有请我坐下。
他向我证明迷燕和得地住进隔离所之后退化得更快。我当然没有透露我打算安排他们逃跑的想法。我让医生自言自语,而在他沉默的时候,我就说些不关紧要的话。随后,我指出没收我带来的医学词典是违法的。狐克死发出冷笑。他认为那本词典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在隔离所里继续求生的情况下,任何医学问题都不再是实际问题了。再说,迷燕已经没有能力阅读了。
梦界,当您在那里的时候,千万不要接近他们。那会马上毁掉他们两人。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您的位置。您得完全遵守他们的指示。简而言之,梦界,我把话先说在前头,您的生理机能是适应不了的。没有医学上的准备就进到隔离所里面,那会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他这时候一脸不屑地观察着我,双手的手指很奇怪地滑动磨擦着。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但我想象得到他那张扭曲的嘴巴,还有他对我的轻蔑。他在向我挑战,我不时听见他空虚的指骨所发出的响声。一段死寂的时间之后,他突然对我说,我还可以放弃初衷回我的住处去。
“什么样的后果?”我问他。
他回答说,精神错乱以及意志衰萎。您甚至对幸存这个念头都会感到陌生。
“这点,对我来说可不是新鲜事,”我说。“我已经习惯克服这点。狐克死,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要为迷燕和得地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他们在我死后帮了我很多忙,我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话,我什么都不是。”
医生一边耸起他那幽暗不明的怪物般的锁骨,一边低声地说,梦界,您什么都不是。一旦进到隔离所,您将会比什么都不是还要不是。
我们的会谈结束了。
在那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大的纸屑篓,狐克死把一堆海鸥的翅膀当作揉皱的草稿纸,乱七八糟地丢在那篓里。这个细节,再加上医生那张无可辨识的脸,使我更加觉得自己很可能还没有完全回到真实的世界。
狐克死和我各自分头走了。他指给我看该往隔离所里的哪个部门去。在幽暗的天空中,月亮一直守据着同样的哨岗,就是在一间间小屋的水泥顶后面的树梢上方。风极缓慢地吹着,慢到无法把臭药水的味道吹散。这个消毒药水呛人的味道此时混杂着种种臭味,还有那些来自所有的食堂和一间间大型的集体囚笼或是个别的等死房的臭味。我双腿旁的草不断地发出唏嘘响声,那些草湿湿的。我总是踏到躺在地上的鸟,那些还没被虫蚕食掉的鸟尸体。因此我避开人们走的路径,宁愿很辛苦地穿越拘卡笆基金会开幕以来就未曾除过草的草地。我现在不是很确定,但我想我那时候就是这么辛苦地走了几个小时。
守卫们接待我好像在接待一个擅自漫步的宿客。在用一具猫头鹰的骨骸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守卫们把我丢在地上,然后打我。他们拒绝听我的免遭恶打的要求,尽管我提到狐克死以及我和他的关系良好,也起不了作用。他们好像聋子。当毒打结束时,他们虚伪地笑着向我道歉说他们把我误认为另一个人。而实际上,他们明明就是在取笑我。我猜想,他们毒打了我,就完成了狐克死要他们做的事。我站起来,整一整我身上的破旧衣服。
一个医务助理人员对我说,我们会把您安顿在走廊的一个角落,不过,向您的幻想告别吧。您见不到迷燕和得地,他们已经离此地太远了。您既见不到他们,也不能接近他们。
“那他们呢,他们能不能看见我?”我问道。有人回答说,不可能,会面是不可能了。
我望着挡住小屋入口的人群之后的地方,我在半暗半明的月夜里用眼梢左右瞄来瞄去。那栋屋子是拼装屋,没有楼层,它的窗户都装上了不难拆下的栅栏。脱逃是可能的。要从那里面逃出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是带着衰弱的并且没有能力跑路的迷燕和得地。但是之后呢?我们要去哪里呢?
那个医务助理人员又说,只有工作人员才能在隔离所里走动,而且必须经过特别的训练才可以接触那里面的宿客。您呢,待在您走廊的角落,不要走动,懂吗?
“懂,”我小声回答。
工作人员们看我不吵也不闹,态度就缓和了。他们给我讲述迷燕和得地的情况,情况很不好。
迷燕现在的羽毛总是脏得不得了,她已经放弃了她向来对个人卫生极端的讲究。得地则常常缩在墙脚下或家具的下面,即使那样的地方一点也不舒适,他却一缩就缩上几个小时。当守卫来喂食他们或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再抗拒了,他们不再向守卫们的头吐口水,他们不再尖声地吼叫,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向守卫们怒喊,向守卫的妻子、母亲和祖先们怒喊。特别是得地,变得沉默而且被动,不管人们在为他做什么事。当助理人员把迷燕拉向浴缸,然后把她浸在蒸汽弥漫的幽灵的洗澡水里的时候,她还会反抗。她不停地抱怨,抵抗着,警告助理人员,热水会使她泻肚子,又抱怨她的括约肌无力。当守卫人员把她拉出洗澡水,然后用力擦干她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搞得全身脏兮兮的,这一次,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咧开双唇,露出一种愚蠢的满足。对在二十年前认识迷燕的人而言,她这种抗议方式显得可怜不堪、毫无尊严并且丑陋无比。守卫人员们用肮脏的毛巾和恶臭的浴袍打她,然后一路把她踢回她的囚笼里,只是注意遵守狐克死给他们的警告,就是不准打断她的骨头。
受折磨和羞辱的迷燕就这样回到他们的囚笼里,和她去浴室之前一样地满身泥泞。得地却不像从前那样温柔地迎接她,当他们两人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们死后,得地对她都很温柔,一直到他们住进特别区里。得地不再流露任何情感。他只从他藏身的家具下面或墙角睁开一只眼看着迷燕回来,然后把眼皮阖上。
守卫人员们不拉得地去浴缸,因为他還能自己洗澡,但是他洗澡的时间很奇怪,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时间感,睡眠时间也不规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得地时常打断他那天晚上或是前一天晚上一直保持的紧张的静止状态,而活动了起来,然后突然步伐敏捷地往浴室走去。门开阖的声音以及水流的响声吵醒了整区的宿客,水管不停地振动,水龙头哗啦哗啦响个不停,很快地,在大厅里打盹的看守发怒了,便从他的扶手椅起来,走去看是谁在吵闹。看守的人经常是一个不知叫作苛他还是苛特的守卫。
苛他捻亮了淋浴房天花板的灯,走到得地浸泡的浴缸那里,他拍打着得地露出水面的所有部分,对得地吐出一串串的辱骂,最后还打开浴缸上方的窗户,希望冷风透过栅栏吹进来,伤害得地的肺。外面的温度不低,不过,夜间守卫们都有这种恶毒心态,苛他或是苛特也不例外。
正是这个苛他让我进入那栋建筑物里,把我安排在长长的中央走廊的尽头。
我不可以跟任何一个人有接触。夜仍旧是幽暗不明。我蹲在一个角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人忘记了。那时候,我就可以为我自己和迷燕及得地做好一份脱逃计划。
我就这样蹲着,蹲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智力衰退的问题,狐克死说得没错。脱逃的想法慢慢地破碎,我所有的想法逐渐破碎。走廊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而且小屋里也显得空荡。我为了不惹苛他或其他的工作人员生气,不得不承受着石化作用,我老想睡觉,而且有时还心不在焉。
走廊的另一端有一间办公室,看起来和狐克死的办公室很像,很可能是一间医诊室,不像狐克死的办公室那么暗,有一个与他的纸屑篓相同的篓子,里面装满了一块块灰色羽毛的或羽毛泛黄的残缺的鸟肢体。在我前面约十五公尺之处,有一些残破的翅膀。其它的门都敞开着,不过,那些房间里或囚笼里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事物。
偶尔有人走过,他们的脚步声使我惊跳起来。我很想再见到迷燕和得地,但是出现的侧影并不像是他们的。在走廊上走动的人大多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有的时候,有人靠近我,把我当作这里的另一个人,也许当作迷燕和得地,然后威胁我,要我回到我的笼子里。另一些时候,有人用肮脏的毛巾抽打我,又用那些脏毛巾阻碍我前进,但没有直接触及我的衣服或皮肉。我必须赶快向他们解释,直到他们的误会消除,再次把我抛弃在低声抱怨的命运之中。
我重新蹲下来,经常不知道怎么处理躺在我面前的鹈鹕翅膀,那翅膀散发出腐烂的味道。我小心翼翼地一边左右摇摆着,一边用脚尖把那翅膀推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后回到我的位置上。不久之后,我苏醒过来,好像曾经昏昏睡了几秒钟。那翅膀不见了。这下,可把我搞糊涂了。
我对什么都不能确定,忧心忡忡地想着迷燕和得地。我多么想尽快跟他们联络上,跟他们谈一点具体的事情,互相看一眼,彼此做个手势,我多么想再度参与他们的幸存过程,跟他们在一起。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而情况毫无改变。小屋外面半明半暗的夜晚一点也没变化。忧愁和不安使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我的眼睛模糊了。一道月光擦过那个装有四分五裂翅膀的纸屑篓,这个景象使我很难过,我宁愿再回到半昏睡状态之中。
有一天,狐克死来到小楼里,走到我打盹的走廊的角落,我蜷缩着,四肢麻痹了,他拍打我的肩膀把我叫醒。我那时候正在做梦,梦到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迷燕和得地的房间里。他们两人抽搐地大声地呼吸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并且咕噜咕噜说着难以理解的话。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跟其他的宿客一样,翅膀都被拆走了。夜光轻轻照着他们的脸庞。我想他们是迷燕和得地,可是,他们的五官和表情看起来却是很陌生。他们也没有认出我。
梦界,您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我把头往狐克死的方向抬起来,我的迟钝使我无法回答。
医生继续说道,您亲眼看见了吧?他们以很快的速度远离此地,就像其他所有在这里活不了的人,包括您,梦界。
狐克死高高地俯视着我。我的视网膜长久以来已经适应了黑暗,假如他没有带上医生面罩的话,我或许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的脸。工作人员们在进入隔离所的时候,都穿上特别的服装,这使他们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但是狐克死四肢长而躯干短,并且他的骨头很奇怪,乱七八糟地突出来,即使他不说话,人们从他的骨头就能认出他来。我听得出在他最后的几个元音里夹杂了一个微笑,他很高兴看到我潦倒不堪,浑浑噩噩,连一份明确的个人计划都没有,好像已经不存在似的。
他咬着牙说道,这个情况还会加速恶化。没有人能够再找到他们,甚至不再合理地记得他们。他们今年冬天里会消逝。
“我有一件事要抱怨,”我说。
什么抱怨,梦界?
“他们受了折磨,”我说。
狐克死抗议说,没有这回事。我指示过不让他们受任何折磨。组织里有一个守卫,叫作苛他,负责保护他们。
“他们没有翅膀了,”我说。
狐克死说,啊?
我听到他的手不断地抽紧放松,抽紧放松……他的关节噼啪作响。月亮很苍白,只照亮了他的腿。
“没有了,狐克死,他们没有翅膀了,”我坚持地说。
狐克死解释道,他们很可能是自己掉的。梦界,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处看。他们自己掉落的,那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彼此逼视着对方几秒钟。我极难专心听我们的对话中,什么说出来了而什么又没说出来。我只知道自己恨死了狐克死,而且我得避免引起他怀疑我打算使迷燕和得地逃走。多说一句话可能会把一切搞砸了,可是我记不太清楚我当时脑子里想什么。我想说话,想对狐克死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我只是动了动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医生再次开口说,梦界,他们将远离此地,而您,您会继续幸存下去。您最好马上离开隔离所。
“我要您留住他们,”我终于说出这句话。
我就没再说什么了。我想用眼神和沉默说着话,我试着想着哑丝谜娜·狐克死,以此来羞辱他并且激怒他。我们置身其中的小屋子让人感觉空荡荡的,觉得它已经撤出了所有的医疗事务或其它的活动,一点响声也没有。就像每天晚上,月亮很可能滞留在树的上方。走廊上有木屑的味道、黑肥皂的味道和鸟粪的味道,我想着我与哑丝谜娜·狐克死的恋情,我用眼神和沉默威胁着狐克死。
医生突然发怒说,梦界,够了吧!不要把哑丝谜娜·狐克死跟这件事搞在一块!
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数了数我外衣口袋里所剩的干肉饼的碎片,两片。我还有两片,这够我坚持下去。重要的不在抵抗饥饿,而是执行我的计划。重要的是有一份计划并且执行之。
守卫们十一月的时候把我驱逐出那间小屋,他们依照狐克死的命令行事,尽可能避免不人道的举动。不是苛他或苛特而是狐克死自己亲自拔除我的翅膀,然后把我丢到外面,丢在高高的草堆之中。我双肩什么感觉都没有,医生没费什么力气,而一切自行脱落。当医务助理人员们挡住我的去路的时候,狐克死反倒鼓励我回去我原来的住所,在那里等死总比在这里等死好。我看到在我的上方那个穿着衣服的影子,当那影子拍打我要我消失的时候,我听见他空洞的骨头嘎咂的响声。在我内心里,我把他叫作狐克死,然而,我事实上已经不知道谁是狐克死。我从我滚动过的草地里向他做了一个友善的诀别手势。我完全记不得狐克死以前是一个同志、一个敌人或是一个对手。我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很有问题,但是我似乎宁愿往好的方向想。既是出于礼貌,也因为我若做相反的事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为着我们曾经有过愉快的关系,所以我向他友善地挥着手。而他已经转身背向我,没有回应。他站在隔离所的门口,看得见他的脚旁有一些翅膀残块。月亮照亮了其他的医务人员,除了狐克死。他们都带着面罩,彼此商量着。也许他们彼此问着,我是否那天夜里就会完全解体。
现在,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明暗如何,再说,时间和明暗都没多大改变,我缓慢地在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之间走着,在高高的草堆里游荡。我绕着迷燕和得地住的小屋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根据狐克死在隔离所门口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在那间小屋里继续地退化。我不论是在梦中或是清醒着,都绕着圈子走动。我不知道哪种策略最能让我不被察觉地进入那小屋里而准备脱逃行动,因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应该行动了,在还不会太迟的时候行动。比如说,我绝对应该弄清楚迷燕和得地被囚禁在哪一个窗户后面,哪一个栏杆是我应该悬挂的,直到它从水泥墙上掉落,还有,在我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我所爱的人之前,哪一片玻璃窗是我应该打破的。我了解到我在那间建筑物里所度过的日子简直是浪费时间和体力,因为我永远不能与迷燕和得地取得联系,甚至不能瞥见他们。现在,一切得在外面准备。
我想,人们把我忘记了,或者他们认为我从此以后变得不怎么有攻击性并且很卑微了,所以不必找我麻烦。人们有的时候把一块块鸟的残骸丢到草地上,如果正好丢到我的脸上,那可是我倒霉而不是他们故意的。我认为没有任何人真的想找我的碴,那样的事只能算我倒霉。当守卫们、医生们或工作人员路过草地小径的时候,我就平躺在地上。那土地闻起来有营区后面特有的湿湿的尿臭味,草(下转第188页)(上接第134页)在我的肚子下面被我压搓而发出响声,正如它们向来在初冬时所做的反应,空气中日夜都流传着消毒药水味,或是肮脏衣服的臭味,或是医务助理人员所拔下来的翅膀的味道,或是自行掉落的翅膀的味道。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四周更加幽暗了。月亮毫不移动,但越来越弯,越来越单薄,最后消失了。她从此不再出现,于是我想我要趁这个黑暗行动。月亮曾经阻碍我行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什么准备。面对复杂的脱逃计划,我是有点被动有点怠惰,而此刻,天很暗,我可以比较容易从事一项大胆的举动。而且我突然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付之行动。
我的主意是这样的:我要在离那些建筑物有点距离的地上挖一个洞,以至于人们不会看见。一旦我把迷燕和得地弄出来之后,我就将他们带到那个洞里,我们三个人都在那洞里,迷燕、得地和我。我不知道我们会继续活多久,因为我所预备的干肉饼总有吃完的时候。我所确定的是,守卫们将找不到我们。
安托万·佛楼定,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猿猴之名》、《内港》、《二流天使》。
林惠娥,台湾学者,现居法国。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