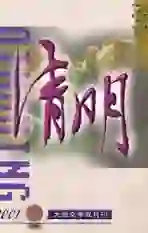生活本身在说话
2001-03-31鲁彦周苏中
鲁彦周 苏 中
1950年10月11月的两期《说说唱唱》杂志上,连载了一部中篇小说,书名《活人塘》,作者是陈登科。这是一个在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名字,但这家杂志的主编却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而这位著名作家不但选中这位新人新作予以发表,而且还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题写了热情洋溢的四首赞美诗,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这家刊物的编委田间、康濯等人,力荐这部作品,并要求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向公众介绍这位新起的工农作家。康濯在1951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的评论文章,指出《活人塘》“朴实、自然地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一切惨烈无比的甚至很难用文字表现的场面,作者都大胆地展示开来,色彩浓,气势大,使我们完全感到当时中国人民严重的情况和斗争情景”;“小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此后不久,在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周扬又以十分热情的语句,称赞陈登科“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强烈的真实情感和力量。在他的作品中,简直不是作者在描写,而是生活本身在说话。生活本身就是那样一场惊心动魄、天旋地转的斗争风景。”我们知道,周扬的文艺批评往往是从政治角度探视多于学术探究,但他这句“生活本身在说话”却十分简洁又十分确切地概括了陈登科的文学特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不仅道出了《杜大嫂》、《活人塘》的基本特色,它还概括了陈登科毕生文学生涯的最显著、最个体化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成名作《活人塘》,还是扛鼎作《风雷》;或是晚年力作《三舍本传》,他几乎都是以“生活本身在说话”这样的叙述方式,展现着生活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的小说世界和生活本原世界浑然一体,时代影象、地域风情、人物话语等,都是以逼真而又传神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他的小说艺术魄力,主要不是靠情节设计的诡谲多变或故事的波澜起伏来吸引读者,而是靠真实的生活情境,真实的人物形象,真实的感情表达,真实的地域风情,真实的性格化语言等等特色,构筑起陈登科小说世界独特的艺术个性。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意味着陈登科不善于应用情节和故事。不,作为农民出身作家,他自幼受到许多民间文学、传统戏曲及曲艺文学的影响,他深谙故事情节的巧妙曲折对打动读者的作用,而且他也是长于编织故事的能手,但他的小说特色主要的却不在于讲述或演绎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在展现“生活本身在说话”,并使读者走进其中,亲历生活本身的多面、多层、多边、多样、多变、多彩等等形态,让读者从中领略生活本身给你的启迪、感悟与认知。
这一特色,构成了陈登科的文学个性,也贯穿于陈登科的整个文学生涯。然而,《活人塘》只是形成这一特色的起点,它只是作者按照个人生活体验来复制生活本来面目,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还受着素材的限制,受着真人真事影子的限制,缺少更高的艺术概括力,故多多少少带有自然主义痕迹。作家在以后的长期实践中,逐步摆脱了这种模拟现实的非自觉的创作状态,逐步领悟了形象思维创造性特征,在忠于“生活本身在说话”这一基本素质的同时,将艺术典型化原则,将想象、提炼、虚拟、集中、烘托等诸般现实主义方法与技巧,融入到他的创作过程之中,从而使作品展现的生活景象不再受一时地之局限,其人物也不再受制于真人真事的拘泥,而是将作家的广泛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融于塑造更富有典型性、更具美学涵盖性的人物形象上,特别是在《风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花费了多年心血,精心构思,反复修改,刻意打磨,终于体现了将“生活本身在说话”的艺术特色,发展和提高到成熟阶段,形成了陈登科特有的真善美相统一、直面人生与作家党性良知相统一的现实主义道路。
“生活本身在说话”从起步、形成到成熟,是与陈登科的个人生活经历及其个性本能密切相关的,也是伴随着他的文学实践而逐步走过来的。
陈登科于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上营村的农民家庭。12岁时,靠母亲为塾师洗衣而进私塾读了两季。但因“愚钝”且顽皮,被先生视为“只能放猪,不能读书”而逐出学门,从此便在家里务农,又因父亲早故,15岁便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1940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涟水、阜宁、淮安、盐东等地参加抗日游击活动,当过警卫员、侦察员、通信员等,他杀敌英勇,斗志顽强,手刃伪军、匪军多人,且在上级的关怀和帮助下,刻苦学习文化,逐渐掌握了写信、写日记、写墙报稿的基本要领。1944年秋,他在《盐阜大众》报上发表了第一篇通讯稿,题目是《鬼子抓壮丁》,内容是记述游击队小队与日寇一次遭遇战情况,此稿共60多字,其中的错别字竟有20多个,经编辑钱毅校订修改发表。从此陈与钱毅交上了朋友,并由此产生了写稿热情。以此为起点,陈登科开始了新闻写作,在1945年1月5日至4月5日期内,他为《盐阜大众》通讯员活动中写稿29篇,发表23篇,被评为盐阜区特等模范通讯员,并被该报聘为“特约工农记者”。同年7月,正式调入《盐阜大众》任工农记者,委派钱毅同志在思想、学习和写作上对他进行辅导与帮助,使他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得以日益提高。在此后的5年左右时间里,陈登科连续发表了数百篇通讯报道以及战地小故事。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也锻炼了写作能力,且在不知觉中培养起一种生活本身在说话的写作路子。1947年5月份,他发表了第一篇报告文学《铁骨头》,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1948年冬出版了第一篇中篇小说《杜大嫂》,成为开创他的小说创作的起点,1950年《活人塘》的问世,则标志着陈登科正式步入了新中国第一代优秀工农作家群体,并以这部小说显示了陈登科身上蕴藏的文学潜能和非凡的毅力。
《活人塘》的成功,使陈登科有机会被送入由著名作家丁玲主持的培养中青年作家的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今为鲁迅文学院)学习和深造,在两年多的时日里,陈登科受到了关于文学史、文学基础理论、中国和世界文学名家名著选讲、作家修养、创作方法与技巧等方面的系统性培训,尽管他的基础文化理论不高,但他以加倍的刻苦和虚心,很好地完成了学业,使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素养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并在就学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最后定稿,于1953年在《人民文学》上全文连载发表。这是陈登科第一次驾驭长篇,其情节和人物都超过了《活人塘》规模,特别是由于人物较多,战斗场面又要一个接一个,要避免模式化和雷同化,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作品所描写的内容都是陈登科所亲历过的生活情景,其人物也都是他十分熟悉的战友和亲人,因此他仍能运用“生活本身在说话”的叙述方法,将故事和人物都写得真真切切而又鲜活生动,比之《活人塘》,它在更广阔、更复杂的背景下,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一段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的历史斗争。作家怀着强烈的爱憎,朴素地描写了那场斗争的严酷、惨烈和悲壮,以昂扬的崇高感赞誉着李振刚等英雄人物,又以强烈的仇视和蔑视之笔,描写了敌人的血淋淋的残暴和叛徒的可耻堕落。这部小说发表后丁玲曾在54年2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给陈登科的信》,指出作品“有生活,真实,能感动人,使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使人对书中的故事和人发生感情。因此这是一部有内容的结实的作品。”另一方面,丁玲也指出“人物毕竟还没有立体地显示出来,人物本身行动少,而由你讲述得多,你越用力就感到你缺少办法,……你笔下的战斗打得局促,打得不精彩,而且使人疲乏。”丁玲在分析其原因时又指出“你看见一些山,一些水,但由于你的修养,这些山水在你脑中还不能成为‘丘壑,你还缺乏一种天然的创造,也就是说你的创作还有些勉强,还不成熟。”此外,丁玲还要求他在原来的生活上,要有“新的提高,而且应当是相当大的距离的提高。”丁玲的信只有两千多字,但她以成熟作家的眼力和真知,看准了陈登科创作上的优势的弱势,堪称对症下药地向陈登科发出了切实而有益的忠告。从《活人塘》到《淮河边上的儿女》,表明陈登科的“生活本身在说话”仍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自在状态,他一方能够再现生活的本原面貌,另方面又缺欠艺术上的提炼和再创造,故难免有堆积素材之嫌。
讲习所学习结业以后,陈登科从新闻单位转入文学界从事专业创作活动。由于他牢记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教导,回皖不久,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治淮大军的佛子岭水库工地。在现场,他担任一个工区的教导员,管理一百多民工,除参加日常实际工作外,还要从创作需要出发,走访各方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级专家等各路人才,使他的眼界从一贯关注农民和战士的角度,开始扩及到他原来不熟悉的工人和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随着生活视野的转变,陈登科的表现对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他写出了一系列描绘水利战线新人新事新风的散文、特写、小说,结集出版有《治淮的人们》、《春水集》和中篇小说《黑姑娘》等等。这些篇章既敏锐地反映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的风貌,同时也为陈登科积累下了大量新的文学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长篇小说《移山记》的构思。
《移山记》是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是陈登科的第一部规模最宏大的长篇小说,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宏观描写水利建设中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表现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历程及英雄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作为第一次涉及工业题材和工人及中高级知识分子生活领域的作家来说,陈登科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他虽然已在工地生活多年,对周边的各色人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和了解,但他毕竟是从泥土走来在战火中锤炼的具有典型农民性格的人,他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一些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工人,自然容易把握,但对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及高层管理人员的思想状态和感情世界的了解和把握,便难以达到非常深入的境界,不可能再像他写《淮河边上的儿女》时所说的那样:“那些人(指书中人物)吐出一口唾沫是什么样的动作我都清清楚楚。”再加上从宏观角度表现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涉及的矛盾、斗争也远比从一支游击队角度写战斗故事要复杂得多,因而在生活体验和创作过程中,必须多观察、多思考、多琢磨、多费心思地去刻画他们的性格,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在结构故事时,还要顾及工程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建设路线上的、思想上的、方法上的、人际关系上的以及敌我与人民内部之间的多重矛盾相互交错的实际情况,疏理好中轴主线与横竖支线的关系,再现人在改造大自然过程中改造自我的宏伟图景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尽管摆在陈登科面前的新课题和难点很多,但他仍以当年学文化、学写新闻稿的顽强毅力,以全身心地投入和在实践中学习的劲头,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多方面地接触人,深入探索各色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日常的观察和思考中,积累起众多人物形象,经过反复构思,反复结构,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终于啃下了这一块硬骨头,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新中国第一项伟大治水工程的长篇小说——象征着中国人民用智慧和力量,进行移山填海的《移山记》。
《移山记》的问世,表明陈登科追求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和驾驭长篇巨制的努力是应予肯定的。在作品中,他塑造了袁久皋、常云翔、江海峰、杨熙等一系列有个性、有特点、有情趣的人物形象,并在展现他们与大自然搏斗的同时,也展现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自己的灵魂搏斗历程。值得注意的是,陈登科在把握和处理这一规模宏伟的素材时,敢于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敢于正面表现工地上出现的闹事风潮,并在妥善处理事件的过程中,有力地表现了常云翔那样的高层领导干部的智慧和魄力,也批评了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揭露了暗藏敌人的挑拨。应当说,这种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生活的态度,是陈登科继续坚持“生活本身在说话”叙述方式的延伸。但由于受到历史思潮和当时流行的文艺观念的限制,另有作家本人才力尚未达到应有高度,驾驭大型长篇尚力不从心,使得《移山记》有图解政策和人物标签化痕迹,也有结构不严、松散拖沓和对高级知识分子心态缺少理解等等弊端。
《移山记》写于1956年出版于1958年。这期间中国文坛发生了一场空前浩大的政治运动。陈登科因与丁玲师生情谊深切,加之他的某些短篇小说受到公开批评,险些被纳入右派罗网。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是因周扬替他说情,以保护工农作家名义,得以宽大处理免于加冠。但未加冠不等于过了关。随着无休止的批判和检讨,随着身边的一批文友被打成右派,纷纷被送去劳改或劳教,他一方面茫然不知所措,另方面又要自觉地感谢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故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回到党的怀抱里来》的表态文章,而在58年的大跃进日子里,他又会同几位作家并领衔发出《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取消稿费)的呼唤,成了中国文艺界第一批向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宣战的“斗士”。与此同时,他又在大跃进声浪的催逼下,写出歌颂大跃进的《卧龙湖》(与鲁彦周合作)、《柳湖新颂》等电影文学剧本和一些散文与短篇小说,为大跃进泡沫撤了一点彩粉。应当说,粉饰生活、讴歌浮夸、颂扬“五风”等等,是与陈登科真正的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但一来是当时的风气使人们大都不自觉地跟着瞎起哄,二来也是陈登科以负疚的心情在创作上显示一下他在政治上的悔悟之态。那时,有人以个人意志可以改变客观规律为信念,创造了大跃进神话,但客观规律本身是不好违背的,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却并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你硬要违背它,它就发了个大脾气,很快,大跃进就变成了大灾害。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建设停顿了,生产停滞了,田园荒芜
了,老百姓吃不饱了,仅在安徽大地就有几百万人拿生命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交了学费。党和政府为了扼制此种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决定派出大量工作队赶赴农村基层开展整社工作,陈登科也奉命领导一个工作队,去淮北某地参与此项工作。工作重点是在基层整顿干部作风,整顿因“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高征购风)所造成的严重后遗症,抢救农民健康,逐步恢复生产,查处少数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等等。当时的工作条件极端艰苦,工作队也面临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且各种问题繁多,事事棘手,既要想法让农民有食物入肚,又要医治那些因饥饿而造成的种种病状,还要打点生产自救,恢复农村生机等事项,可谓难而又难。但陈登科凭着共产党员的良知,凭着他对农民的天然的关爱情怀,他率领的工作队,认真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体察党的良苦用心,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妥善地扭转了危机局面,使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恢复,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农村面貌得到了某些改变。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段经历,是因为这段经历不仅是陈登科的工作经历,而且也与他的文学经历以及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段经历使他从盲目跟风写作的境地走出来,使他再次回到了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关怀人民的命运的正确轨道,并且为他彻底修改《寻父记》(初稿名《樱桃园》、后改为《寻父记》,出版时更名《风雷》)积累了最鲜活的素材,也提供了变更主题,变更中心情节、变更切入点的新颖构思。这期间他曾经陆续发表了《写不完的日记》、《百岁图》、《三省庄的一段插曲》、《短篇三题》等短篇。这些作品一扫早年的热情有余而深沉不足和跃进期的虚浮痕迹,显示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在短小的篇幅里,融进了作家关心人、爱护人以及尊重农民自主意识的呼唤。
《风雷》的原始初稿始于1958年。但那时只完成了17章,60年下乡工作后就没有继续写下去,62年返回原单位后,他把在整社工作中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观察、体验、思考、感悟以及各色人物形象的积累,作为重新改写这部作品的立足点,以主人公祝永康寻父为线索,将改造落后乡所面临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曲折复杂斗争,全面铺展开来,形成展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历程的立体画卷,生动而逼真地记载下那一历史时刻中国农民为改变自己命运所付出的汗水、泪水、智慧和苦搏,刻画出祝永康、陆素云、熊彬、羊秀英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富有典型意义且饱含内心隐秘的人物形象。陈登科再一次回归到“生活本身在说话”的创作境界,突破了描写农村题材作品中常见的图解政策、人物分属阶级标签或成份符号的观念化、模式化的框架,而是将生活本身的纷繁景象,将变动着阶级关系、社会思潮和多种多样的农民心态,都做出了维妙维肖的逼真描写,形成了一部全景式的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淮北地域的民风、民俗、民性、民情、民心、民气的长幅画卷,令读者对那个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在身临其境中,产生真切的感受和认知。《风雷》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塑造了一个被权力和私欲异化了的腐败分子区委书记熊彬的形象。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非符号化、非脸谱化的真实而可信的腐败分子典型,在当时的文学界曾引起很大的震撼和争议。尽管陈登科这部作品是回归“生活本身在说话”的基本叙述方式,但此次回归,乃是陈登科的文学生涯走向成熟、走向创作自觉的飞跃。此时的“生活本身在说话”,已不再是《活人塘》时那样的简单地复制生活原貌的自在状态,而是自觉地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以直面人生、再现真实为圭臬,以创造典型为宗旨,以表达农民心声为己任,以求索改变农民生存环境为理想,以追求上乘的艺术表达为目标,基本上体现了思想、内容与技巧较为完美的融合。使陈登科的“生活本身在说话”,从初级阶段上升到成熟阶段,使他从此不再仅仅被人们视为欠缺文化修养的工农作家,而是当代文坛中的一位有胆、有识、有为、有才的成熟作家。
《风雷》的创作过程正是陈登科追求自我超越并实现了自我超越的过程。从初稿到定稿,历时五年有余,63年完稿时定名为《寻父记》,在朋友、同行、编辑间多次征求意见后,又进行了数十次较大幅度的增删、修改和润饰。可以说陈登科为这部作品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空前的。他为了写出真实,写出当时农村面临的内外交错种种矛盾,写出个性独异的人物,他显示了一个党员作家应有的勇气、胆略和良知,他以入骨之笔刻画了熊彬,又以绝妙之笔塑造了杨秀英,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陆素云,复以史鉴之笔书写了祝永康的寻父情结实为改变农民命运的求索情怀。另外,作者对地域风情的描绘和语言的运用,也都做到了刻意琢磨,精益求精,力求传神。
《风雷》出版以后,在创作界、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在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里,发行量达百万册以上,不少四清工作队把它作为认识农村、了解农村的必读书,人手一册。《文学评论》杂志于1965年第4和第6两期,连续发表论文对《风雷》的成就和不足展开了深入的评析和认真的探讨。
当然,由于历史思潮的局限,《风雷》在思想和艺术上也的确存在某些不足和缺憾,比如作品把阶级斗争特别是敌我矛盾描写得有些过分严重或者失之于牵强,有些人物仍有符号化痕迹,对某些人和事的认识,尚有受当时左倾思想影响的偏颇。尽管如此,《风雷》仍不失为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题材长篇著作中颇具独创性的力作,它提供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典型,至今仍富有魅力,它以“生活本身在说话”所展示的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至今仍富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作家在创作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心血、勇气、见识和才力,也都可以使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留有一席地位。
不幸的是,《风雷》的成功,不仅没有给陈登科带来好运,相反却使他遭劫受难,蒙受了五年牢狱之苦,身心倍受摧残。在十年动乱期,江青公开点名诬指曾与国民党军队血战数年并手刃敌人多名的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是“黑手”;他的《风雷》则被定性为“特务文学”,“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复辟资本主义黑碑”。由于《风雷》在广大公众中具有深厚影响,“四人帮”为了把它“批倒批臭”,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起多次规模宏大、声势浩大的批《风雷》运动,除见诸于大报小报的胡言乱语的所谓大批判外,省内还组织一个专门从事批《风雷》工作的专业写作班子,耗时经年,抛出署名安学江的《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的大批判“杰作”,于1968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新安徽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所加的编者按语中的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这篇大批判的重点,说什么“《风雷》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它披着‘写农业合作化的外
衣,大刮反革命的黑‘风,大打资本主义妖‘雷,穷凶极恶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肆无忌惮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在这以后,《新安徽报》又以两篇社论、十个版的文章和报道进行了旷日持久地批《风雷》活动,省革委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全省广播大会,让全省人民都来听省革委会领导人的批《风雷》的报告和一片嘈杂的批判与表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围剿《风雷》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气焰之烈、帽子之多,参与之众实为文坛罕见、历史罕见。
但牢狱之灾和大批判唾沫都不可能消解陈登科对党的忠诚和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尽管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病状,甚至下达过三次“病危通知”,他依然铁骨铮铮,坦然面对牢狱生活,甚至用铁钉在狱中墙上刻下“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的诗句,以表明他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心态。在狱中,他先后构思了《不废江河》、《颂歌声中》、《烽火大地》、《破壁记》等四部长篇小说,并着手写了《不废江河》的提纲和回目设计。因此在他出狱不久,便很快完成了这部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并定名为《赤龙与丹凤》。
粉碎“四人帮”后,陈登科已步入花甲之年,且体弱多病,心力交瘁。但他在精神上、气质上、思想解放的前卫性上,却都显示青春焕发、朝气蓬勃之势,不仅积极参与政界、文艺界、社会各界的各种活动,且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对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邓小平重要讲话的竭诚拥护,理直气壮地与“两个凡是”观点以及“四人帮”极左思潮余毒进行针对锋相对的斗争,而且创作精力上也显示出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活跃态势。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回忆录、报告文学、文艺思潮见解外,他还相继完成了《赤龙与丹凤》、《破壁记》(与肖马合作)、《三舍本传》、《暴尸滩》等四部共150多万字长篇巨著。其中,除《暴尸滩》(实为《三舍本传1》下集)系已完成之手稿,其他则均已公开出版。此外,他还与鲁彦周、肖马、韩瀚等人合作有电影文学剧本《柳暗花明》、《淝水大战》、《徐悲鸿》等多部。就陈登科的小说世界而言,《赤龙与丹凤》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农民革命斗争悲壮历史故事的;《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是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移山记》是描绘建国初期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宏伟面貌的;《风雷》、《三舍本传》是表现中国农村改造之路的;《破壁记》则是揭露“四人帮”制造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和呼唤改革开放的。可以说,陈登科是为中国社会变革历程书写了它的方方面面,书写了中国人民在这一历程中的奋斗史和心灵史。他把自己毕生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都献给了他的小说世界,同样他也是在小说世界里咀嚼着自己的人生体察。其间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两部作品是《风雷》和《三舍本传》。这是因为陈登科最关注的题材是农村,他最关爱的对象是农民,他最善于描写的人物是农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的语言是农民口语,他的民俗情趣也重在农村,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直把关注农民命运的变化视为自己的永久性主题。《赤龙与丹凤》是寻求农民革命的路;《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是寻求农民解放的路;《风雷》、《三舍本传》则是寻求农民发展的路。如果说《风雷》写作时,陈登科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政治思潮和政策影响的话,写《三舍本传》时的陈登科,已经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年代农村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三舍本传》便能更好地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更真切地表达作家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思考与叩问。《三舍本传》虽然在题材和立意上和《风雷》形同姐妹篇,而且也是以淮北农村为背景,把小镇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纳入到一个共生的生存环境里,但作家此刻已没有了左顾右盼的疑虑,没有原有的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对文学的非文学干涉,能够更加自如地把“生活本身在说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写活了姣姣、五斗、三舍等一大批人物形象,妙趣横生的生活情景,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情景,叫人怒不可扼的生活情景,时不时地把读者引入其境。让你和作家和书中人物一起品味生活本身的苦辣酸甜。《三舍本传》几乎是陈登科笔下的农村社会百科全书,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贤愚良莠,个个扮演着历史赋予他的角色,且鲜活生动无比。可惜,由于作家没有来得及对作品进行深度加工,没有像对《风雷》那样反反复复的打磨、修饰、润色,故而显得粗糙一些,某些人物交待得不清楚,某些细节尚有漏洞,个别场面写得有些过于直露。但不管怎么说,《风雷》和《三舍本传》既是标志陈登科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体现陈登科关怀农民命运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的代表作。陈登科的心在农民一边,陈登科关注农民的心也在这两部书里。
陈登科以不自觉地应用“生活本身在说话”开始了文学生涯,又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提升和完善了这种叙述方式。它的成熟过程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在陈登科的小说世界里完满体现的过程。它要求真实,真诚,真切,以真诚的话语表达人民的心声,以真挚的情感关怀人民的生存际遇,以真知来诉说作家的思考,以真心来回报养育他的人民和培育他的党。
陈登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真字。
陈登科的“生活本身在说话”也是一个真字。
责任编辑鲁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