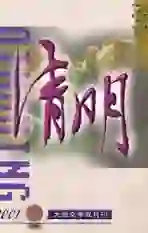洞房花烛
2001-03-31傅爱毛
傅爱毛
(1)
山里的庄户人家把闺女出嫁叫作“出门子”。豆苗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出门子的日子说来就来了。日子定在农历年底的腊月二十六。满打满算也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了。
豆苗一边悄悄地做着该做的准备,一边想着远在天边的“那个人”。“那个人”叫王石根,在西藏当兵。要回家一趟,单是在路上就得花费半个月的工夫。回到家里就像是掏火儿一样,屁股还没坐稳板凳呢,就又该往回赶了。因此,每一趟回来都紧赶着把该办的事情办了,一点都不敢拖泥带水地耽误工夫。
前年里头一趟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见了第一面儿。去年第二趟回来就算是正式定了婚。今年这第三趟,说成亲就要成亲了。豆苗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呢。两家里原本没打算这么快就办事的。可是,王石根他娘半年前突然得紧病死了。家里缺少个女人操持,日子难将就。王家就想叫豆苗早些过门子去,里外好有个帮手。
媒人来商量的时候,豆苗她爹一口就应承下来了。爹应承下来了,豆苗就没再说什么。豆苗想:面也见过了,亲事也定下了,两个人的年岁也不小了,过去就过去吧。作闺女的,早晚都是人家的人。现在,人家死了娘,正是用着人的时候,自己要是强拗着不过去,往后人家就要低看自己了。于是,豆苗就点了头。
点了头以后,心里却空荡荡的,没来由地不踏实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刚刚拿起了针线,泪珠子就叭嗒叭嗒地掉下来了。她是哭她娘呢。她娘死了好些年了。她边哭边在心里说:王石根啊王石根,你是个没娘的娃子,俺是个没娘的闺女。咱俩的命一般苦呢。要是有个娘活着,哪里要这般作难呢?
说到作难,其实也没啥多难的事情。需要她亲自料理的也就是出门子穿的一身红衣裳。别的还要做什么呢?豆苗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却忍不住还是要想。越想脑子里越乱,越乱就越要理出个头绪来。于是,想起来就没个头尾了。
当然,想过来想过去的,都离不了那王家的后生王石根。
(2)
跟那王家后生头一次见面是在前年的春上。
豆苗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一。天上下着星星点点的小雨儿。王石根就是冒着小雨儿来她家相亲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媒人四婶子。
吃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的坐着,却谁都不抬头,谁都不说话。直到吃完了饭,她把一碗鸡蛋茶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时,他才抬起头来偷偷看了她一眼。她也大着胆子看了他一眼。两人目光相遇的工夫,他朝她笑了一下,她也朝他笑了一下。笑了一下以后,两个人的脸就都红了。她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话,一时却又找不出来,便又窘迫又着急的,出了一脸的汗。他看出了她的窘迫和着急,想安慰她一句什么,也没想出来,于是便比她更窘迫更着急了。最后,两个人到底还是一句话都没说。不过,那一看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打过招呼,相亲的仪式就算是结束了。山里头相亲都是这规程。
后来,四婶子给豆苗送过话来说:“他没意见,只看你了。”其实,四婶子不捎话过来,豆苗心里也有底儿。她也不知道凭什么,却笃定地相信,那王家后生一准是相中她了。当然,她也相中那王家后生了。她觉得,那王家后生当时就猜出她的意思来了。
一想到那王家后生看破了她的心思,她就有点生气。她在心里骂自己:豆苗啊豆苗,你咋就这般没出息呢?看了人家一眼就相中人家了,你贱不贱?心里虽是这么骂,嘴上还是半推半就地说:“他既然没意见,俺会有啥意见呢?”四婶子趁势说:“你没意见,那就是愿意了。我可捎话过去了啊。人家后生要回部队,只等你一句话了。”
四婶子把话递过去,那王家后生带了这句话就往部队上走了。一走就是整整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豆苗的眼前晃动的都是那王家后生的一张笑脸。那笑脸又羞涩、又腼腆,跟个姑娘家似的,让人一看就疼到心里头去了,想薅都薅不出来。
抬头看天时,他浮在天上朝她笑;低头看地时,他站在地上朝她笑。上山采茶时,他藏在茶树丛里朝她笑;到潭里洗衣服时,他又站在潭水里朝她笑。见他整天地对着自己笑,豆苗就装作生气了。悄悄地说道:笑什么呢笑?俺早已就看够了,也看烦了。俺不想再看了呢。豆苗在心里这么说着,便拣起一颗小石子来投到了潭里去。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他的笑脸便不见了。可是,刚刚转个眼儿的工夫,他又站在眼前朝她笑呢。豆苗便无可奈何地也笑了起来。痴痴地笑了半天,衣服都顺着潭水漂走了,她才灵醒过来。急急地把衣服捞上来,骂一句“冤家哎!”才端起洗衣盆子回家去了。
(3)
两个人第二次见面,就到了第二年年底。
这一次媒人四婶子没有来。他自个来的。来了以后,一家子围坐在一起,人多嘴杂的,他们也没能说上体己话。直到临走的时候,豆苗送他到村口,他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纱巾来递给她,说:“天冷,你围上吧。别冻坏了身子。”还没人给豆苗买过东西呢,连针头线脑都没有买过。豆苗把纱巾捏在手上,心里就腾起了一团软软的雾,浑身上下都暖融融的。她也给他准备了礼物,是一双自己亲手做的千层底儿布鞋。他把鞋拿在手上,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看不够的样子。
她手里捏着条纱巾,他手里握着双布鞋。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路宽的时候,他们便一左一右;路窄的时候,他们便一前一后。豆苗的心窝子里攒着一年的话,拢到一起能有一大萝筐。一大萝筐的话搅成了团往外涌,便一句都说不出来了。心里的话堵着说不出来,眼里的泪却是憋不住往外淌了。
豆苗不想让那后生看见自己流泪。心想,好端端的,哭什么呢。于是,流出一颗她便偷偷地抹掉一颗。抹掉一颗却又流出一颗来。抹得急流得快,这样只顾着流泪抹泪,那心里的话就更没工夫说出来了。说不出来就不说了,只埋着头往前走。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村口的槐树林边。穿过了槐树林,离那个人家里就不远了。槐树林密密匝匝的,人进去就没有了踪影。平日里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男女才往里钻呢。豆苗没再往前走,在槐树林旁站住了。豆苗站住了,那个人就也站住了。两个人都站住以后,就觉出不自在来了。孤男寡女的,站在密匝匝的树林旁,怪惹眼的。站了一会,豆苗便说:“你走吧,天不早了呢。”那个人点点头,就踏着林间小道一步一步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豆苗说:“你在家好好等着我。别太累着自己了。你身子骨单薄,得自己顾惜自己,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豆苗点点头,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却鼻子酸酸的,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了。
豆苗从小就是个没娘疼的孩子,这世界上没谁对她说出过这么贴心贴肺的话。那王家后生把话说出来,便一下子触到了她的痛处。这一痛便整整又是一年。想不到的是,一年到头,竟是要出门子了。
(4)
一想到要出门子,豆苗便直犯愁。愁得
眉毛头子拧成了疙瘩。不愁王家的日子苦,也不愁山里的活路累。愁什么呢?豆苗说不出来。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愁只愁那洞房花烛夜呢。
豆苗是个真正的女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有哪个男人碰过她呢。连头发梢子都没有被哪个男人摸过。现在,突然间就要跟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同床共枕作夫妻了,怎么能不发愁呢?她愁得不敢拿这件事往细处想,一想就耳热心跳,满脸发烧。跟做了贼似的。
她明白,女孩子家,都要过这一关。早不过晚过,左右是躲不过去的。除非一辈子不嫁人。可是,作女孩的,又哪能不嫁人呢?她对自己说:别想了豆苗。到时候说过去就过去了。村里的姐妹们不是一个一个都过去了吗?可是,她越是这样劝自己,就偏偏越要想这件事情。她简直拿自己没法子了。便骂自己道:豆苗啊豆苗,你羞不羞啊?亏你还是个闺女家呢。
出门的日子越近,她越害怕。怕得不敢往人前站,更不敢跟人搭话。她觉得每一个人都看出她的心思来了。尤其是嫂子。嫂子一见了她就抿着嘴儿笑,笑得不怀好意。她吓得不敢去看嫂子的眼睛。她不看嫂子,嫂子却追着一个劲儿地看她。到后来,她只得像老鼠躲猫一样,一天到晚把自己藏在小屋里头不出来。出了屋门,即使不见人她也脸红,跟刚刚生了蛋的小母鸡一样。
好在日了一天一天地临近了。她想,熬过了出门的那一天就好了。出了门,她就成了王家媳妇。拉下脸儿来作了王家的媳妇,她就不害怕了。
一个月的光景说过去就过去了,作王家媳妇的那一天终于近在眼前了。
(5)
到了腊月二十六这一天,一切就全由着别人摆布了。
她像个木偶人似的,婶子大娘们让她怎么着,她便怎么着。晕晕乎乎地穿上那身红衣裳,晕晕乎乎地被一群人簇拥着上路,晕晕乎乎地就坐在了王家布置好的洞房里。
“洞房”是一问土坯子小屋,虽然简陋,却也干净整洁。屋里放着一张宽大的木床。床上的被褥簇新簇新的,弥散着棉花的香味。床头上并排摆着两只绣花枕头,枕头上绣着戏水的鸳鸯。看着两只枕头,豆苗的心就砰砰地跳了起来。脸颊也火一样地发烧,用手摸一摸,烫得吓人。她就不敢再看那两只枕头了。她把身子扭过来,背对了它们坐着。
屋子里挤满了人。男的女的,婶子大娘,还有半大的孩子。他们不论老少,都一律地叫她“嫂子”。她一个闺女家,突然间就平白无故地成了“嫂子”,一时之间她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却也没法子。这个叫一声,那个叫一声,嫂子长嫂子短的,还说一些叫人不好意思的话,羞得她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才好。有两个半大的后生,把那个人也拽进来了。她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过那个人了。当这么多人的面儿,她也不敢大着胆子抬头去看他。只偷偷地瞅空儿乜斜了他一眼,见他还是一脸腼腆的微笑,跟个闺女家似的,她心里头就有了几分不落忍。那几个人却不管这些,他们一齐动手,把两个人硬往一块堆凑。虽然他们两个都拚命地挣扎反抗,无奈后生们人多力量大,到底让他们给撺掇到一起了。她又是羞又是气,却不敢恼,就急得哭了起来。哭了他们也不放过她,又折腾了好一阵子才罢休。
夜幕慢慢地降临了。热闹了整整一天的院子,渐渐地沉寂了下来。按山里的规程,闹过了洞房以后,女人和孩子们该回家的回家,男人们则要留下来陪新郎喝喜夜酒。那个人在部队是个连长,在寨子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了,来喝酒的人就特别多。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是叔伯还是兄弟,人家端一杯,新郎就要陪着喝一杯。喝来喝去的就没个早晚了。不过,在山里人看来,来的人越多、喝的时间越长,才越好呢。
(6)
在男人们喝着酒的当口,婶子大娘们陆陆续续地领着孩子走了。小屋里只剩下了豆苗一个人。起先的时候她坐在床沿边,把身子斜靠在桌子角上。这么坐了一阵子,她就觉出不妥贴来了。心想:若是那个人进来了,看见她这么坐着,会以为她是在等他回来呢。“我才不等他呢。等他作什么?”
豆苗心里这么说着,便换了个比较随意的姿势坐了。屋子里没有钟,她也不知道是啥时间了。只觉得已经坐了好久好久了。这么晚了却不睡觉,直愣愣地坐着,不是在等那个人又是在干什么呢?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在等,豆苗就吓了一大跳。吓了一大跳以后,就不敢再等了。她对自己说:该睡就睡,等什么呢?天不早了呢。那个人就是喝到天亮也不关你的事。
一想到要睡觉,她就又发起愁来了。屋子里只有两只枕头一张床,自己怎么睡呢?她一个闺女家,自己主动睡到男人的床上去,总归是不大好的吧?
想到这里,豆苗“噌”地一声就站起身来,不在那张床上坐了。屋子里地方不大,不坐在床上,她就得站在桌子前。桌子正对着窗户。她站起来,自己的身影就映在窗户上了。她想,要是有人在院子里朝窗户望一眼,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身影了。人家看见她站在窗子前,会以为她是在翘首盼望着那个人回屋里来呢,这比坐在床上还要不妥。这样一想,她便又在床沿上坐下了。坐了一会,就觉得困意慢慢地袭来了。好些日子她都没能好好地睡过踏实觉了,那困意一来就像粘在了身上,赶也赶不走了。她打了个哈欠,对自己说:困了就睡吧。管他呢。进了王家的门,就是王家的人了。
这样对自己说着,她便和衣在床上躺了下来。
(7)
人躺下了,眼睛也闭上了,两只耳朵却是一直都醒着。院子里稍有风吹草动,她都听得一清二楚。每一次院子里有脚步声响起,她的心都揪成一团,狂跳不止,像擂一只小鼓似的。可是,每一次都是一场虚惊,那脚步声响着响着就响到别处去了。她长长地舒上一口气,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望,然后又屏声静气地听着院子里的动静。就这么一惊一怍的,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忽然听得堂屋门吱呀一声响,一群人说着笑着迈着杂踏的步子走出院门去了。她知道,那酒席终于散场。最后一拨客人走掉了。
她急忙紧闭了双眼,把头侧向墙壁躺着,装着睡熟了的样子。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响到小屋里来了。她知道,是那个人。
一想到那个人就要进来了,她全身立时僵成了一条棍子。心脏也几乎停止了跳动。只有耳朵还活着。她听见那个人一步一步地进了屋。然后“叭嗒”一声把门闩死了。随着那“叭嗒”一声响,她全身的血就凝固不流了。她知道,这时辰,屋里就只剩下他和她两个人了。她像是大难临头了一般,紧闭了双眼躺着,一动都不敢动,仿佛只要她稍微动弹一下,立刻就会天塌地陷一般。
那个人进来以后,便把身子伏在床上轻轻地唤道:“豆苗,豆苗。”豆苗没吭声,装作睡熟了。鼻子里竭力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两只手里却湿浸浸地捏出汗来了。那个人见豆苗睡着了,便脱了外衣上得床来,轻轻地偎在豆苗的身边,动手解起豆苗的纽扣来。豆苗不能再装睡了,伸出手来抵挡,却是挡不住。挡
不住就不挡了,听任那个人一颗一颗地解开了她的纽扣。把外衣脱下来以后,豆苗却无论如何不让那个人动她的秋衣秋裤了。于是,两个人都穿着贴身的衣裤那么躺下了。
躺下以后,豆苗尽量把身子往一边偏,竭力不去挨近那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人也拘谨地躺着,不去挨豆苗。过了一会儿,却不动声色地向豆苗靠近了一点点,豆苗发觉了,装着无意的样子,赶紧往旁边挪了一点。豆苗往边上挪一点,他便悄悄地向她靠近一点。却又不敢靠得太近,怕冒然造次了会惹豆苗生气。豆苗把身子挪得不能再挪以后,那个人便慢慢地偎上去,伸手把豆苗揽进了怀里。
那个人的怀抱又踏实又温暖,散发着男人特有的体香味。豆苗的头一靠上去,就像是船儿靠了岸一样,就再也不想抬起来了。她把脸紧紧地贴在那个人的怀里,听凭他摆布。那个人的身体里早已就烈焰熊熊了。他一边紧紧地搂着豆苗,一边不管不顾地亲吻起她来。先是亲她的头发,后是她的额头、她的眼睛、她的面颊、她的嘴唇。他的唇胶着在豆苗的唇上,像对着一朵盛开的蜜罐花儿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品咂着,如同一个馋嘴儿的孩子,没个完没个够。
豆苗长了这么大还不曾被人这么爱抚过。她浑身痉挛着,像一条蛇一样,紧紧地缠绕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腾出手来,在豆苗毫不防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把手伸进她的内衣里,在她的乳房上碰触了一下。豆苗只觉得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胸而过,浑身酥麻难忍,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我的亲娘啊!”就晕厥过去了。
看到豆苗呼吸停止,一动不动的模样,那个人一下子吓傻了。他伏起身来,一边按摩着豆苗的脖颈,一边低声而急切地喊着:“豆苗!豆苗!”喊过了几声以后,豆苗才慢慢地缓过气儿来,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的豆苗像大梦初醒那样,颤颤巍巍地贴着那个人的脸叫道:“石根哥,我的亲人!”这是两年多来,她头一次叫那个人的名字。刚一叫出口儿,滚烫的泪珠子就泉儿般涌了出来。一颗连一颗,赶趟儿似的,想止都止不住。石根见豆苗醒过来了,又是惊又是喜,一边唤着“豆苗,豆苗,我的心肝”,一边不停地用舌头舔着豆苗脸上的泪痕。
舔着舔着,石根浑身的血液就又燃烧起来了。每一根神经都如同一条火舌,每一条火舌都恨不得烧到豆苗的筋骨里去。但他却是怎么着都舍不得再招惹她的豆苗了。他狠下心,一条一条地掐灭那些滋滋往外冒着青烟的火舌,像水儿轻轻地漫过河岸那样,小心地把手抚在豆苗的身上,缓缓地爱抚着,摩挲着,玩味着,沉溺着。当他的手快要触到她的敏感区域时,他便轻轻地绕开。他不是不想。他实在是太心疼她的豆苗,怜惜她的豆苗了。他怕豆苗再一次痉挛和晕厥。他的手绕开了以后,却又不舍得离去,便久久地在周围回旋着,留恋着。仿佛一个馋嘴的孩子来到一棵樱桃树下,先把那些不太红的樱桃果一颗一颗地采来吃了,唯独留下树顶梢上最圆润,最光洁,最饱满,最鲜艳的几颗。他知道,那几颗的味道最美,吃起来最甜,因而他也最舍不得动手。他要把它们留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在他这么精精细细地爱抚下,豆苗便不知不觉地溶化在他的怀里了。她浑身的骨头先是一点一点地由硬变软,又由软变酥,由酥变碎,然后,一点一点地化成粉末,消失不见了。她的整个身子都变成了一条柔软的面团,随了石根的手伸缩着,变形着,漫延着,又弥散着。石根把她抚弄成什么形状,她便是什么形状。让她圆她便圆,要她方她便方。到最后,她就整个地把自己化成了一汪水,而石根就成了嘻戏在水中的鱼儿。
她在心里叫着:我的亲人啊,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啊,我的亲人!你把我吞进嘴里去吧。你把我咬烂了,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去吧。她心里这么喊着叫着,嘴里却一个字都说不成,一点声音都发不出。连呼出的气息都微弱得如同游丝了。她想:就让石根慢慢地游,漫漫地醉吧。她在岸边守着他。一生一世。地老天荒。
(8)
第二天一早,当石根和一家人起床的时候,豆苗已经把粥煮熟,菜热好,馍也熘出来了。石根刚吃完早饭,就被前庄一个人叫了去。说是拖拉机坏在了山道上,让石根去帮忙修理。石根没当兵时是个修车的好把式。二话没说就跟着去了。
石根去了以后,豆苗便在家里里外外地找活干。看见该洗的洗了,看见该刷的刷了。看见该拾掇的拾掇了,看见该摆落的摆落了。她简直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一分钟。只要闲下来一分钟她就要想石根。一想到石根,她的全身就会一阵痉挛、一阵麻酥,如同过电般,连气儿都出不匀活了。她觉得石根那双手还一直抚弄在她的身上。时而是头发上,时而是肩膀上。她想要把他的手拂开却是不能。于是,便只好不停地做活。只有手脚不停地忙活着的时候,她的念头才会稍稍地往别处转移一点点,心里也才会稍许平静一点。
好不容易挨到后晌的时候,她觉得这个白天已经太长太长。长得她快要忍耐不下去了。她认真地数了数,石根从早上吃了饭出门,已经将近十个钟点没有回家来了。这十个钟点漫长得如同十年,怎么熬都熬不到头的样子。左等右等,等得太阳花都枯了,黄昏才一点一点地走近来了。
那黄昏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走起来特别的迟缓。先是慢慢地爬到了西边的院墙头上,后又艰难地攀到了鸡窝的挡板上,最后才一寸一寸地挪到灶间的锅台边上来了。豆苗开始动手预备晚饭。她知道,石根快要回来了。山里的夜黑灯瞎火的,就是拖拉机没整治好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再修。一想到石根快要回来了,豆苗的脸便开始发烫。她已经打定了主意。今个晚上要把自己一股脑给了石根。她已经是王家的人了,她不想再让石根受煎熬了。再说,要不了几天,石根就该回部队上去了,她还想早一点替石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来呢。
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已经耳热心跳了。就在她耳热心跳的当口,她忽然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伴随着低沉的哭泣声,由远而近向大门口响过来了。她的头嗡地响了一下,预感到不对劲儿。她丢下手里的烧火棍子奔了出去,迎面就见一群人抬着个担架进来了。
石根死了。
石根修好了拖拉机,试着挂挡的时候,那拖拉机一下子就跌到了山崖下。石根被压在下面,当时就气绝身亡了。
人们把石根放在地上,开始在堂屋里搭草铺。
从始到终一句话不说、一滴泪不掉的豆苗像个魂魄一样,轻飘飘地走到堂屋里,扑嗵往地上一跪,说:“大爷叔伯们,老少爷儿们,我进王家门才一天,日子浅,这我知道。可我好歹是进来了。要是你们当我是石根的屋里人,就听我一句话,把石根放到我屋里吧。床我都铺好了。”
人们愣怔了一阵子,便随了豆苗的意思,把石根放进了新婚的洞房里。
床还是那张床,枕头还是那对枕头,被子也还是那床被子。石根还像前一天晚上那样,不声不响地躺在了婚床上。寨子里的后生们要留下来守石根,豆苗坚决地回绝了。她说:“石根睡了。你们也回去睡吧。天不早了。”
人们见她态度笃定,就去守着石根他爹去了。他爹还在村卫生所里躺着呢。
豆苗按步就班地收拾了灶台,喂了猪娃,堵上鸡窝,就回自己房里去了。回到房里,她就闩上门,放下了窗帘。然后,开始一件一件替石根脱衣裳。脱完衣裳以后,她拿热毛巾认真地替石根擦了身子。石根的身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外伤。把石根拾掇好了,她就上了床。上了床以后,她毫不犹豫就脱光了身上的衣裳,脱得一件不留,一丝不挂。然后,她就熄了灯,躺进石根的被窝里去了。
石根的身子很凉。他乖顺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像一个睡熟的孩子。豆苗说:“石根哥,我知道你累了。你不想说话。也不想动弹。那你就好好躺着吧。我来替你暖暖身子。”豆苗泪流不止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就把自己滚烫的身子结结实实、严丝合缝地贴到了石根的身上。在她的身子触到石根的身子的一瞬间,她大叫一声:“石根哥啊,我的亲人!”就晕厥过去了。
责任编辑张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