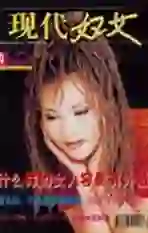家有洋亲
2000-06-13越声
越声
沈先生:韩国儿媳“宠坏”了儿子
去美国前,才知长子在美国娶了个韩国媳妇。
儿媳的英文名字叫June,比儿子年轻9岁,17岁时从汉城移民美国。她中等身材,漂亮和气而善解人意,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女性。
儿子不懂韩语,她也不懂汉语,两口子平时交谈用英语。韩国是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在这种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儿媳,依旧保留着固有的韩国传统。
第一次晚餐,我发现儿媳总在注意每人的饭碗,原来她在观察谁的饭即将吃完,随即一一替大家添饭,无一遗漏。开始我也入乡随俗,后来天天如此,我就婉拒了,作为长辈倒不是领受有愧,而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我,吃饭总是自己添,不太习惯儿媳这种盛情啊!
除了上班,她还承担了全部家务。洗涤烘干后的衣服她都要熨烫,连我的内衣都不例外,既快又好;不论吸尘清扫、切菜刀功均属上乘,好像曾受过家政服务专业训练似的。尽管都是东方人,但中韩两国的饮食文化总有不同吧!但她“嫁鸡随鸡”,一切按照中国的习惯。儿子从小爱吃红烧大排、红烧肉之类浓油赤酱的菜肴,儿媳均能适应。偶尔她去超市购买一瓶韩国风味泡菜,权当她的专利享受。
原来儿媳童年时,父母就离异了。按照韩国法律,她家五个子女全部判给男方。儿媳是长女,便义不容辞担当起持家之职,是环境铸就了她善于理家的本领。
我告诉儿子,不能对媳妇自愿赋予的大男子待遇心安理得。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也应该让媳妇感受到我们中国男女平等的优越性。
施先生:洋女婿爱吃中国菜
女儿去美国四年多,这次回国探亲,带回来一个当医生的洋女婿Gary。
Gary未来之前,着实让我们担心了一阵子:怕女婿初来中国生活起居会不习惯,可事实并非如此。
Gary不会说中国话,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但很会察言观色。刚进家门,我们没给他准备拖鞋,他见大家都换了拖鞋,于是一声不响地也脱下了皮鞋,穿着袜子在房内走来走去,叫他别这样,他的回答是:入乡随俗。
吃饭了,怕Gary用不来筷子,特意在他面前放了刀叉,可他嘴里在叨念着“chopsticks”(筷子),原来他要跟大家一样用筷子。虽然他用得并不顺手,但仍坚持在用,连吃汤团也用筷子。
洋女婿Gary仰慕中国的饮食文化,对美国式的中国菜也十分欣赏。女儿告诉他,美国的中国菜是走了味的,因而Gary对品尝真正的中国菜是向往已久。
我们带他去豫园“绿波廊”尝中国的小吃。当各色玲珑剔透的小吃端上桌后,他先是赞叹不绝地观赏着,然后嘴里品着“鸽蛋圆子”,眼睛盯着“眉毛酥”,一手又忙抓过“迷你小粽子”,不懂剥去粽箬直往嘴里送,边吃边翘起大拇指说:“Very good!”
品过“绿波廊”的小吃之后,又到湖心亭喝茶。Gary对湖心亭的建筑极感兴趣。服务小姐端上铁观音,他又目不转睛地专注着服务小姐倒茶的一招一式。等服务小姐一转身,他也拿起了紫砂茶壶,模仿着服务小姐的动作,像模像样地倒起茶来,并举起茶杯学着老茶客的样慢条斯理地品起茶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李女士:三弟媳玛丽塔
我的丈夫是德国人。丈夫的三弟媳是法国人,长得很矮,头发却长,像一挂金色的瀑布拖至腰下。她钢琴弹得实在太好了,但她是学农业工程的。她结婚那天,骄傲地指着身上的白色礼服说:“这是我自己缝的!”
去年夏天,三弟媳再一次地让我们对她刮目相看。他们买下了一个养猪场,整整两平方公里的场地里,除了四个巨大的机械化养猪棚,还圈养了六十多只鸭子,二十来头山羊和一匹黑色小马。猪棚里的四百多头母猪和一百多头小猪,见我们去参观都昂起头来嗷嗷地叫声震天。我们的三弟媳则把长发利索地在脑后绾起,一边陪我们吃饭,一边念叨着要去给刚满月的小公猪做阉割手术,对母猪进行人工授精。我吃惊地问:“这些都由你自己干?”她笑着说:“是啊,我是老板嘛。”她说每一头小猪都是她接生的。
夕阳下,她小小的身影正拥着两个孩子,一头耀眼的金发盖住了她大半个身子,玫瑰红绸衣映照着一脸灿烂的微笑。我禁不住产生了强烈的错觉,这个好像穿着水晶鞋的公主,怎么会骑在母猪身上给它们授精呢?
玛丽塔,你真行!
走“后门”娶来的妻子
在阿拉木图有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男主人是中国小伙,人称小贾。妻子是哈萨克姑娘,名叫里玛。
小贾30出头,来中亚做生意已有5个年头。
八年前,小贾计算机专业毕业,当时正值中国人闯东欧的风头上。小贾先在布达佩斯做事,后来到了莫斯科,最后落脚中亚。五年前,阿拉木图“羽绒服大战”如火如荼。小贾咬牙投资30万元人民币,从“浙江村”购入大批羽绒服,账算下来,利润“能翻个大跟头”,纯利至少50%。孰料,几周后,中国羽绒服已铺天盖地,当地人更领教了衣服中散发的难闻的鸡屎味。小贾亏了。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朴实善良的哈萨克姑娘里玛。
两颗属于不同国度的年轻的心,终于碰撞到一起。当时,哈萨克斯坦政府不允许中国公民娶哈族女性为妻。在司法部外国人婚姻登记处,通过400美元“走后门”和法律事务所朋友的帮忙,他们才领到结婚证。
聊起自己的哈萨克妻子,小贾言语间洋溢着骄傲之情,哈萨克女人比中国女人更能吃苦。里玛生完孩子头一个月,洗衣做饭,什么都干。她们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坐月子”。
虽然妻子贤惠能干,但小贾还是得不断适应“哈萨克斯坦国情”。哈萨克自古便是游牧民族,宗族观念极强。里玛的亲戚经常不请自来,在家又吃又住,弄得小贾哭笑不得。
随着我国与中亚各国人民往来的扩大,跨国婚姻愈来愈正常。但不少哈萨克人却将这一切视为中国“静悄悄的渗透”和“移民潮”。小贾告诉记者,一次经过阿拉山口海关,哈方边检员见他带着里玛回国探亲,调侃道:“你们中国人把我们的姑娘都娶走了,把我们的东西也拉走了……”里玛对记者表示:“中国男人对家庭有责任心,我父母对中国女婿很满意。”
向女士:说起洋婿眉开眼笑
五年前侄女在异国宣布要和美国青年史密斯成婚时,我们这个相对传统的家庭顿时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情绪中。
那年春节史密斯先生第一次登门。他个子不算高,一头褐色卷发。睁大了一双灰蓝色眼睛听夫人介绍家人。我同情地看着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面对着因春节聚会而人数倍增的异国亲戚,他礼貌认真,但显然力不从心。不过当他骑上自行车和岳父一块去逛南京路时,倒是显得非常快乐和兴趣盎然。
这位侄婿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法国移民,他的理想是当个医生。多年前在美国健康署工作时,曾因机构调整被“下岗”过;也曾放弃到哈佛大学任副教授的难得机会而受聘于一家公司。他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如果妻子允许他周日再去实验室忙碌,他会眨眨眼睛做出惊喜状,并眉开眼笑地问上一句:“真的?”然后乐颠颠地跑出门去。
“史先生”说他深感中国人是非常勤奋和聪明的。他还说其实许多美国人连本州都没离开过,他们不了解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因为一个只有200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读懂一个5000年古国的兴衰沧桑实属不易。
侄女婿总是布衣牛仔裤,简朴的生活并不妨碍他每年捐款给慈善事业。去年他听太太说她的表哥因肾移植要付巨额的医疗费用,就很痛快地表示要尽力资助。他的理由是:“支援非洲和救济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史先生”喜欢吃中国饭,但有时也拱手对夫人说:“求求你,吃顿西餐吧。”至于他的早饭是稠得可以立起来的无盐麦片粥,工作午餐是自制花生酱三明治,终年不弃不离。在谈起他们美丽健康的爱女时,史先生很郑重地对妻子说:“杰西卡6岁时,你要允许我们一起分享走进图书馆的快乐。”M
(责编 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