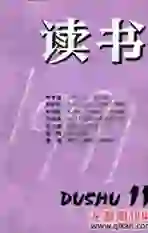从一个戏看两种莎剧中译
1991-07-15刘炳善
刘炳善
在我面前摆着海峡两岸所出的两种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一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朱生豪翻译、多人校补的《莎士比亚全集》;另一部是一九六七年出齐但直到最近才流传到大陆的梁实秋译《莎士比亚丛书》。这是我国翻译界、出版界至今所贡献给中国和世界读者的唯一的两部莎集全译本。这是我国两位老一代的翻译家,按照各自的翻译宗旨和翻译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两部莎译大作,代表了我国莎剧翻译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眼前正在读的一部莎剧是“Love'sLabour'sLost”,朱译本叫做《爱的徒劳》,梁译本叫做《空爱一场》。
说到《爱的徒劳》,以往批评家们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作家赫兹里特说得很干脆:“如果我们要把作者的喜剧舍弃任何一出,那么就是这一出了。”然而,这又毕竟是莎士比亚的“真经”(canon)。对它提出严厉批评的约翰生博士也得补充一句:“在全剧中散见许多天才的火花;任何一个剧本也不像它具有这么多的莎士比亚手笔的确切标记。”
对于翻译家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如果依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大概不会选上这个戏来发挥自己的翻译才能。但是,立下雄心壮志要翻译大作家全集的人,都逃避不了上天降给他的这么一种“大任”:他既要翻出作家的那些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作,也要翻出他在初学阶段的那些不甚成熟的作品;他既要翻出他在创作高潮时期灵思泉涌、逸兴湍飞的神来之笔,也要翻出他的天才“打瞌睡”的时候写下的那些平庸篇章甚至败笔,为的是给读者一个全貌。所以,莎翁全集的译者“别无选择”。他必须“背水一战”,使出浑身解数,把《爱的徒劳》翻出来:精采片断固然要尽力译好,平平之处也得认真对待。这个戏对于任何译者一律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取巧、“藏掖”之处。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看一看两位翻译家各自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个硬壳果”。
朱生豪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又酷爱英国诗歌,是一位天分极高的青年诗人。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条件下,他以身殉了自己热爱的译莎事业,为中国译出了三十一部莎剧。他在翻译中所追求的是莎翁的“神韵”和“意趣”,而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用通常的说法,他采用的方法是“意译”。
梁实秋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作为一位莎学家,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图书资料,逐字逐句精研莎氏原文,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终于在晚年完成了莎翁全集的翻译工程。他认为这是自己“所能做的最大的一项贡献”。从他亲友的记载中知道:梁先生译莎的宗旨在于“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他“需要存真”,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可以说是“直译”。
只要拿两种译本和“Love's Labour's Lost”原文对照一下,就可发现两位翻译家忠实贯彻了各自的翻译原则。
第一幕第一场162—169行(本文所引莎剧原文行数,除另有说明,均据新剑桥版)有一段那瓦尔国王的台词,介绍一个脾气古怪的西班牙贵族亚马多。开头八行原文是这样的:
King.Ay that there is,our court you know is hauntedWith a refined travellerofSpain——Amaninalltheworld'snewfashionplanted,Thathathamintofphrasesinhisbrain:OnewhothemusicofhisownvaintongueDothravishlikeenchantingharmony:Amanofcomplements,whomrightandwrongHavechoseasumpireoftheirmutiny.
王有的。你们知道宫里来了一位客人,
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高雅的游客;
此人集全世界的时髦服装于一身,
古怪的词藻装满了他的一脑壳;
他爱听他自己的放言高论,
就好像是沉醉于迷人的音乐;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是是非非都会凭他一言而决。(梁译本)
国王有,有。你们知道我们的宫廷里来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游客,他的身上包罗着全世界各地的奇腔异调,他的脑筋里收藏着取之不尽的古怪的辞句;从他自负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他自己听起来就像迷人的音乐一样使人沉醉;他是个富有才能、善于折衷是非的人。(朱译本)
从整个效果看,两种译本都把原文的内容传达出来了,但两种译文的风格又截然不同。梁译本的翻译原则是把原文中的“无韵诗”一律译成散文,而“原文中之押韵处则悉译为韵语”。因此,他将这段原文的五抑扬格,按ababcdcd押韵的台词,译成了格律相近的中文诗,译文严谨、质朴、细密,就韵文来说也流利可诵,舒徐婉转地描出了这个西班牙人的文雅而又古怪的性格。朱译本则更注意译文用语的艺术加工以增强效果。例如,“他的脑筋里收藏着取之不尽的古怪的辞句”和“从他自负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这两行,“取之不尽的古怪的”和“狂言”都属于译者的“艺增”,而“自负不凡的舌头”一语也较梁译“放言高论”更为形象生动。另外,对于“A man in all the world's new fashionplanted”一行,朱译本的“全世界各地的奇腔异调”较之梁译的“全世界的时髦服装”更能突出刻画这个“怪诞的西班牙人”的怪诞脾气。所以,这两小段的译文给人的印象是:朱译本的特点是不惜通过中文加工手段,以浓笔重彩强调人物性格,梁译本的特点则是尽量遵循原文,亦步亦趋,忠实而委婉地反映原文面貌、表达原文内容,效果更为细致。
朱生豪以诗人译诗,自是好手。他那华美
旭日不曾以如此温馨的蜜吻
给予蔷薇上晶莹的黎明清露,
有如你的慧眼以其灵辉耀映
那淋下在我颊上的深霄残雨;
皓月不曾以如此璀璨的光箭
穿过深海里透明澄沏的波心,
有如你的秀颜照射我的泪点,
一滴滴荡漾着你冰雪的精神。
每一颗泪珠是一辆小小的车,
载着你在我的悲哀之中驱驰;
那洋溢在我睫下的朵朵水花,
从忧愁里映现你胜利的荣姿;
请不要以我的泪作你的镜子,
你顾影自怜,我将要永远流泪。
啊,倾国倾城的仙女,你的颜容
使得我搜索枯肠也感觉词穷。
应该说:这是译诗中的上品——冰雪之文。
梁实秋的译诗别有风格:文词朴素,不施铅华,但也自有它明快流丽的优点。且读前诗的梁译:
太阳没有这样亲热的吻过
玫瑰花上的晶莹的朝露,
像你的眼睛那样的光芒四射,
射到我颊上整夜流的泪珠;
月亮也没有一半那样亮的光
照穿那透明的海面,
像你的脸之照耀我的泪水汪汪;
你在我的每滴泪里映现:
每滴泪像一辆车,载着你游行,
你在我的悲哀之中昂然而去。
你只消看看我的泪如泉涌,
我的苦恼正可表示你的胜利。
但勿顾影自怜;你会要把我的泪珠
当作镜子,让我永不停止的去哭。
啊,后中之后!你超越别人好多,
无法揣想,亦非凡人所能言说。
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倘能再比较一下第四幕第三场九十九一一百一十八行那首有名的杜曼情诗(“On a day,alack the day!”),以及全剧之末猫头鹰和杜鹃鸟所唱的《春之歌》和《冬之歌》的两种译文,当会得到类似的印象,即:朱译诗语言优美,富于诗情,梁译诗调子明快,朗朗可诵,由于紧扣原文,译得更细致一些。
现在,我要在这枯燥的译文比较之中插进一段小插曲。
事关另一首诗。见于第四幕第二场五十六一六十一行(据Riverside ShakesPeare)。它是剧中一位塾师霍罗福尼斯的大作,内容写法国公主猎鹿。在朱译本里,塾师吟诗云:
公主一箭鹿身亡,
昔日矫健今负伤。
猎犬争吠鹿逃奔,
猎人寻鹿找上门。
猎人有路,鹿无路——
无路,无禄,哀哉,一命呜呼!
他的朋友纳森聂尔牧师听了,连声赞曰:“真奇才也,可仰,可仰!”
我也觉得“奇才可仰”。但因为太佩服了,就去查查原文。原来,这是剧中这位酸学究瞎编出来的歪诗(附录)。它的内容只是利用Sore(四岁鹿)和Sorel(三岁鹿)仅有“I”一个字母之差,而在那里颠来倒去换算;形式则是利用音义双关耍贫嘴的“绕口令”;表面上又装出一副深奥莫测的假象。据J.D.威尔逊考证:这首滑稽模拟诗意在嘲讽当时一个爱做数字游戏打油诗的数学教师。这种酸腐的歪诗,类似我国旧小说《绿野仙踪》里那个冬烘塾师所做的“哥罐体”诗。这种缠夹不清的诗文,正像《堂·吉诃德》里说的,即使让亚里士多德复活,也弄不清它的“微言大义”。翻译家对它们头疼,也就可想而知了。
梁实秋先生宁肯自己吃苦头,下硬工夫来对付这首歪诗,老老实实把能译出来的地方都译出来了——原来,这篇了不起的大作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
狩猎的公主射杀一头受人喜爱的两岁鹿;
有人说是四岁鹿;现在射杀了未免太惨。
群狗大吠;惊起了五十只鹿,三岁鹿跳出了丛林深处;
也许是两岁、三岁或四岁鹿;大家齐声呐喊。
如果射中了,伤五十只只等于射中三岁鹿一头,
我可以把伤处变成一百,只消加上一个L就够。
那么,朱译本里那首古色古香的“公主一箭鹿身亡”究竟算是谁的作品呢?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朱生豪,因为他在《无事生非》的译本里就曾替克劳狄奥为希罗写过大有《芙蓉诔》味道的祭文和可以上追风骚的祭诗。但是,查一查一九五四年的《爱的徒劳》旧版,他的原译文里并没有这首诗的影子——这首诗不对他的胃口,删掉了。这才明白:现译本中这首滑稽俏皮的七言古风,原来是校订者吴兴华的作品。就诗论诗,这是一首别有风趣的好诗,可以置之“古逸诗”之列。无奈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不但词句,就连内容,跟莎翁原作也只剩下那么一点点若有若无的联系了。这不禁叫人想起我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个掌故:《茶花女》歌剧的第二位译者陈绵曾经埋怨歌剧的第一位译者刘半农翻译的《茶花女》、《饮酒歌》(“这是个东方色彩的老晴天,嘿,大家一起饮酒吧!……”赵元任作曲),说是对照法文原文,“不知道他老先生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见商务旧版《茶花女》陈绵译序)
现在又发生了一件译界趣闻:富有诗才的校订者,遇到一首歪诗,触发了诗兴,干脆抛开原文,大笔一挥,替莎士比亚另外写了一首诗。
我想笑,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马上想起了校订者吴兴华的命运。吴兴华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莎剧翻译家。从他的《亨利四世》译本可以看出他对古今中外的学识修养和磅礴的才气,他把剧中的市井俚语、流氓黑话、插科打诨都译得生动传神。从人文版莎氏全集来看,他做的校订工作也最多。令人痛惜的是,这位重要的莎剧翻译家竟在十年浩劫中饮恨而亡!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给翻译家留下了说不尽的难题。四百年间的一般语言隔阂不说,他还使用了大量当时的俗词俚语,融汇了大量当时的风俗人情。这些构成了后世理解和翻译他的障碍。同音异义的双关语(Puns)遍布在每个莎剧之中。这是当时人的一种说笑习惯,曾经使得伊利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妙趣风生,但今天要把这种英语用中文译出来可就太难了。另外,外国作家“临文不讳”,作品中常有“不雅驯之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写文章似乎又特别泼辣恣肆,像薄伽丘和拉伯雷都是以此出名的。莎士比亚也有此特点。莎剧中猥亵语甚多,国外还有专书研究这一问题。J.D.威尔逊曾不无幽默地说:伊利莎白时代的人对于cuckoldry(老婆偷汉子)开起玩笑来从来不知道疲倦。莎剧中也反映了当时这种市井习气。——不过,《金瓶梅》和《红楼梦》里也有“王八”长、“王八”短一类的话。可见这也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不能单怪莎士比亚。说到这里,还得补充一句:莎剧中的猥亵语,总的社会效果类似《红楼梦》,并不像《金瓶梅》。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我们所谈的两种译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法。
宋清如回忆朱生豪的译莎工作时,写道:“原文中也偶有涉及诙谐类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的语句,他就暂作简略处理,认为不甚影响原作宗旨。现在译文的缺漏纰谬,原因大致基于此。”(转引自《朱生豪传》第129页)
从朱译本看,确实如此:莎剧中许多双关语、猥亵语和其他难译之处,已被改写、回避或删去了。因此,朱译本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洁本”。
梁译本反其道而行之。台版《莎士比亚丛书》例言中说:“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
自从严复提到“狭斯丕尔”,梁启超为这位爱文河畔的戏剧诗人起了一个标准的中文名字“莎士比亚”以来,我国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介绍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两位翻译家各有自己的追求,也都以毕生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朱生豪才气纵横,志在“神韵”,善于以华美详赡的文笔描绘莎剧中的诗情画意。他的译本语言优美、诗意浓厚,吸引了广大读者喜爱、接近莎士比亚,从四十年代末以来对于在中国普及推广莎剧做出很大贡献;但限于他当时的工作条件,今天拿原文去检查,也会发现他的译本尚有不少遗漏欠妥之处。
大陆读者对于朱生豪译本知之甚稔,而知道台湾另有一部莎士比亚全集译本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为了学术上的公正,对于梁实秋先生的莎译贡献应该给以充分肯定。梁译本不以文词华美为尚,而以“存真”为宗旨,紧扣原作,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回避种种困难,尽最大努力传达莎翁原意。他的译文忠实、细致、委婉、明晰,能更多地保存莎剧的本来面貌。总的说,这是一部信实可靠的本子,语言也流利可诵。对于不懂英文而又渴望确切了解欣赏莎剧的读者,从这个译本里可以窥见莎翁原作的更多的真实面目。
梁译本由于上述优点,还具有另外一种作用,即:它能引导具有英文基础的读者去钻研莎士比亚原著,帮助他们去准确了解莎剧原文。这后一种作用不可低估。因为,我们未来的莎学研究和莎剧翻译的基础在于我们今天的青年学者攻读莎士比亚原文的能力。缺乏这个根本基础,今后对于莎剧的欣赏、评论、翻译、研究都将落空。专家早就指出:直接阅读莎氏原著并非易事。在目前国内莎学参考工具书极端缺乏的条件下,梁氏的莎译加上其中的简明扼要的注释,对于初入门的中国学生在攻读莎剧原文时能起到一种“拐棍”的作用,有助于对于原文的准确理解和欣赏——因为这部译本包罗了一位严肃不苟的莎学家一生中对于莎翁全集一字一句、一事一典的辛勤研究的成果,后学者对它细细揣摩,将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这是梁译本所具有的特殊学术价值。本来,梁氏译莎的苦心,就“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
(《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译,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