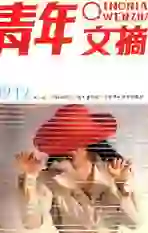有那样一支歌
1989-01-01嵇伟
嵇 伟
好久好久了,无论在作品中抑或闲谈间,我都不再提起那些岁月。当年写血书报名上黑龙江的那份狂热,当年远去淮北改天换地的那份虔诚,当年在失落了理想后无所适从的那份颓丧与沉沦,全都被我丢弃在以往的作品中,尘封进心的最底层。如今我已不再年轻,不再狂热,不再虔诚。朋友们却对我说:写写几度春秋吧。
于是,我把它从记忆的沉淀中捞起。
有谁还记得这首歌么,曾在安徽插队的朋友们?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随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地球,是我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极普通的旋律,极普通的歌词。这些年,曾经我的手发表过无数令人感动的好诗好文章,但再没有什么象这首歌那样打动过我,烙印在我的灵魂中。
记得那是个初冬的下午。连着下了几天雨,屋里屋外全是稀滑的烂泥。麦面吃完了,只有一筐红芋堆在乌黑的灶边。水缸里剩下一汪浅浅的混水。同屋的早已不知去向。我蛮可以换上胶鞋上哪儿去混几天的,但我只是倚着秫秸编的门望着空旷的田野怔怔地发呆,心就象这灰蒙蒙的天地一样阴沉。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叫“阴雨忧郁症”,那时我只感觉疲乏,感觉空虚,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想呜咽想抽泣的欲望。
天渐渐暗了。田野里的树影从我茫然的视线中消逝。我开始考虑怎样填饱肚子。记得他俩就是那会儿来的,一高一矮,背着人造革方包,穿着南京知青们流行的劳动布工作服。他们在我门口一站,自来熟地说:
“上海的插妹,我们走不动了,在你这儿混顿晚饭吃。”
我想让他们去敲前庄男知青的门,我想说这儿没有水没有面只有红芋。但我那会儿太孤寂了,我什么也没说,点亮了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
……煮完芋头汤的锅里还残留着丝丝热气,怕冷的苍蝇们爬满了麦秸编的锅盖。如豆的油灯摇曳着。屋外的雨淅淅沥沥。
高个子说:“谢谢你的晚饭,教你一支歌吧,我们南京知青最流行的。”
那首歌就这样从他略略沙哑的嗓子里流出来了。感伤,忧郁,却不哀怨。就象我们的命运。
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了。灶下的柴禾燃尽了最后一星余辉,变得冰冷灰暗,他们象从来不曾出现过似地消失了,仿佛是个梦。只有那首歌真实地留下来了。这以后,每当我忧郁和寂寞,每当我思念亲人和家乡,每当我感觉对于生活无可奈何,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唱起它。
第二年夏天,当这首歌在全安徽的知青中流传时,我极偶然地得到了歌词作者一个朦胧的地址。我向生产队的会计借了五元钱,就背上绿色的帆布书包上路了。走了三十里?五十里?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拦住了一辆去南京的卡车。
谁都有过虔诚狂热痴情的十七岁。那时我不知道一夜颠簸之后还会乏累,那时我也不懂得39℃高烧最终会让我躺倒在哪儿,我只以为那份火烧般的灼热是为想看他的急迫心情所致。我在梅花山附近,在雄壮的古城墙附近面色通红地向简陋平房里的人们打听着他。我那样地渴望见见他,仅仅是见见,为了那首歌。它打动过千千万万知青,和我。
我倒在哪儿的?我不知道。我猜是哪个好心人把我送进了城郊的一家卫生所,让医生给我打了退烧针。我象梦游般挣扎起来,坐汽车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至今无法知道我昏睡了多久,直到车站扫地的一位大娘摇醒了我。
“闺女,你在发烧?你去哪块?”
她拄着扫帚,一手攥着我的胳膊。
我摇摇头,觉得胸口灼热,呼吸急促。我的脸上已经长满针尖大的红豆粒儿。
“闺女,你赶小出过疹子吗?把舌头伸出来,让大娘看看。”
我听话地伸出了舌头。于是一切都明白了,我在出麻疹!那年我十七岁。
再以后,就是被列车乘务员护送回上海。吐血,昏睡,休养一个月。
我再也没有去找过那首歌的作者。
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抓并且被判了十五年。还有人说是判的无期徒刑。当然,只是为了那首歌。年复一年,唱那首歌的人渐渐的少了。更少了,甚至没有了。可有的东西,即使它曾经多么辉煌过,一经时间的沉淀,总会被淡忘,被遗弃。
那首歌,相伴过我们这代人生命中最黯淡的岁月,如今,有谁还愿意去追忆那份久远的黯淡呢?
只有在那些似醒非醒的早晨,在极少的失眠的晚上,我会朦胧地记起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初冬之夜,在摇曳的油灯下,有过那样一首歌,从一个略略沙哑的嗓子里流入我的青春,流入我十七岁的灵魂。
他是谁?他就是那首歌的作者吗?抑或只是我孤寂中生出的梦境?我不知道。
所有的回忆都只是心灵期望的梦,对么?
(文心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