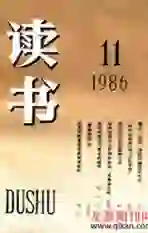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1986-07-15翁绍军
翁绍军
罗素曾说过:“阅读哲学之后,我仿佛感觉到由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多彩多姿的新世界。”我没有进山出谷的亲身体验,但对罗素那种豁然开朗的欣然之感还是能领略几分的。鲁一士(J.Ro-yce)说得好,“哲学家应当追索的,乃是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有深度的哲学著作之所以扣人心弦,使人顿生解脱之感,就在于有这种思想的流动、变化和冲突。它们具有一种神奇的启示作用,激发人的思想火花,使人在倏忽洞明的一个新世界里神驰意游。感谢《读书》编辑部惠寄一本新出版的德国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H李凯尔特的名著《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使我一享先睹之快,并有机会将读书得到的启示,调理成文,奉献给读者。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断言:全部哲学都随着黑格尔体系没落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又被称为“科学的科学”,黑格尔体系既是它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是它没落的标志。哲学史的事实证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确实是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哲学却不会没落,也不会被实证科学所代替。在旧哲学涅
从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文明的过渡,其最本质的变化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十六世纪是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降下帷幕的,而培根则以这样一段话拉开十七世纪的序幕:“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份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这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进入十八世纪,康德却以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公开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他断言,对象意识的成立,取决于自我意识,对象要符合我们的直观能力,这是人在认识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他断言,人是目的,任何财富珍宝都代替不了人,道德使人超出一切自然物之上,这是人在实践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梁启超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十九世纪就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在起伏嬗递的思潮之中,新康德主义尤其引人注目。提到新康德主义,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它“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并本能地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流派”划上等号,这兴许是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哲学史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说新康德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论,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许把他们说成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相对抗,会更合适一些(其实也不尽然)。这股思潮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力图恢复和突出在康德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思想。它在思想史上起了一种桥梁作用,这座桥梁把康德和本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家联结了起来。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八九九年问世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新康德主义的价值。
新康德主义者都称自己是“康德世界观的使徒”,并坚信自己“永远是康德的真正传人”,但他们也和其它任何学派一样,对自己宗师的学说加以修正补充,希冀灌注给它新的生命,因此,不免各有所持,门派分裂。在康德的旗帜下,马堡学派和巴敦学派就发生了这样的分裂。马堡学派认为新的哲学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托普(Natorp)说:“我们是把作为哲学对象的自然、把自然科学的自然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哲学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拼写出经验”。他们致力于寻找科学的先验逻辑结构,寻找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根源就是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的普遍联系,但又是先于自然的人的知识的先验形式,它们极其类似柏拉图的“理念”,那托普声称“我们力图用柏拉图来深化康德”,其原因皆出于此。
自然科学能否代替哲学?“理念”能否代替现实?巴敦学派和马堡学派相反,作了否定的回答。巴敦学派的文德尔班把哲学喻之为莎翁悲剧中的李尔王,把自然科学喻之为李尔王的诸女儿,李尔王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女儿,自己却只留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如果自然科学真能代替哲学,那么,哲学除了束手待毙,没有别的出路。这种命运当然不是巴敦学派所希望的。巴敦学派指责马堡学派的泛自然主义,指责他们把伦理学和历史自然化。李凯尔特指出,他们“认为‘理念就是现实;而且,由于理念是一般的,是与处处特殊的、个别的而其实本来并非真实的感性世界相对的,因此个别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只有一般的东西,因而反映理念的表象,才是真实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8页)。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专门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直接所与的、内在的感性世界,它的任务仅仅在于模拟这个世界。”(第29页)这样,科学只能起到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的作用。在李凯尔特看来,如果只是让这种由理念组成的自然科学代替认识现实的一切科学,那么,科学所起到的作用还远远及不上一面镜子。因为,现实是异质的连续。它具有普遍性,所以是连续的;它具有个别性,所以是异质的。普遍概念只能反映前者,因此,自然科学“不能借助于概念而表述所研究的对象的一切特征”。(第40页)
李凯尔特从自然科学与现实的鸿沟以及理念与现实的鸿沟中,得出了自然科学不能代替哲学、理念不能代替现实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可以追溯到康德。李凯尔特承认,正是康德,“在哲学中结束了自然概念的独霸地位”;康德在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第9页)这里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发表前半个世纪,丹麦思想家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也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克尔凯戈尔指责抽象思维为了追求普遍和永恒而抹杀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好比医生为了消退病人的高烧,先用药毒死病人一样,他不无激忿地说:“所有的腐败最终来自自然科学”。克尔凯戈尔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李凯尔特从理性主义的立场,不约而同地都对自然科学的绝对合法地位投以怀疑的眼光,这种眼光出自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全面凯旋的时代,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曾出现过以毕希纳为代表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他们在自然科学成就面前忘乎所以,断然宣布自然科学可以代替一切,而把以往的哲学体系都视之为“精神骗术”。恩格斯嘲笑这些小贩“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列宁则把他们称为思想僵化的不能从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珍珠的“一群雄鸡”。与这群“雄鸡”相比,李凯尔特等人的眼光不失为哲学家的眼光,它尽管不合时宜和过于偏激,但其可贵就在于具有智慧的火花,这些火花可以把人类的视线引向更深邃的远方。事实上,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以牛顿力学为支柱的旧自然科学体系就迅即崩溃,由之构画的世界图式也随之而销匿。
对于普遍和个别,李凯尔特的态度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要把普遍和个别都纳入科学领域。根据认识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科学采用个别化方法。读者也许会问:自然由个别的物体和事件组成,为什么对自然的认识要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对文化的认识要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自然不具有价值,文化具有价值。李凯尔特在另一部著作《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具有价值的自然和具有价值的文化之间的区别。他把一块煤比作自然的个体性,而把英国王室珍藏的科伊诺大钻石比作文化的个体性。一块煤随时可被另一块煤代替,它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谁也不会看重它,人们把这块煤分割或砸碎,可它依然还是煤。而科伊诺大钻石则不同,它永远不可能用另一块钻石去代替,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个体性,把它分割或砸碎就不成其科伊诺大钻石。自然的个体性如同一块煤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科学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认识它,自然可以被数量化(分割和砸碎,也就是抽象),认识自然的科学应当也只能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的情况就不同了,“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第20页),每种文化现象都只出现一次,它们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次”和“这一个”,如果用普遍化方法去认识它们,抽象掉它们的个别性,那就无异先把科伊诺大钻石砸得粉碎再珍藏起来一样。
指责李凯尔特把自然和文化、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在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竟无知到去否认自然界里有个别的东西以及社会历史领域里有一般的东西。其实,他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对于个别特殊与细节作详尽深入的考察”,也不排斥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普遍化的科学。李凯尔特只是认为,科学应当作为人对现实的能动的认识,而不是消极的反映。“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第30页),因此人与现实相比较,应当始终采取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第34页),把所研究的对象加以改造,选择其本质成分,省略其非本质成分。面对一尊商鼎,凡夫俗子立时联想到的也许是和尚庙里的香炉,因为他选择了庙祭礼器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而一位考古学家则不会作如是的联想,他的眼光只盯住“这一尊”,他要研究的也只是“这一尊”,他完全明白,面前的鼎,对于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这一尊”,显然,考古学家选择了文化价值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
要把个别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真是谈何容易,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这种关于单一的和特殊的东西的科学,在自然科学旁边要安插一门文化科学,无异是想在他人卧榻之侧安睡一样。李凯尔特对这个困难是充分认识到的,他指出,直到今日,文化科学“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第11页)。可以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伊诺大钻石是件自然物体,但它对人类具有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可能替代的意义,因而被人保存珍藏,从而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美尼尔氏综合症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但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区别在于方法的(即形式的)区别。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利用个别性概念,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对我们也许是陌生的。举个例子来说,歌德和某个普通人都是现实的个体,普通人的个别性是任何别的普通人都可以替代的,而歌德却具有普通人都不具有并因此永远不能被替代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就是他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他的个别性与文化的价值联系,这种联系是文化科学在歌德身上所选择的本质成分,概括这种成分,就形成了歌德的个别性概念,而用个别性概念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就是个别化方法。文德尔班最先运用这种方法,并把它称为表意化方法。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与这种表意化方法有所不同,文德尔班追求突出事实性的直观效果,李凯尔特则追求意义性的概念效果。
十九世纪是人类值得自豪的一个世纪,一提到它,人们就会想起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的突破、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突破,以及类似铁路电报的数不清的发明。然而,怀特海(Whitehead)的说法却出人意料:十九世纪最大的发现是找到了发现的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巴敦学派特别是李凯尔特所提出的个别化方法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索的一个突破,并且已经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社会学研究,现在已越来越为各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瞩目,他确定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以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体的价值取向为对象,断言概念形成的基础,不是客体共性的抽象,而是主体对问题的设定。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变革,正是从李凯尔特那里获得启示的。探索,攀登,独辟新径,我在阅读《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时,对于作者的理论勇气,是时时生发出一种敬佩之感的。
人们爱读史书,这不仅因为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更因为它所记载的人事兴废,变迁沉浮,最能激起人的共鸣。梁启超称赞王船山的历史评论最富价值,认为“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喜爱《史记》《汉书》,往往“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项羽田延年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震撼人心,这本来是值得称道的,王船山却斥之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史书应当具有鲜活生动的特色,古人曰,“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这也许是他们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之谈。
李凯尔特历史观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强调历史的个别性。他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提出,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不至于象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学认为对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是它自己的课题”(第50页)。我国史学界是否有必要借鉴一下李凯尔特的观点呢?“历史的个体对众人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人们读到的拿破仑,应当是不同于亚历山大与恺撒的拿破仑;读到的贝多芬,应当是不同于巴哈与勃拉姆斯的贝多芬;读到的黑格尔,也应当是不同于柏拉图的黑格尔。这样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政治史、艺术史和哲学史。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不正是一部有鲜明历史个别性的著作吗?恩格斯称誉它是“天才的著作”,绝不是出于寻常的恭维,这部著作需要天才的历史洞察力和富有独创性的选材和表述能力。这部历史著作表述了一八四八年二月路易—菲力浦被推翻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这段时期法国的阶级斗争,在它里面没有“铁的规律”、“必然性”和“曲折性”这类用语,有的是对这段时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书中出现的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这段特定时期的小农,闭塞隔离的生产方式、落后的交通、自给自足、相互敌对、迷信的传统,使他们成了波拿巴复辟帝制的支柱。书中表述的军队是“没有从共和党人中得到光荣和附加军饷”的军队;这段时期的大资产阶级把波拿巴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而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则把他作为对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正是这些具体的个别性的历史关系,使路易·波拿巴这位不只丧失法国公民资格而且当过英国特别警察的平庸可笑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部非凡的历史著作在我们眼前活现了路易·波拿巴帝制复辟的闹剧。据说,马克思这部著作的这一特色已引起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出现了专题研究论文。我想,在这方面参考李凯尔特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康德说: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历史是文化的积累过程,在这过程中,沉积着各个时期人类的认识功能、道德实践和审美情感的结晶。这里贮存着各个时期人类创造意识、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的无数信息。对于哲学来说,这里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在这天地里驰骋和开掘,可以达到对人类自身的更深邃的认识。今日,当我们处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之中时,对于文化科学的倡导者李凯尔特,也许是会产生一种亲切感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德〕H.李凯尔特著,涂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三月第一版,0.8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