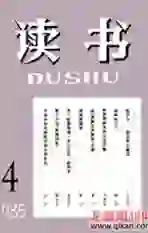熊十力与《新唯识论》
1985-07-15魏达志
魏达志
去年暑期,蒙陈子展、吴剑南先生指点,又经当地老人热心引路,好一番辗转反复,我终于得以访问已故熊十力先生的家。冷落多年的新唯识哲学又有人问津了!熊十力先生的女儿熊再光和儿媳万云娇高兴地接待了我这位不速之客。面对十力老人的遗像,我以极浓厚的兴趣听取了她们关于这位老人生平治学经历的生动叙述。
熊十力,湖北黄冈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自号黄冈逸翁、漆园老人等,生于一八八四年,卒于一九六八年。解放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熊十力的童年,是在没落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度过的。他年幼丧母,家境困厄,从小为人放牛,学习裁缝。父亲熊启样是一名笃守程朱理学的穷儒生。熊十力自小记忆力就极强,一天之内能背诵《三字经》。“少时好探求宇宙论”(《体用论》),如儒家六经,老庄道论等,并略览大易爻象,始读格致译本,对于王船山、顾炎武及启蒙、维新之文,亦孜孜以求,手不释卷。广泛的涉猎为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熊十力“年未二十,即投身兵营,以谋革命”(《十力语要初读》),参加武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并考入陆军特别学堂,投身反清革命。后因创设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士兵学生起义,引起驻防军统张彪的注意,遭通缉追捕而被迫潜逃回乡。辛亥革命爆发后,熊十力曾任黄冈地方军政府参谋。至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迫害革命党人,熊十力暂时退出政界,由此废学数年。至三十左右,他自度非事功之才,又因长兄幼弟相继贫病死去,于是另辟蹊径,寻求寄托,致力于学术一途。三十五岁以后,专治国学,主要是哲学思想方面。当时由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影响,统治者对儒佛的极力提倡,封建传统哲学又有了复归的趋势。一批上层佛教僧侣,适应这一潮流,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组织佛教协会,创办佛学院,出版佛教刊物,熊十力亦值此机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渐门下,研究佛家法相唯识之学。
熊十力曾以研究佛学作为他“安身立命求学问”的根本,由于儒学根底的深厚及对群书的博览,使得他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对旧有唯识之学,“潜思既久,渐启疑端”,发誓要造作“新唯识论”,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九二三年,熊十力初以文言文撰成“新唯识论”,并在国立北京大学设课讲授。其间与林宰平、梁漱溟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纵横古今,“时或啸声出户外”(《十力语要初读》)。后又甚疑旧学,尽毁前稿,并与友人林宰平、马一浮等时相攻诘,商榷疑义,历经更改,至一九三二年十月,《新唯识论》定稿并自印行世。熊十力认为:“本书于佛家,元属创作。凡所用名词,有承旧名而变其义者,有
《新唯识论》虽经几次印行,版本亦不相同,但主要有二种:“一,文言本,写于病中,极简略。二,语体文本,值国难写于流亡中。”(《体用论》)一九四四年,熊十力在四川北碚创办中国哲学研究所,写成《读经示要》一书。熊十力学养深湛,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明心篇》、《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等,均围绕其新唯识哲学加以发挥和详释,犹如为经作传,所以《新唯识论》为最重要,熊十力“平生心事,寄之此书”(《新唯识论》),是反映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一九五四年秋后,熊十力到上海居其子熊世菩处。从此后出版的《原儒》、《体用论》、《乾坤衍》等几部著作看,熊十力晚年更重儒学,认为唯孔子“集古圣之大成,开万世之学统”(《原儒》),其学术创明体用不二之宇宙论,最终归本孔子。“益信孔子之道,终为人类所托命也”(《原儒》),认为《体用论》既成,“新论二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余之学自此有主,而不可移矣”(《体用论》),自认为学术上有了更高的升华。
吴剑南先生是熊十力的生前好友。据吴先生回忆,抗战时在北碚因一次偶然机会结识熊十力。当时熊十力已蜚声文坛,颇有名气,但一般人不易与之接近。吴先生虽久仰盛名,亦感不便冒昧拜访。吴先生当时除在复旦大学任教外,兼擅医术并挂牌问诊,一次被请去为熊十力看病,熊同吴谈不多久便说:“你身上有一股奇气”吴先生回答:“什么奇气,是股穷气吧!”说罢二人相视而笑。从此,吴先生成了熊十力家中的座上客,他虽比熊十力年少十几岁,但情趣相投,成为忘年之交,直至全国解放以后。在学术上,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见解,熊十力从不随波逐流,自始至终坚持他的哲学体系和学术观点,对此,吴先生感触很深。说到做学问,吴先生认为学问不但要“学”要“问”,而且要“做”,“做”即身体力行,有学问不“做”学问只能是半个学者,熊十力在吴先生心目中,就是这种身体力行的学问大师。吴先生将他珍藏的《乾坤衍》借给我,并嘱我慢慢领会,深心体玩。经过吴先生的介绍,我还从已故林同济教授家里借到《佛家名相通释》上、下二册,此书综述法相、唯识体系,亦是熊十力的用心之作。书内扉页上有熊十力的亲笔题款和林先生的印鉴,显得更加宝贵。可惜藏书浩瀚的复旦图书馆竟没有这部书,我准备复印下来以填补这一空白。吴先生还答应专门就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及其学术源流和我谈一次,但是由于杂务缠身,没有及时聆教,以至于错过了一个永远不可再加以弥补的机会,吴先生在不久即与世长辞了,每念及此,甚感痛惜!
佛教的唯识宗派虽在中唐以后渐趋衰弱,但其精致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却对以后的哲学流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派分析了世界上各种“法相”,即心和物的现象,称法相宗。但最终将一切“法相”归结为“识”所产生,所以定名为“唯识宗”。唯识宗属于佛教大乘学派,因为强调心识为有,以区别于大乘空宗,故又名大乘有宗。欧阳渐感到无着和世亲之学互有不同,并加以区别,认为“世亲成立唯识,是唯识宗。无着以方便解析一切法相,是法相宗。”(《新唯识论》)熊十力则弃旧学而造新论。“新唯识论”以主观唯心主义一元论的面目问世,代表了现代中国思想界儒佛学说的恢复及新释这一重要思想倾向。解放后三十余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在海外,特别在台湾,五十年代初就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熊十力在文中被誉为一代大儒、中国现代哲学家等。据熊十力家人介绍,熊先生现有不少学生侨居海外,其学术在海外具有相当的影响。
周谷城先生也是熊十力生前难得的莫逆之交。我想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渊博学者,这与周先生的胸怀坦荡、熊先生的气度不凡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在学术上见解不尽相同。周先生告诉我,在他早年的著述中,有专文评价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由此,我又拜读了周先生写于三十年代的这篇评论。周谷城先生认为:“新唯识论的要旨,首在说明纯一寂净的本体,次在说明生化不已的妙用。寂净的本体,印度的空宗讲得最透彻;生化的妙用,中国的儒家讲得最透彻。儒家非不讲体,但比较地偏重用;空宗非不讲用,但确实只重体。为使学理圆满,熊先生乃汇通儒佛,于寂净的体上加以生化的用,于是体用合一,印度的空宗,中国的佛家,汇合起来了。……此外,更于生化的妙用上,施设一个物理世界,或外在世界,以为科学知识的安足处,于是西方的科学在东方的哲学中似乎也有地位了。这是新唯识论中最要紧的意思。”(《中国史学之进化》)
熊十力矢心求学,冥探繁深,对百家之说,先是深心体现,辨其脉络,得其系统,穷其枝流,而后才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他“常有赖于平日所读百家之书,借资引发。久之,豁然贯通。……亦自觉得,对于百家之说,或有所同,或有所异,或于众异中有一同,或于众同中有一异,或于小同中有大异,或于小异中有大同。然无论同异如何,而自家思想,毕竟不是浮泛或驳杂的见闻所混乱凑合而成的,毕竟是深造自得的。”他说“新论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自是会通之学”,“新论于西洋学术上根底意思,颇有借鉴”,还认为“读本书者,若于佛家大乘学,及此土三玄(大易、老、庄),并魏晋宋明诸子,未得其要,则不能知本书之所根据,与其所包含,及融会贯通处。”熊十力自己对“新唯识论”有一概括,他认为:“新论要义有三。一,
《新唯识论》成为熊十力深造自得的一部创新之作,也是儒佛唯心主义系统合流的一个产物。当他以僵化、片面的认识去观察一个花瓶或一棵树的时候,他的宇宙观又充满矛盾运动的朴素辩证法;当他冶儒佛于一炉并自创唯心主义新体系的时候,却又在追求着科学与民主。“新唯识论”不仅承继的是一份唯心主义的思想遗产,还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总而言之,熊十力不愧为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从世界观高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而且代表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股重要的思潮,在现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这种思潮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新唯识论》也就因此而成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份总结。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