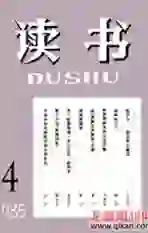略论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
1985-07-15舒昌善丁聪
舒昌善 丁 聪
被卢卡契誉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托马斯·曼,在西方的某些评论中是纳入现代派作家的行列的。如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后现代派”的代表巴思说:“‘后现代派文艺美学的前驱可以循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伟大的现代派作家如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安德烈·纪德、詹姆斯·乔伊斯、弗兰茨·卡夫卡、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一直上溯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①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彼得·福克纳在《现代主义》一书中也有类似说法:“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到灯塔去》和叶芝的《钟楼》,这里还不说里尔克、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马查多、阿波利奈尔、温加雷蒂、阿尔维蒂、托马斯·曼、普鲁斯特、卡夫卡和斯韦沃的同代作品。”他还说:“讽刺笔调是现代派文学中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主要标志,例如,普鲁斯特、穆西尔、托马斯·曼、卡夫卡的作品。”②显然,这里所说的现代派,是指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不同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的总的文学潮流,而不是E·庞德的那种概念:主张中世纪以后五六百年的文学都可称现代派。
托马斯·曼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抑或是现代派作家?试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以及他对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的态度方面略作分析。
曼在二十五岁以前创作的十余篇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表现“局外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孤独感”。但是,在他笔下的局外人,不是由于社会原因而是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或病态——有的发育畸形,有的酗酒成性,有的异常神经质——才无可奈何地过着孤独的生活,然而在他们的内心却还在寻求幸福和生活的意义。如《矮小的弗里德曼先生》的主人公,是个驼背,由于生理缺陷,似乎和爱情与婚姻无缘,眼前也看不到能成为巨商的前程,于是不得不培养自己的爱好,他阅读各种文学作品,经常到剧院去,甚至战胜身体的痼疾,拉小提琴,内心“充满着一种自己创造的恬静的幸福”。一天晚上他到剧院去,发现座位旁坐着楚楚动人的盖尔达夫人,她不时用小动作向他调情,他以为盖尔达真有意于他。一天他到她家中看望,两人散步到花园的河边,他终于不能自持,哪知这个女人突然把他推倒在地,自己扬长而去!他爬到河边,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上来。一心想驾驭自己命运的弗里德曼最终还是被生活抛弃。作者的同情跃然纸上。显然,这种局外人的形象和现代派作品中的那些敌视客观世界、社会与他人,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倦、恐惧与迷惘,对现实采取极端虚无主义态度的非理性的局外人完全不同。《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是表现“孤独感”的短篇,它在情节上和卡夫卡的《老光棍勃鲁姆费尔德》颇相似。敏德尼克尔是个孤苦伶仃的人,一天他买了一条小狗,从此和它相依为命,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可是小狗不通人情,乱蹦乱跳,不听主人召唤,于是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心爱的小狗,事后又泣不成声。老光棍勃鲁姆费尔德希望有个伴侣,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两个赛璐珞小球,跳着蹦着跟在他身后,成为他的生活伴侣,开始使他感到有趣,后来又吵得他无法休息,带来新的烦恼,最后不得不把小球送给邻居的小孩去玩了事。这两篇小说情节虽相似,但实质却不同。曼笔下的小狗是生活的象征,主人一怒之下把它杀死,事后又悲痛万分,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卡夫卡笔下的小球也同样是生活的象征,但主人把它们送走之后,却觉得如释重负,得到了解脱,暗喻着对生活的厌恶与困惑。一九○三年,曼发表了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主人公是富裕的市民阶级子弟,后来成了声名很大的文学家。他的原型就是当时已出版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曼自己。小说表现了文学艺术家在创作道路上的彷徨,因为其时正是欧洲现代派文学(当时曾被一些人笼统地称为颓废文学)兴起盛行之际。文学艺术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热爱生活、反映现实、把自己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还是憎恶生活、表现自我,使自己与社会脱节。最后主人公发出这样的心声:“我佩服那些高傲和冷酷的人,他们在具有魅力的伟大的‘美的路途上探险,并且蔑视‘人——但我不羡慕他们。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作家,那正是我对人性、对生活、对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爱。”这就是曼的自白。“高傲和冷酷的人”即是指叔本华和尼采,曼以“佩服但不羡慕”的态度清算了叔本华的唯美主义和尼采哲学对自己在青年时代的影响,从此告别了文学上的尝试和摸索阶段,开始进行“肯定人生、热爱生活、倡导人性”的文学创作,这篇小说也就成了二十八岁的曼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的里程碑。以后一系列重大作品都是以宣扬人道主义和批判社会现实为内容,并且具有明显的进步的政治倾向。《马里奥和魔术师》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控诉和鞭挞;《国王陛下》是对美好生活、幸福爱情的追求;《绿蒂在魏玛》是对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命运的深刻思考;《魔山》是一部“威廉·迈斯特”式的教育小说,一部理性小说,主人公卡斯托普的最后结论是:“为了善和爱,人不应当让死神主宰他的思想。”《约瑟夫和他的弟兄们》是要从神话中寻找人道主义因素,用来对现代人类进行人道主义教育;《浮士德博士》通过主人公——音乐家莱维屈恩坎坷而罪恶的一生,象征性地反映了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不幸的经历,曼把它称为“一部痛苦的书”、一部“我的时代的小说”,小说的主题表现了德国人在黑暗势力统治下天才与罪孽的两个侧面。纵观曼的五十余年文学生涯,虽然他青年时代的创作,受过尼采、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但自中年以后,特别是晚年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反法西斯倾向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并没有现代派文学的那些思想特征,诸如表现人的异化、世界的非理性、悲观绝望、虚无主义等。
固然,曼的创作方法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许多不同之处。
象征性的人物形象,几乎贯串于他的全部创作。如《特里斯坦》中的颓废作家史平奈尔是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哲学和唯美主义的象征,批发商科勒特扬一家是健康生活的象征;《马里奥和魔术师》中施行催眠术的魔术师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被尽情愚弄、苏醒后愤而把魔术师打死的小伙子马里奥是意大利人民的象征;《魔山》中的纳夫塔是非理性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象征,塞特姆布里尼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浮士德博士》中的魔鬼是纳粹德国的象征;等等。
隐喻性的细节描写,例如,史平奈尔用蛊惑人心的语言向科勒特扬太太灌输“黑夜与死亡的美”——“甜蜜的夜,永恒的爱之夜!无所不包的极乐之土!……亲爱的死亡,求你驱散这愁苦吧!”科太太在这种“死亡之美”的诱惑下终于悄然离开人间,隐喻着“悲观厌世哲学与唯美主义”对“生活”的侵蚀。纳夫塔在决斗中自己把自己打死,隐喻着军国主义最后必将自取灭亡,等等。
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例如,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的全部情节只发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一八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早晨,三天以后的一次午餐和晚上。而歌德一生各个时期的经历和思想都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内心语言(内心独白、回忆、联想)来再现,仅歌德本人的长篇内心独白就占了整个第七章。
小说的非情节化,“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和曼在小说中随时随地夹入大量的哲理性的议论以及各种思想意识的交锋(包括人物的对白和内心的思考),使情节在小说中完全处于次要的地位。
此外,曼还运用心理分析、含蓄的讽刺,甚至带有荒诞色彩的细节(如,发霉味的玫瑰花,拔一颗牙而丧命,在决斗中自己把自己打死),把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觉、记忆与印象交织在一起,并和时代的基本思想问题以及主人公的思考、探索、争论与精神生活的各种变化熔于一炉,置于小说的情节框架之中。
曼的这些表现手法,也是现代派作家们所采用的,或许正是这一点给人一种印象:托马斯·曼是现代派作家。其实不然。
象征的手法,早已被二十世纪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所采用,但在他们的笔下,象征的外貌和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直接的有机的联系,如《马里奥和魔术师》中的催眠术师象征法西斯主义,虽然小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西斯主义,但小说问世不久,就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书单,可见象征影射的对象十分清楚。
意识流的手法,更为不少现实主义作家所采用,但在他们的笔下,用“意识流”描绘的图象,最终是完整的、清楚的,《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的那一章长篇独白,写得极其流畅自然,思想丰富而深刻,逻辑上又很有条理。
不仅如此,曼还蓄意保留某些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技巧,以示自己同现代派作家的区别,旧小说的作者往往以故事讲述者的身分出现在作品之中,而这种“说书人”的程式早已被二十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小说家所舍弃,而曼却还常常用这种写法,如《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的第一段中写道:“说起这个人来,倒还有段故事可以讲一讲……”,又如《火车事故》的开端:“讲个故事吗?但我没什么可讲的。好,就讲一个吧。”一直到一九二四年的《魔山》,作者还不时以叙事者的身分出现在小说里,如第六章中写道:“当我们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时光正在流逝——我们讲故事的时光在流逝,生活在山上雪原里的汉斯·卡斯托普和他的病友们的时间也在流逝……”又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欧洲长篇小说大都已放弃一条线索的平铺直叙方法,而崇尚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即所谓同时性(simultaneity),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各种个人和集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打破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曼却在自己的创作中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小说中有一个中心主角、情节发展的一条线索、把情节安排在一目了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
就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基础而言,核心是非理性主义,在德语文学中,其渊源之一是尼采哲学。尼采在大学读到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一书时,深为所动。可是以后尼采逐渐认识到,叔本华的人生充满痛苦的悲观主义和陶醉于艺术的忘我主义,把人引入麻醉的忘我境界,泯灭了人生旨趣,于是他写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和《人性的、十分人性的》两部著作,从此由叔本华的消极悲观地否定人生转为积极壮烈地肯定人生,并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出发,最后把它变为积极行动的反叛哲学,创立了“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尼采哲学脱离当时经院哲学的气味,字里行间充满着诗意和隐喻,悲怆中夹带着辛辣的讽刺,富有感染力。曼在一九三○年的《生平简述》中写道:“我在这里必须提到那些对我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诚然,我以后摆脱了它们的影响——我指的是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毫无疑问,在我最初发表的一些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尼采对我在思想上和风格上所产生的影响。我曾在《一个非政治人物的观察》一文中谈到过我与尼采那个错综复杂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体系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归结为我个人所处的具体条件与局限。……尼采对当时整个社会风尚的影响;他的简单的‘复兴主义以及崇拜超人、唯美主义;大肆鼓吹血与美的说教——这一切在当时都相当流行,但我对它们的态度却是鄙视的。……总而言之,我在尼采身上主要是看到他是一个自我制胜者。”③由此可见,对青年时代的曼发生影响的是尼采之“积极肯定人生”的观点和尼采的文风,而对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和艺术主张: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现代派作家的基调,曼是加以谴责的。
卡夫卡——这位被人称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曼对他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赞赏他的讽刺天才,又责备他写出如此阴暗、厌世的作品。
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充分反映了曼对尼采和卡夫卡的批判。
弗洛伊德学说,是现代派文学思想基础的另一渊源。曼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在一九三六年的《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报告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中确实有“潜意识”的魔力,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弗洛伊德学说与从叔本华到尼采德国哲学发展轨迹的联系,曼显然不信奉弗洛伊德从心理学推导出的非理性的哲学结论:“人对人是豺狼”。曼试图用精神分析来为自己的“新人道主义”服务。在曼的创作中,潜意识是作为心理的一部分,是与意识和理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理性的对立面。《约瑟夫和他的弟兄们》的主人公约瑟夫说:“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自己所做的梦的解释者。释梦先于做梦,我们是根据释梦来做梦的。”——这段话反映了曼关于潜意识受制于理性的观点。《死于威尼斯》是曼描写“情欲冲动”的小说,曼却赋予它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情欲会使人迷惑与丧失尊严”。可见,曼所描写的性意识和潜意识与现代派作家所表现的“情结”不同,不能和非理性的描写“性本能”的现代派作品相提并论。
诚然,托马斯·曼的“现实主义”不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式”的,也不是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追求“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被人称为独步世界文坛、不属于任何流派的托马斯·曼,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又一流派的代表。
曼的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用象征手法反映精神领域里的时代基本问题,并宣扬人道主义——既赋予作品以多层次的思想内涵,同时又使作品显得艰涩难懂,曼自己也说,《魔山》“是否能为读者所了解,一直是我很担心的问题”,“这部冗长的怪物似的小说的大部分章节一定会显得很枯燥。”④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九八四年欧洲五家影响较大的报纸评选出十位欧洲最受欢迎的已故作家,其中属于二十世纪的是这样四位:卡夫卡、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乔伊斯。这一信息显示出今日欧洲人的文学情趣:他们已不再满足于那些只反映作者眼前的社会现实问题、以情节取胜或以刻划人物性格见长的传统小说,而欣赏那些能发人进行深刻的哲理思考、展示内心世界图像的小说。
这后一类小说,未必都是现代派作品,同样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托马斯·曼的创作表明现实主义作家为创作具有深刻哲理内容、展示内心世界的小说,同样可以采用现代派作家的表现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非情节化……等。古人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欧洲传来的信息也会对中国的文学界有所启迪,尽管由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历史原因,中国读者的美学欣赏不可能和欧洲读者同步。
(本文托马斯·曼像,丁聪画)
①〔美〕约翰·巴思《后现代派小说》,载《外国文学报道》一九八○年第三期第1页。
②PeterFaulkner:Modernism(Methuen,LondonandNewYork,一九八一),Page13,60。
③ThomasMann:Lebensabriβ,GesammelteWerke,Aufbau-VerlagBerlin,1956,Bd.XII.Seite394-395.
④《托马斯·曼致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信》,《托马斯·曼书信集(一九一○——一九五五)》,第116、109、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