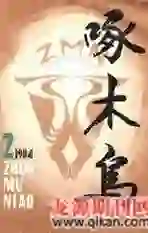小镇星光
1984-09-24唐海华
唐海华
我突然收到一封很厚的远方来信。自制的黄褐色牛皮纸信封上,我的姓名、住址准确无误,但庄重中略带洒脱的柳体楷书毛笔字和发信地址,却十分陌生。我不无困惑地拆开信封,先翻到最后一页,只见信末明明白白地写着:你的同学段坚。
段坚?就是那个高大,红脸膛,翘着嘴唇,凹着门面冲着额角,两颗大门牙象崇明珍珠米的大学同班同学?是他。
这段坚,分配工作后字还蛮有长进。这使我想起毕业前贴在墙报栏内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自我正名》。大意是人应该强调自我意识,“雷锋叔叔的感情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精神状态……”云云。有一位同学责问该期编委:
“为什么刊登这样的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
我跟段坚住同屋,自然少不了攻击他的歪论。有一次,我们俩正端着碗吃饭,我突然想挖苦他几句:“小段,我觉得变态的自我意识等于宣布自己是一具活尸。”
“啥意思?”
“你看,”我望着眼前这位村娃子,想到他学了四年却莫名其妙胡谄什么“自我意识”的怪论,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接着说:“你现在吃饭,从形式上看是你的自我意识在起作用,是一种生存的意识,但实质上你享受的则是他人的劳动成果。”
“他们也可以考大学嘛,来念书好了。”
“那么好吧,”我搁下饭碗压着火说:“假使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即使把全世界的书都当华夫饼干,所有的人最多也只能维持一天,然后都得饿死。你不用瞪眼,这个数据是我花了四年时间考证出来的。”我这样连蒙带哄,实在也是生气使然。“就说你爹娘,”我决定把火往他身上烧,“如果也‘自我意识起来,又何必生你出来!一口水,一口饭,还得供你上大学,可他们还不知道你以后还认不认这对爹娘呢!”
“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我在行使‘自我意识,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服,不服可以辩……”
“嘭!”段坚扔下饭碗就扑了上来……直到别的同学闻声前来扭开。毕业前夕的这场由精神上升到力量的“斗殴”,使我和段坚四年的同窗之谊土崩瓦解。可想而知,他能给我来信,是我意想不到的。
当我开始从第一页阅读他的信时,我才真正地诧异乃至震惊了:
“……他死了——在七天以前一个寂静的深夜。我们才相识两个小时,对他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是凶杀案,段坚是凶手?顿时,我的神经绷紧了,不由地趴下身子,双目象雷达那样扫视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是的,我没有用刀,从法律角度看是无罪的;但在道德和良心上,可以说罪不可逭。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面对台下的热烈掌声,手捧着在镁光灯下熠熠闪光的奖杯,犯罪的自我感便越发地沉了。我不得不笑,而心就象被刺了一刀,在默默地淌血。无私无畏的他已化为一缕青烟,而卑怯、懦弱、圆滑、自私的我却成了‘英雄,堂而皇之站在这里,站在这本来应该由他来站立的地方。
“哎,自从学会作文以后,我曾数十次地使用过‘心情象铅块一样沉重的比喻句。可直到这件案子发生后,我才真正尝到了‘沉重的铅块是一种什么滋味。白天,我只要一遇见干瘦精明的老头,那老头就会幻化成他的影子;晚上,他来到我的梦里,就象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深深地朝我一瞥,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果断地挺着干瘦的身躯向黑暗走去,所经之处,光明顿开——一个又一个地,似乎总也不断绝。唉,真后悔啊!有入说,后悔是无用的别名,我说后悔是痛恨的别名。我痛恨我的无能,我的故我,我的自我意识!……”
段坚把解剖刀对准了自己的灵魂……
那是国庆节前夕。按照惯例,镇政府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提早下了班。我为给镇长编写的一份形势报告作最后润笔,稍事滞留。
半小时后,我把整理好的报告送到镇长办公室,见镇长正和镇治安联防队队长、派出所贾所长在谈话。一见我进去,他就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哎!来得正好,来得正好!贾所长刚才还向我诉苦,说联防队节日值班人手不够……怎么样,小段?你,就应征了吧!文秀才当一回武状元嘛”。
联防队值班?我的“自我意识”开始活动。在我寻思,这种值班跟逛马路差不多。你想,小镇原本不大,方圆不足里把,人口不满万数。镇的四周是一片田野,一条黑浊又不能流通的小河傍着小镇,算是镇乡的分界线。镇上南北一条街,东西一趟路,相交延伸,长不到二里,分布其中的还有十数条弄堂,值班巡遍整个小镇,最多也就个把钟头。可是,省力不省心呐!俗话说,小有小的难处。地方小,人口少,又都是上午不见下午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牵丝攀籐,得罪谁面子上也不好看。再说我刚来还不到二年,马马虎虎刚稳住脚跟,值班万一碰上这档子事,管也不是,不管更不是,岂不难煞人?不过,稍稍迟疑了一下,我还是答应了。你想,镇长亲自交办的事,能不干吗?
根据安排,我和贾所长一组,值午夜一点钟的班。正当我吃好夜饭,准备出门外巡时,一个老头风急火燎地闯了进来。
这老头也就一米六五的个儿,肤色倒挺白。黑白相间的板刷头,前额上印有几颗明显的老人斑。精瘦的“V”形脸上虽然也布满皱纹,但因了那脸的白净,这皱纹犹如那清澈小河中漾起的几丝波漪,显得柔和清爽。一进屋,他就朝办公室桌边一坐,顺手抓起蒲扇用劲扇了几下,眼睛却斜着桌上的小闹钟说:“真差一点儿!还好,提早了五分钟!”
我以为这是来报案的,刚想问话,不料贾所长紧前一步,摇着他的肩胛客套起来。
看你,今夜叫你别来别来……
“你准我假,可我的脚批不准有什么办法呐!”
“你女儿明天不是出嫁吗?”
“哈呀,明天么,她出嫁归出嫁,我喝酒归喝酒,保证两不误。一个老头子,一不会烧菜,二不会待客,混在里头……嘿嘿,就只有喝酒的份喽。”
“可今夜值班已安排好了。你看,镇宣传干事小段就是来顶替你的。”
“他顶我?”老头眯着眼睛扫了我一下,说:“好,那我就顶你。怎么,你值整夜,就不谁我值半夜啊?夜班费大家拿拿嘛。好了,好了,别争了,你去困觉也好,不困觉也好,反正腿长在我的肚皮底下……”
这老头看人时眯着眼睛,说话时也眯着眼睛,不仔细观察,很难知道他的眼睛究竟是大还是小。他脸上老是荡漾着笑意,但那本地话音夹着北方语音的洋泾浜官话中却带着不容分辩的口气。
贾所长大约是了解他的脾气的,看拗不过他,便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没办法,真没办法。实在……咳,小段,你就和老黎辛苦一次吧,我正好还要赶写一个结案报告。”
老黎?我看着那个显得精明的老头,颇感意外地想:他莫不就是那个离休干部黎明?!据说,他是我们镇上唯一的‘解放牌离休干部,原来是上海市政府某部委的副主任,堂堂的市局级干部,三个月前才离休回到这个乡村集镇。在一个放屁响半镇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也满算是个体面人物了,自然断不了成为众人品评的对象。而一个人被观察得久了,谈论得多了,形象自然也就“脱颖”而出。可惜的是,回到小镇才三个月的黎明,形象并不“丰满”,有人甚至赐了他一个“上海八怪”的别名。
所谓“上海八怪”,其一是说他“刮皮”,不近人情。比如说吧,他有个老伴叫杨大嫂,是普通的妇道人家,原先住在老家——县城东部靠海的一个小小的D镇上。五年前,她的女儿杨梅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此地县属仪表厂工作,杨母才随之而来。杨大嫂的穿戴是地道的村妇模样,家里的摆设也简陋得近于寒酸。就这样,别说杨大嫂家有人在外头做高官,就说有个出门寻工资的,人家也不会相信——你想,现在毕竟已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等到黎明离休回来,小镇上的人们听说杨大嫂的老公竟是一个高干时,不由又都为杨大嫂感到愤愤不平了,以为夫贵理当妻荣才是,而杨大嫂的土劲儿一定是她老公过于苛刻逼的。这还不算什么,更使“舆论”不满的是他对待自己女儿的态度。杨梅是他的独生女,长得也标致。高挑个儿,身材苗条,镇上有学问的称之为亭亭玉立。她那甜美清脆的嗓音,使她成了我们小镇上当然的“郑绪岚”。然而人们发现,就这么一颗掌上明珠,老头可并不爱惜。
一个月前,杨大嫂为杨梅置备了五条出嫁被面,想不到横路杀出个程咬金,黎明干预了此事。他只给女儿留下两条被面,其余全被他退给了商店。为此他不惜花费了一番口舌,美其名曰“文明办喜事”。在这件事成为小镇爆炸性新闻的同时,·“刮皮鬼”的雅号也应运而生。
黎明另一个较有特色的“怪”,便是爱管闲事。“张家长,李家短,去问一声阿二家的娘”。这原是流行在我们小镇上的一句戏谑的话。自从来了黎明,便取代了“阿二家的娘”,变成了“张家长,李家短,老黎头心中有本账”。家邻家坊,妯娌夫妻,买者和卖者,路人和路人,谁家有个三言两语,谁人心中的疙瘩有几两,只要他碰到、晓得,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总爱去听听、聊聊、管管。有一次,他发现女儿的月奖比平常多了十元,就一五一十地追问厂里是以什么名目发的?结果,他管闲事硬是管到了女儿厂里,全厂职工多领的奖金被追回不算,厂领导还多拿出了一张纸头:一份黑字白纸的检讨书。管这种闲事,别说人家骂他“缺德”,就连一向温顺听话的女儿也熬不住嘀咕了几声……
唉,老同学,你想想,人有“两怪”就已经够呛了,何况“八怪”呢!当然,关于他的“怪”都是“据说”,不足为凭。但“无风不起浪”,不怪说怪,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那夜,我初次同黎明接触中,也的确闻到了一点“怪味”。你想,堂堂的离休干部干什么不行,偏偏要揽这个“夜出世”的活儿;再说,明天如花似玉的独生女儿、掌上明珠要出嫁……说他是为几角“夜餐”费,未免也太那个了——老头每月一百几十元的工资,平日再“刮皮”也不至于这样;说他思想好,想为治安工作出点力,为人民服务,这岂非更怪!其实,那不过是时髦的口号罢了。六十年代的雷锋我没见过,八十年代的朱伯儒、张海迪我也未碰到过,黎老头大概也未必真会照报纸上写的、广播中说的那样……
对这种联防队值班,我本来就不那么顺心,偏又搭上个怪老头,就别提有什么共同语言了。老同学,以你我四年同窗,我当时的心境你是可以想见的。在巡视的路上,我只是“跟”着黎明,不发一言。可他倒挺来劲,话还特别多,说得不中听,就象吃了隔夜螺丝的老太婆。岁数啦,学业啦,工作啦,家庭啦,朋友啦,性格啦,爱好啦,平时常谈论些什么啦,朋友中有谁犯过错误啦……喔哟,真不得了。对这种外调式的交谈,我只能“嗯嗯啊啊”,可他呢,问七问八,竟一路问到我的根上来了。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是怕了吧?怕鬼呐怕人?怕生人还是熟人?小段,你不说,我估计得可八九不离十,你准是怕熟人!其实么,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喽,一是一,二是二,咬咬牙就过去了。眼前正在严厉打击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作为共产党人、国家干部可容不得半点情面观念呵!
说实情话,对黎明敏锐的观察力,我倒禁不住有点佩服了。但从这位怪人嘴里吐出的这通人人都会讲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是显得很滑稽么?所以,我打定主意,既不表白,也不抗争,只是一味敷衍下去。
晚秋的深夜,扯紧警惕的神经,漫步在这江南小镇,这在诗人或许能触其诗兴大发,但对第一次巡夜的我,却充满着神秘感。群星争辉的碧空是神秘的,掠过田野吹来的带着湿味的凉风是神秘的,转弯抹角的暗弄小巷是神秘的,而他那娓娓的话语声则更给神秘的秋夜平添了一分神秘。
在昏黄的路灯下,我们俩——一老一小,一前一后,拖着两条长长的黑影,踩着长条石铺成的街面,慢慢悠悠地四处转着。来到东街末梢的一座桥堍下,黎明忽然止步,神情有点异样地凝视着斜对面两间还亮着灯火的平房。在国庆节前夜,象这样的灯光何止此家,老头怎么独独对这户人家发起愣来?八成是又犯开“怪”劲了。
老头大概察觉到了我的不满,便看了我一眼说:“这是我的家。”
“过节的日子,一般都睡得晚。”
老头似乎并不理会我的话,顾自说:“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离开这个家喽!”语调中不无感慨,“娘俩有多少话要说啊!咳,二十七啦,翅膀长全啦,明天就要飞了……二十七”,他摇了摇头,“算起来,我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日子恐怕还不足三年,离休回家,本想……咳,在我眼里,她总象一个长不大的小囡,可明天倒要出嫁了……”那窗里溢出的灯光映洒在桥下的水面上,随波摇动着。
“那你……”我本想诘问他,既然这样,今晚为何不呆在家里念念“女儿经”呢?转而一想,人家毕竟是离休干部,年纪又大我一辈,况且又“怪”味十足,问他何益?所以一句话吐了两字就又吞了回去。
黎明似乎明白我的意思,说:“当然想同女儿多聚聚,多谈谈。女儿是娘的心头肉,也是做父亲的心头肉嘛。”他恋恋地将目光从那亮着灯的窗口收回,双手反背,一边朝十字街方向踱去,一边继续说:“可嫁女儿事小,值班事大呀。虽说中央两个‘决议颁布后,社会治安比以前好了,但还是麻痹不得。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万一我们鼻子底下出了事,那多不好唷。女儿嘛,好在嫁不出这个镇,能常来常往的……我听他这么说着,嘴里只是慢应着,可心里早起了疙瘩。心想,他不是怪人是什么?有福不享,偏要……大概实在是闲得难受了吧!
我们慢慢走到了小镇上唯一的十字街口,接着又踅向了旁边一条小弄堂里。
这是一条只有近二米宽的小弄堂,再走进十几米,便又有二条更窄的弄堂,呈“丫”字样叉开去。右边一条曲曲弯弯,一直延伸到小镇边缘;左边一条是死弄堂,五十来米长,两边一式五六米高的老式双壁围墙,弄内没有路灯,唯有天际璀灿的群星给这条黑黝黝的弄堂洒进些微的光亮。
当我们走到一个三条弄堂的交叉口,黎明突然站定,憋住气,眯起眼朝那条死弄堂里横看竖看起来。“那个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他颇有点紧张地拉住我的胳膊,指着阴暗的弄堂对我耳语。
我探头探脑地仔细辨认了一会,不禁暗暗竖起了汗毛——这不是人是什么!还蹲着!这下我犯难了。实说吧,黎明肯定要去死缠不清;不说吧,万一那家伙真是个犯罪分子,我又担当不起纵容犯法的罪名。所以,我只得含糊地说:“好象……嗯……看不太清楚,再不,咱们咋唬几声……”
这个老黎头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怯懦,眯着的眼睛里闪射着光亮,朝我深深地瞥了一眼,压低声音却带有责备的口气说:“怎么能喊呢?我去看看!”
他果断地走了,挺着他那干瘦的身躯。留下的只是在这夜幕下的深深一瞥,象上空的星星,光辉闪亮……当自我意识要选择某种可能付出代价的行为时,犹豫便会象毒藤一样缠着你,使你寸步难行。终于,我没有跟上老黎头。就在这踌躇之际,本来也许能避免的惨案发生了。
“小段……”我忽听到黎明低沉而急促的呼唤,便情知不好,拔腿向弄底扑去。到那儿一看,我傻眼了。地上满是亮晶晶的手表,而老黎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半倚在墙根下,双手却使劲抓住黑暗中一个人的右手;那人则单腿跪在老黎的左侧,身子拼命仰着、扭着,左手对着老黎的头部乱捶,就象一匹被夹子夹住的狼,竭力想挣脱……我的天!顿时我只觉得头脑倏地一胀,狂叫一声便扑向那家伙,抡起右拳疯狂地打击那颗罪恶的脑袋……
可是天啊,你知道这个罪犯是谁吗?说来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黎明的亲侄子。老黎的侄子住在D镇,也就是杨大嫂原来居住的那个地方。这次他的侄子是赶来吃堂姐的喜酒的。照这里的习俗,相隔两地的表兄妹、堂姐妹一般是不去庆贺同辈人的婚礼的,但因为黎明的弟弟死得早,黎明自己又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一向把侄子当亲子抚养。谁知这个侄子不成器,轧上了坏道,常干一些偷鸡摸狗之事。这次趁着来吃酒的机会,竟撬窃了小镇百货部的钟表柜台。不巧,撞上了自己的亲伯伯。那个不争气的侄子先是求之于情,哀求黎明顾念死去亲人的情份上,放他一码;后又说,愿意将所盗之物放回柜台,以后决不再偷……他以为自己的伯伯只是面子上过不去,还不至于真送他到派出所去。然而他想错了,黎老头是凡事认真朝前,何况对这偷盗国家财物的行为!后来听贾所长说,老黎的侄子还有前科,是漏网之“鱼”。
唉,罪犯最后算是被我抓获的。但老黎却从此走了,永久地走了。走的这样突然,这样匆促,来不及跟相处几十年的糟糠之妻打一声招呼,顾不上看一眼即将出嫁的爱女……啊,昔日被视为“怪人”的他从这个曾被自己热诚维护过的小镇上消失了,而昔日“自我意识”极强然而卑怯的我,却留下了……唉,这是多么地不公平啊!
那天下午,县里开完了表彰大会,我又一次来到老黎的坟前,把奖杯埋在了墓碑底下——这原本不是应该属于他的吗!
晚秋傍晚金黄色的霞光格外耀眼,给镇西头小土岗老黎的墓上涂上了一层明丽的色彩。四周有几棵柏树,使这片死者的领地增添了几分肃穆。我久久地伫立在墓前,难免触景生情,回味着同老黎短短两小时交往的一点一滴。他可真是个好老头!
太阳终于沉落了下去,在天边留下一片绚丽的余辉。面对老黎的墓碑,我想自己今后唯一要做的便是:彻底埋葬我的“故我”!
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家时,竟在街头巷尾发现了我过去的影子,看到了第二、第三个“故我”。我听到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模样很斯文的青年正用轻佻的口吻谈论着老黎的死:“哈,老怪人死得真没意思,坑了亲侄子,倒给旁人捞了便宜……”另一个青年搭讪说:“嘿,就这么个怪法嘛!要不,怎么叫“上海八怪”!
你听听,这才是真正的怪物讲的真正的怪话呢!当时,我真想冲上去扭掉那几个家伙的脖子!可我过去不也这德性吗?我默然了,回家后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我虽然有信心埋葬我的“故我”,可没法埋葬“故我”的影子。什么悲伤啦,愤恨啦,忏悔啦……于在天之灵有什么安慰?于现实生活又有何裨益呢?
忽然,我记起了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而写的自传作品《忏悔录》中说过的一句话:把自己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揭露!我也要扯开我思想的拉链——不是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黎明的存在——把“故我”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健康人看了感到厌憎,让“故我”的影子看了自愧,让刚走上社会的朋友引起警惕和深思。让变态的“自我意识”见鬼去吧!!
老同学,刚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你在《当代青年》从事编辑工作。如能借助贵刊发表此信,这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恐怕都是一种安慰……
我合上了信。沉思中仿佛看到老黎就站在眼前,同样向我投来那审视的目光……啊,小镇上空闪亮的星星,深邃的夜空不都在感受着您那晶亮的光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