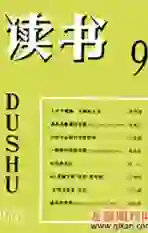谈新译《大卫·考坡菲》
1983-07-15王治国
王治国
狄更斯自己说过:“我有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考坡菲》。”如果我们从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深度和艺术成就来看,这确是狄更斯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有人简单地把这部书归结为自传或“自传体的变种”(苏联英国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在其编著的《英国文学史纲》中就持此说),则不免又失之偏颇,贬低了这部作品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这部作品不仅是狄更斯创作力最旺盛时期的产物,而且它的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涉及了当时英国的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司法和政治制度的一些症结,可说是在英国史上号称盛世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情况的实录。狄更斯在酝酿这部作品时,的确曾打算写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但写了一部分后,他感到无法把广阔的社会现实容纳进去,因此改弦易辙,写成了一部虚构的传记体小说,以间接的形式大量表露其童年生活的不幸,而其中绝大部分情节,是由艺术的虚构所成。
《大卫·考坡菲》在我国已有多种译本,就我所见,最早有林纾的译本,以后又有董秋斯、许天虹、林汉达等译本,它们各有长处。近出张谷若的最新译本《大卫·考坡菲》,无论从对原文的理解、风格的表达还是文字的流畅和典雅来看,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水平,应该说这是目前狄更斯这一名著的最佳译本。它既不是信笔而译意,也不是着眼于逐字逐句的对译,而是在深入领悟原书之奥秘和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上,用优美、得体的文字从原文
张谷若先生翻译的哈代作品脍炙人口,咸皆称赏,可是哈代的创作风格和表现形式与狄更斯不尽相同,前者缜密、严峻,后者粗犷、幽默,如果用同一笔调来翻译哈代和狄更斯这两位大家的作品,就会湮没这两位名家各自独特的风格。这决不是弄懂文字就能翻译的,必须事先经过一番周密的推敲才行。张先生在译述狄更斯这部名作时,的确能做到深琢细磨,别具一格,即使在一部作品中,翻译时也力求注意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语言,务必用适合的文体译出,不是千篇一律,因此有时平易朴实、有时幽默轻松、有时鬯达明丽、有时则端庄深沉而别有韵致。如书中有位怀才不遇的米考伯先生好卖弄文才,因此在译他的信时则采用比较古板的文字,一则可以寓谐于庄,另则更能依照文意表露米考伯的个性。狄更斯模拟人物身份的挥洒自如的文笔,由译者用恰如其分、精心构撰的道地中文译出,尽量吻合原文的语气,可谓旗鼓相当,相得益彰。和上述同样的情况还有不少,兹不赘引。
狄更斯在作品中喜欢旁征博引,涉及面很广,一般读者不易理解。对此,张译本在脚注中较详尽地对一些理解作品有关的重要人地名、典故、民间习俗、典章制度、成语、谚语和难以理解的寓意等加以诠释,颇便读者。
当然,本书亦非尽善尽美,如书中有些译名的字形就值得斟酌。书中译名所采用的字在中文中不大用作姓名,容易和前后的字串读在一起而生歧义,并且有些译名的发音和原文也有一定距离,如坡勾堤(Peggotty),周阑(Joram),提费(Tiffey),批治(Pidger),道对(Doady),破费先生(Mr.Copperfull)和诺锐直(Norwich)(地名)。此外,书名“DavidCopper-field”以前的译本和英国文学史的中译本通常译作《大卫·科波菲尔》,似仍可沿用,似没有必要另立新名。
(《大卫·考坡菲》,张谷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上册2.05元,下册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