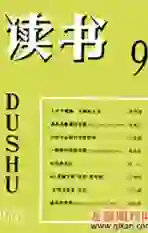加姆扎托夫/邵肃
1983-07-15凤子
凤 子
《人世间》随想
我接编过两次《人世间》。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夏在桂林,一次是一九四六年秋在上海。在桂林是丁君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事变,香港的地下组织把“旅港剧人协会”全体人员接送出来,经东江游击区到达桂林。我是“旅港剧人协会”的成员,要在桂林等待组织的安排,就暂时在桂林住下来。这期间“旅港剧人协会”整理演出了《北京人》。
在桂林的时候,出版人丁君
丁君
桂林版一卷一期有一段编者赘语,兹摘引数段,可以看出当年改版的目的和编者的意图。
(一)本刊内容完全改革为纯文艺性的
(二)A、(从略)
B、文艺创作方面,除特约作家撰述外,尽量刊登青年作家来稿。
所谓纯文艺性者,一则区别于《人间世》原来的面貌,实则是堵审查老爷的口。特约作家撰述是做到了的,尽量刊登青年作家来稿是很好的愿望,但记不得有未发现多少青年作者。
用编辑封凤子的名字,刊行的桂林版《人世间》,第一卷出版了六期,第二期刊期是十二月十五日,等于是双月刊了。第三期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而第四期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五期是是年五月二十五日,而第六期则拖到是年十一月五日,相距一季或半年才出刊一期,虽然当时我早已回到重庆,编务完全委托给周钢鸣,而一卷六期前后竟拖了一年多,说明抗日战争时期编辑出版刊物的困难到什么程度。
桂林版《人世间》在我离桂后,仍继续撑持到桂林撤退,一直是周钢鸣、马国亮负责编的。
一九四六年冬,在上海,我已结束了编辑《和平日报》副刊之一三日刊《海天》之后,叶以群同我谈,试找丁君
内战时期,要编辑出版一个刊物,这决不是什么个人爱好,从兴趣出发的同人刊物。国民党扼杀民主自由的手段是难以想象的,共产党的《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出版不到两周就遭到禁止,《新华日报》根本不让复刊。要登记出版一个刊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复刊《人世间》,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得到了批准。
当时有了出版证,还要办登记手续,掌握审查刊物出版登记权的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经过多方了解,我托人介绍才认识了上海社会局的局长李建华。解放后才知道李建华是中共地下党员。
登记获准,第二步就是经费了。经费来源之一是广告。广告除新拍摄的影片预告外,大都是与文化无关的。如煤号、运输、银行、饭店……等等。现在看来可笑,当时为了拉这些广告,冯亦代是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的。这些广告确实是维持一个刊物的一大支柱。另一来源是募款,当时出得起钱的决不是文化人,我们找过官场失意转业到商业方面的各种人等。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我们通过种种关系,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捐给了《人世间》一千元法币。孔祥熙根本不知道《人世间》是个什么性质的刊物,也根本不认识我们中任何一人。当我们拿到孔祥熙签名的一张某钱庄的钱票时,我从代表组织的叶以群的这一决定,领会到“动员一切为我所用”党的这一策略的意义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斗争的领导艺术。
据说孔祥熙这类反动大官僚,也曾出资资助过中、外人士办的刊物,目的当然是为了树立他个人的社会威信。可笑他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一千元的“投资”是不利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
《人世间》从一九四七年四月复刊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止,共编辑出版了两卷零一期,一卷是六期。为什么两年多只出版了十三期?原因很简单,是经费拮据。经费开支主要是纸张、印刷和稿费。一位编务秘书,每月车马费法币二十元。编务秘书姚平统管有关编辑的一切行政事务,包括通讯、联络、财会、下厂、校对等等。第一卷作为月刊,做到按期出版,工作是比较正常的,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一年多时间只出版了七期,近乎是季刊了,其原因不言自明。
我们的主编和编委当然都是义务的。头两期的编委是丁聪、李嘉、马国亮。第三期起,李嘉离沪,冯亦代参加了编委。每期定稿都经过编委会,每期出席编委会的还有一位不具名的编委叶以群。
我们每月召开一次编委会,也就是定题和发稿会。决定发的稿件早在上一次编委会上议妥,分头组织来的稿件早已交换审定,发稿会一边研究个别需要讨论的文章和下一期选题,同时负责版面的漫画家丁聪就当场画了版式。会完,就由编辑秘书送印刷厂。丁聪不仅负责版面设计,每期的封面到扉页的美术设计和有的文章的刊头与插头都是他一人“包办”的。
上海复刊的《人世间》,是一个综合性刊物,为什么要办成综合性的?复刊辞中有一段话抄录于下:
上海复刊的《人世间》,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这可能使一部分读者、作者们失望,但,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上海,出版事业较之任何其他事业的遭遇更惨。纸张、印刷、排工,随着物价变动,物价是一匹脱了缰的马,“一日千里”,我们的经济力量实在无法追上物价。不用讳言,爱好文艺的读者们多数是穷朋友。好在综合性刊物,不妨碍我们精选几篇文艺作品,同时,多样的形式可以获得更为广大的读者们的支持。
在桂林出版的《人世间》,强调它的纯文艺性,可是五年后在上海复刊时却又改为综合性,不是我们不坚持办刊物的宗旨;要争取生存下去,为了坚持斗争,文艺刊物作为战斗的阵地,就不得不改变策略。从《复刊辞》里多少可以传达出编者的苦衷。
作为综合性刊物,内容有小说、诗歌、通讯、特写、报告、杂文、剧作、绘画以及译文等,发行由利群书报发行所总经售,外地只有北平朝华书店特约经售,事实上大多是分发到街头书报摊上零售的。印数多到四千册,这在当时是个中等数字。撰稿人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翦伯赞、沙汀、欧阳予倩、景宋、吴组湘、丁玲、许寿裳、姚雪垠、徐迟、赵超构、顾一樵等。
《人世间》上刊载的文章,除了我们就地组织外,部分是叶以群主持的中国文化联络社(简称文联)提供的。中国文化联络社是在太平洋事变后,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间在重庆成立的。社长茅盾,总编辑叶以群,总经理冯亦代。设立这么一个文化机构,是为了组织解放区的和国统区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供应给海外华侨办的报刊。当时代表组织出面的是叶以群,这个机构的设立,是随着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周副主席批准的。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斗争还在继续,中国文化联络社的任务也更为繁重了。
当时办刊物是奉组织的命,是革命的需要。来自组织的指示是:“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我们这些搞文艺的都一直是在党的外围工作,这是“人心所向”!所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最怀念的是在上海每月举行一次的编委会,开的那么痛快,那么别致,也真解决问题。当时来稿虽然不多,但总得负责处理。当时看来稿的任务我包办了,同时我们还要分头组织文章,或者分工写文章。编委是名义,却绝非挂名。我们谁也不拿报酬而都负责一定的编务,甚至还要掏钱应急。为了生活,我们都有一个职业,当时我就在昆仑影片公司文学组工作。我们把刊物当作事业,没有什么编辑部,开会就在我住的虹口的一所房子里。编委会一开会就是一天,中午就上虹口小馆吃点东西。今天翻看当年的刊物,就版面看,做到活泼多样,内容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精神面貌。例如一九四七年第五期,为了纪念为民主革命大声疾呼以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闻一多先生,发表了一组“周年祭”文章,有郭沫若、凤子、流金、王
中国也快要天亮了,普天四海将要看见无数金的、石的、石膏的、木的闻一多。
你是一粒健全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天亮,随着太阳光的照射,普天四海而且万年永劫,将有无数无数活的闻一多。
由一而多,你的名字和你自己一样,便代表了真理。
我现在不是纪念你的死,而是庆祝你的生。
闻一多先生万岁!
这一期的扉页刊有丁聪的素描《闻一多画像》,这幅画像画出了这位烈士的反抗精神。
《人世间》还发表了揭露国民党经济崩溃,金元券贬值的讽刺喜剧《万元大钞》。汪巩创作的这个独幕讽刺剧当时在上海舞台上曾起过有力的鞭挞作用。
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友,为《人世间》写了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许先生不幸逝世,《人世间》特发了一组景宋等悼念许寿裳先生的文章。
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严的,从《人世间》的版面上挑不出遭忌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国民党已是自顾不暇了。否则那些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的丁聪的漫画、雪峰的寓言就会被开天窗或者禁止出售了。
解放后,虽然大多时间是站在编辑岗位上,可是总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有负于组织的委托和信任。迫切要求自我改造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愿望,而不能辩证地分析一切事物,对走过来的革命道路轻率地给以全盘否定,这也是失去信心的又一基因。
写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应该予以分析,对历史要有所扬弃,有所借鉴。我们不要被历史的灰尘迷住了眼睛,也不要把历史埋藏在灰尘里而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
回忆三十五年前、甚至四十年前的事,许多都淡忘了,手边又缺资料,自己编的刊物,仅留下《人世间》两卷,而“文革”中上交给革命群众审查,落实政策时只退回一卷一至六期的合订本。七期至十二期的合订本据说没有了!问谁去呢?这样的一场浩劫,丢失了一个刊物的合订本又算得什么呢!
一九八三、一、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