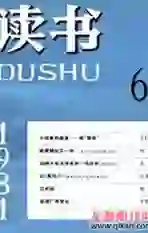关于新与旧的相互关系的光辉思想
1981-07-15许征帆
许征帆
在乌托邦主义史上,德尼·维拉斯这位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塞瓦兰人的历史》,究竟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有很大出入的。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虽风行一时,其实“其基本思想是很少创造性的,大部分都从莫尔和康帕内拉那里借来的。”(麦克斯·比尔:《社会主义通史》第八章第五节)有人则认为:“凡熟悉十八世纪社会理论的人都清楚知道,维拉斯的体系已经包含着十八世纪最流行的观念的一切基本因素。”他“是十八世纪共产主义作家的先驱和导师。”(维·彼·沃尔金:《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位空想主义者》)现在,我不准备就这些分歧发表意见,只想按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阐述《塞瓦兰人的历史》一书中若干值得重视的光辉思想。
维拉斯笔下的理想国,确实处处可以看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糟粕:在那里,国家的最高主宰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宗教愚弄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而高级官吏则拥有自己的猎区、奴隶,并且允许多妻,公然实行特权制度;在那里,奴隶占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有生产奴隶、家奴、甚至实际上是娼妓的女奴,战败国被迫每年进贡男女青年以补充奴隶的队伍,用对外的“殖民主义”来支持内部的奴隶制度。这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比起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
但是,糟粕毕竟是糟粕,它掩盖不了维拉斯思想中的某些精华。我认为:《塞瓦兰人的历史》中有关新旧两个世界的又有斗争又有交往的相互关系;塞瓦兰国的开创者与继任者之间的又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相互关系;塞瓦兰人的前辈与后辈的那种又肯定其血缘联系又破除其财产继承的相互关系等等,都是有关新与旧的相互关系方面的创见。有必要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时,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理想社会制度进行空想的描写。故事往往是这样开始的,一个来自旧世界的航海家、旅行家偶然地发现了某一个新世界。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想象中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并存的局面,产生了这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莫尔、康帕内拉都曾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个问题。他们的“乌托邦”、“太阳城”都与邻国打过交道:或互派使节、或结盟、或交战。但他们讲的多半是关于新世界的战争观、爱国主义,及其克敌制胜的强大的军事力量、高昂的士气、英明的战略策略。只有维拉斯在解决新旧世界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
维拉斯和莫尔、康帕内拉一样,一再赞颂自己的理想国是“古往今来的国家制度的楷模”(《<塞瓦兰人的历史>告读者》),是“一个一切都美妙绝伦的国家”(同上书第二章第89页),“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同上第三章第183页),因此,当然要警惕地“守卫自己的疆界”,防止“外国人会采取卑劣的手段来破坏他们的安宁和纯朴,或者使他们染上外国的恶习。”(同上第一章第74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维拉斯在强调防止旧世界的武力进犯与思想腐蚀的同时,一再指出,旧世界并非一无是处,对新世界来说,它决不是毫无值得效法的东西。他说:“鉴于在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中间也往往会遇到在政治、科学和艺术方面拥有优异才能的人,所以塞瓦利阿斯(塞瓦兰国的开创者、太阳王总督一世——引者注)认为,为了避免沾染他们的恶习而忽视他们的可取之处和有益的发明……,那是不明智的。”(同上第二章第110页)因此,国家从“学生中选派一批人到欧洲大陆去研究有益的一切科学。”(同上第三章第188页)甚至军队中的大部分制度都是从欧洲学来的(同上第114页)。历届太阳王总督命令人民普遍学习波斯语,派遣精通此种语言的人化装为波斯人、取道波斯到其他各国去旅行,“去发现一切重大的事物,以便从考察中汲取一切对我国人民用之有益的宝贵经验。”(同上第二章第110页)维拉斯以塞瓦兰人的名义这样写道:“我们就是这样通过派往亚欧大陆去的人……随时了解亚欧大陆最著名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精通了各国的语言,获得了这些国家的各种科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按照我们的看法,是能促进我们国家人民的幸福的。”(同上第110页)
维拉斯的这些见解,是何等精辟呵!至今读来仍然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在饱尝“闭关自守”的苦头之后,深深感到:在与资本主义旧世界打交道时,如果“为了避免沾染他们的恶习而忽视他们的可取之处和有益的发明”,那的的确确是“不明智”的。
维拉斯之前的、以及与他同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他们各自的理想国的领导体制,都作了许多既有趣又有益的设想。譬如说,温斯坦莱就拟定了一整套民主选举、群众监督、定期轮换公职人员的措施,实际上废除了终身制。维拉斯把这方面的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比较详细地研究了理想国的开创者与继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新贡献。
我们从维拉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塞瓦兰国的开创者在他七十高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力已经衰退,难于掌握政权了,要是选举一个比他年轻力壮的领袖来管理国家,那将是对社会有利的。他已为了民族的富裕和幸福工作了三十八年,因此想到告老退休也是正当的。”(同上第三章第165页)于是,他决定把政权禅让给别人。尽管这种禅让被涂上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根据所谓“天意比人意更重要”采取抽签的办法(这实在有点荒唐),但重要的是,塞瓦利阿斯毕竟是自动让贤了,而且非常坚决地拒绝了那种要把“太阳王总督”的称号传给他儿子并在他的家族世代相传下去的建议,“他的美德在这个场合下战胜了人类智慧的一切弱点。”他知道,“当事情关系到社会利益时,必须放弃骨肉的感情,必须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同上第166页)
塞瓦利阿斯并没有把禅让变成退居幕后进行操纵的把戏,他对自己的继任者说:“昨天你还是我的臣民,而明天你就将成为我的统治者;我自愿离开宝座,而你将毫无阻碍地登上宝座。”(同上第167页)在举行禅让大典的那天,他领着自己的继任者登上宝座,“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把权杖递到他的手中,接着就第一个向着这位新即位的太阳王总督参拜。”(同上第170页)在他摆脱政务以后的十六个年头里,他是作为一个不问世事的平民安逸地度过晚年的。
维拉斯就塞瓦兰国的开创者与继任者之间的那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相互关系所发表的意见,很值得注意。他一方面强调指出,塞瓦利阿斯“严禁他的继承人推行任何与自然法或国家根本大法相抵触的法律”(同上第162页),具体说来,“民族是以大家庭(公社)的形式而生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财产所有权转入私人之手”,“官衔和称号不得世袭”、“人们的出身一律平等”,“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好逸恶劳的坏现象”(同上第162—163页)等等都是必须坚持、维护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说:“虽然这位伟大的立法者自己奠定了法律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建立塞瓦兰人现今所实行的一切制度,而是授权他的继承人去建立。可以根据情况来改变、增加或删除法律,如果他的继承人认为这对民族幸福来说是必要的话。”(同上第162页)显然,这是赋予继任者在遵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经验进行创新活动的大权,这对推动国家、民族的建设大业前进,是十分必要的。
在维拉斯看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根本原则而进行的创新活动是可贵的,而否定根本原则的篡改行径则是可恶的。他认为塞瓦兰国的根本法是英明的、是不会改变的。“要尊重它们的起源,要谨防作任何的篡改。”(同上第169页)他说:“万一总督变成一个凶恶不仁的暴君,企图破坏国家的根本大法,那末这时就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劝谏他,如果对他的劝谏最后仍然无效,那末这时就由最老的塞瓦罗巴斯召集总会议,把这种情况向大家宣布,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需要由总会议向太阳神请求选出一位摄政王,以便代理国政……”(同上第180页),在推举出摄政王之后,总督就被看作是“丧失理智的人”,“此后,他就没资格参加总会议了,而被安置在冷宫中。”(同上第180页)
维拉斯在阐发塞瓦兰国的开创者与继任者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夹杂着讲了一些塞瓦兰人的老一代与新一代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涉及上至领导层、下至老百姓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育、培养、财产、爵位等等问题。
在塞瓦兰国,儿女不是父母的私产。他们出生之后,准许由双亲抚育一段时间,这时,父母可以对自己的“爱的结晶”表示“最初之爱”。孩子满了七岁,就得送进公共学校,交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去培养,“这些人对待儿童一视同仁,既不溺爱,也不憎恶,只是通过说服、赏罚、示范等方法来教育儿童分辨善恶,要他们弃恶从善。”(同上第185页)孩子入学后,为了不让父母妨碍导师履行自己的职责,法律规定他们必须放弃做父母的权力,而把这种权力移交给国家及其公职人员。
我们已经讲过,在维拉斯的理想国,公职人员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这些特权被认为是本人贡献的酬劳(实际上,远非贡献的酬劳,而是名副其实的特权),后代不得无功受禄,换句话讲,他们的官衔、称号、财产一概不得传诸子女。他们“也不必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发财致富、为了安排女儿出嫁或为了赎回遗产而积聚钱财。”(同上第182—183页)“他们遗留给子女的仅仅是值得模仿的良好的范例。”(同上第179页)塞瓦利阿斯在临终前“便告诫自己的子女要忠于职守和热爱祖国,并向他们指出,只有遵守法律、大公无私和善于节欲,才能获得真正的荣誉。”(同上第171页)
维拉斯在自己的理想国中给公职人员保留的特权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想在这些人的第二代就全部彻底地否定掉这种特权成为很困难的事情。他书中多次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公职人员的子弟和平民的子弟都得靠功勋来升迁,一方面又容许塞瓦利阿斯的子弟比其他家族的子弟提早三年担任国家职务;一方面规定人们出身一律平等,一方面又说有人出身高贵、有人出身低微,有贵族、非贵族之分。当然,维拉斯竭力说明,“他们或者是贵族,或者是非贵族,但没有一个人因自己出身低微而受到贱视,也没有一个人因自己出身高贵而骄傲自大。谁都看不到有一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另外一些人却为了他们的骄傲和虚荣心而工作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同上第183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拉斯力求论证生活在塞瓦兰国的后辈是不可能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吃现成饭的,即使还有特权的遗迹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改变不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维拉斯关于新与旧的相互关系的这一系列光辉的思想,在十七至十九世纪,并不是他的著作中最引人瞩目的东西。当时,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居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最为关心的是破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当这个伟大的阶级着手解决新世界与包围着它的旧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开始处理新政权的领导体制、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接班问题,以及革命胜利前后两代、直至三、四代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时,维拉斯的上述思想,自然要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其中渗透着幼稚的幻想和各种各样的糟粕。
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维拉斯既然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提供了一些他的前辈未曾提供的东西,他的功绩当然是应予以肯定的。至于功绩究竟多大,用不着急于做出结论。
(《塞瓦兰人的历史》,汪裕荪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三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