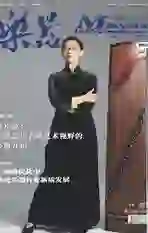陈锦农:一生钟情斯氏提琴
2025-02-18孟建军/编写



1980年,陈锦农首次代表中国参加美国第四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他参赛的提琴是用国产木材制作的一把红棉牌高级小提琴。比赛结果出炉后,陈锦农参赛的提琴一举荣获音质金奖,陈锦农成为首位获得该项提琴制作比赛金奖的中国人。
1929年,陈锦农出生于广东南海。童年时,陈锦农离开家乡,在广州一家皮匠作坊当徒工。一天他奉父母之命去探访本家一位堂兄,堂兄是木匠,时常会从市面上买回一些破旧的木箱板,用来制成一些小提琴来出售。陈锦农对这门手艺一下就着迷了。他天性喜欢音乐,对提琴制造这门手艺感到特别亲切,于是他就赖在堂兄那里不走了。堂兄心里思慕着自己有个帮手干活也方便,于是就让陈锦农留了下来。那时他们两兄弟技术平平,做出来的琴外观并不精细,工艺和音色与专业提琴也相去甚远。
1951年,热爱乐器制作的陈锦农竟然如愿踏进了广东乐器厂的大门,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乐器制作领域,开始了他崭新的制琴生涯。
1958年,国家轻工业部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了全国首个高级提琴制作培训班,广东乐器厂选送陈锦农等三位年轻的工人前去深造。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主持下,陈锦农接受了全面系统的提琴制作理论、工艺和技术基础教育的学习。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陈锦农顿觉视野开阔,体会到了知识海洋的深奥与博大。陈锦农从许多提琴史料中,了解了提琴发展沿革的历史,也看到了意大利三大制琴家族一件件历久弥新的提琴作品,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令陈锦农眼界大开。在学习期间,陈锦农暗下决心:努力汲取提琴制作知识,争取制作出精美的小提琴,努力为国争光。
三个月的培训时光很快过去了。陈锦农和另外两位师傅共同完成的毕业习作,受到学院的嘉奖和谭抒真副院长的好评。谭抒真副院长曾对接受培训的学员说:我国高级小提琴的制作就寄希望于你们了!这句语重心长的话,陈锦农始终牢记在心头。
斯特拉迪瓦里在意大利三大提琴制作家族(阿玛蒂、斯特拉迪瓦里、瓜奈里)中具有崇高、独特的地位。在陈锦农眼里,斯特拉迪瓦里作为制琴巨匠,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陈锦农从上海学成归来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然而如何才能把学到的东西落实在工作中?如何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非同凡响的作品?陈锦农提醒自己:只有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才能有所作为。制琴之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练就过硬的技术。一个没有深厚制作技艺、艺术修养和品鉴能力的人,不可能够制作出被专业人士认可的提琴,因为每一把专业级别的提琴,都凝聚着制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提琴制作精髓。
在选择标准器型时,陈锦农毫不犹豫地选定斯特拉迪瓦里1722年~1725年的巅峰时期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和仿制的蓝本,他决心把继承克雷蒙纳的制琴风格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当年,国人手中缺乏外国提琴资料,更鲜见意大利名琴实物。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一位独奏家来华演出,听说他用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精品小提琴演奏,陈锦农很想一睹这把名琴的真容。当时他天真地以为,只须通过外事部门出面,凭着兄弟般“友好”的关系,定能如愿以偿。哪知这位高傲的演奏家不讲情面,打消了陈锦农想看名琴的念头。这件事令陈锦农耿耿于怀。
有一年,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医生到广州乐器厂,他想请师傅们帮忙修复一下他的老琴。当老人家打开琴盒取出这把支离破碎的老琴后,在场的师傅都惊呆了。只见这把琴的琴头、面板全部断裂,琴的底板也被虫蚁咬蚀成蜂窝状,密密麻麻的孔洞触目惊心。在常人眼里,这就是一堆朽木,没有任何维修的价值。而陈锦农依稀从中辨认出这把残琴有意大利克雷蒙纳时代的余韵,于是便接受了修复的请求。陈锦农为何如此稀罕这样一把破琴呢?因为他太需要从老琴的实物中获得直观感性的知识,只是多年来苦于没有机会罢了。
当年有关提琴制作资料奇缺,更是难得见到一把真正由意大利大师亲手制作的提琴,因而,无论仿制斯式琴还是瓜氏琴,全凭一些数据。
面对这把残琴,陈锦农和同事们抓紧时间开展研究分析,边修复边进行实体解剖,从琴型结构、木材质地,琴板厚薄和弧度,都作了细致的记录,掌握了意大利老琴的第一手资料。
在十年动乱期间,陈锦农从工厂下班回家后,一头钻到小阁楼里,不是钻研制作工艺,就是聆听唱片,以此躲避外面世界的喧嚣。电唱机是他向朋友借来的,快到了归还的时间。他多想有一台自己的电唱机。然而三代八口之家,全靠他和妻子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手头拮据哪有余钱去满足自已的奢望?为了能买电唱机,陈锦农每天省下早点钱,只为“勒紧肚皮,满足耳朵”,省吃俭用的他终于积存起几十元钱,兴致勃勃地买回一部206型电唱机。没有唱片,他就通过音乐老师的关系,跑到音乐学院借到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唱片,如饥似渴地聆听。通过品味名家的演奏,增强自己对提琴声音品质的辨别能力,以确定自己认为理想的音色。
一次,陈锦农下班经过广州的海珠广场,街头喇叭上播送着一组小提琴独奏曲,令他不由自主地驻足聆听,直到音乐结束,他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后来他得知,这是新上映的罗马尼亚音乐故事片《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里面的插曲。陈锦农得知这部音乐片正在广州上映,于是他下班回家后连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往电影院。这部影片他连看了数场,他被影片中的提琴音乐所吸引和征服。影片中小提琴爆发出来的音波、反射力和折射力是那样的强烈,音响性能极佳,令人叫绝。他想: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由人的双手创造的,只要经过努力必能达到这个高度!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撞击着他,他暗下决心:此生一定要制作出音色优美的小提琴!然而他深知,要想有所成就,就要不断突破自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艰辛。
陈锦农白天在工厂潜心研制,下班后回到家也认真钻研。他买回一套套木料,设计着一个个制作方案。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在炎炎的夏夜,他照样一头钻进闷热的小楼,用方凳支起一个皮箱当工作台,在暗弱的灯光下,探索制琴的奥秘。
数十年来,陈锦农只以斯氏琴为蓝本,制作了上千把小提琴,每把琴都留下了他精心仿制斯氏古琴的痕迹。因为钟情于斯氏提琴,于是有人认为他食古不化,只会模仿斯式琴。而别人除了模仿斯式琴外,也会仿制瓜奈里、阿玛蒂、马基尼等不同大师的作品。对于别人的议论,陈锦农一笑了之。他执着地按照自己心中设定的目标奋力前行。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陈锦农的制琴生涯进入了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他的精力集中在如何对我国自产木材的应用和琴弧度与厚度配置的研究上。他深切体会到:一个作品能否成功,就在于精微之处见高明。仿制古琴,在琴型上哪怕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但没有相应的声音加持,徒有琴型的提琴不过是一具躯壳。工艺与音色融为一体,才是好琴的最高标准。“有志者,事竞成”。经过多年的钻研和不懈追求,1980年春天,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提琴制作观摩大会上,陈锦农的参赛作品锋芒初露,荣获音色第一名。同年11月,陈锦农制作的另一把参赛琴又以其音色优美、圆润、工艺精湛,为祖国夺得了首枚国际提琴制作比赛的金奖。
陈锦农的获奖琴在纽约展出时,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前来观瞻。这把获金奖的琴具有鲜明的特点:琴头、琴角雕刻流畅,刀法硬朗。金红灿烂的油漆晶莹剔透,闪着耀眼的光芒,突显着华丽高雅的本色。
陈锦农力求在悦耳动听的前提下,达到在现代化大型音乐厅与交响乐队(包括钢琴伴奏)一起演奏时,应具有小提琴独有的音响效果。这既是他在提琴制作中的独特思维,也是他追求的目标所在。1983年12月20日,轻工业部在北京隆重地授予广东乐器厂技师陈锦农“小提琴制作大师”的荣誉称号,国内多家报纸和媒体也纷纷报道了陈锦农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金奖的消息。
陈锦农无疑是广东提琴制作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提琴制作技艺上,更体现在他为推动中国提琴制作业的发展和提高国际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他对小提琴的选材、结构、制作工艺有独到的研究。“音色,创造美妙的音色!”是陈锦农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为只有美妙的声音,才是乐器不朽的灵魂。
陈锦农认为,木材上乘、工艺精湛、弧度适当、厚度合理,是构成优质提琴的四个基本条件。他特别重视木材的选择,并根据材料的不同而确定琴面板弧度以及底板的厚度。陈锦农根据自己多年来总结的经验,撰写了一篇《材料·技艺·传统》的论文,这篇论文在中国乐器协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并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
陈锦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提琴制作大师,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他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提琴制作人才,还亲自口述经验,悉心教导年轻人。他的诸多弟子后来相继成为广东提琴制作的翘楚,他曾经教授过的弟子在国际比赛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81年,陈锦农被美国提琴协会接纳为国际会员。1982年,他获得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2020年1月28日,陈锦农大师因病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