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伴我成长
2025-02-14胡炳基
我出身农村,也当过农民。记得小时候,房前有一棵百年枫树,一到夏天的晚上,我就会在树下铺上稻草纳凉,与小伙伴们聆听村子里一位叫胡春元的老人讲故事。他将《封神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我们听得痴迷,小脑袋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离奇却也无端的画面。长大以后,我特地将这些古代小说浏览了几遍,终究觉得没有当年听故事那样引人入胜。我似乎明白了,听书贯耳,读书入心。
我们兄妹6个,父亲长年在汉口打工,母亲拉扯我们艰难度日。我是长子,自然要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初中毕业后,父亲要我回家挣工分,我心有不甘,却也无奈,好在母亲执意要我上学,她常说“穷莫丢书,富莫丢猪”。但苦于交不起学费,高中开学九天了,我还在地里劳动,母亲跑到学校哭着求情。凑巧班主任是我的远房伯父,他私下里为我垫交了学费,才使得我重新进入校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后来每年都要去看望伯父,直到他去世。
那时不兴高考,高中毕业后还得回乡务农。由于身强力壮,干活踏实,又有一定的文化,且根正苗红,我很快入了党,当上了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二十刚出头就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我不敢有“山窝里飞出金凤凰”的奢望,总觉得肚子里缺少货。当时正值“文革”末期,书籍奇缺,能看到的、听到的尽是些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东西,我还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去接受它,尽管吸收不了什么“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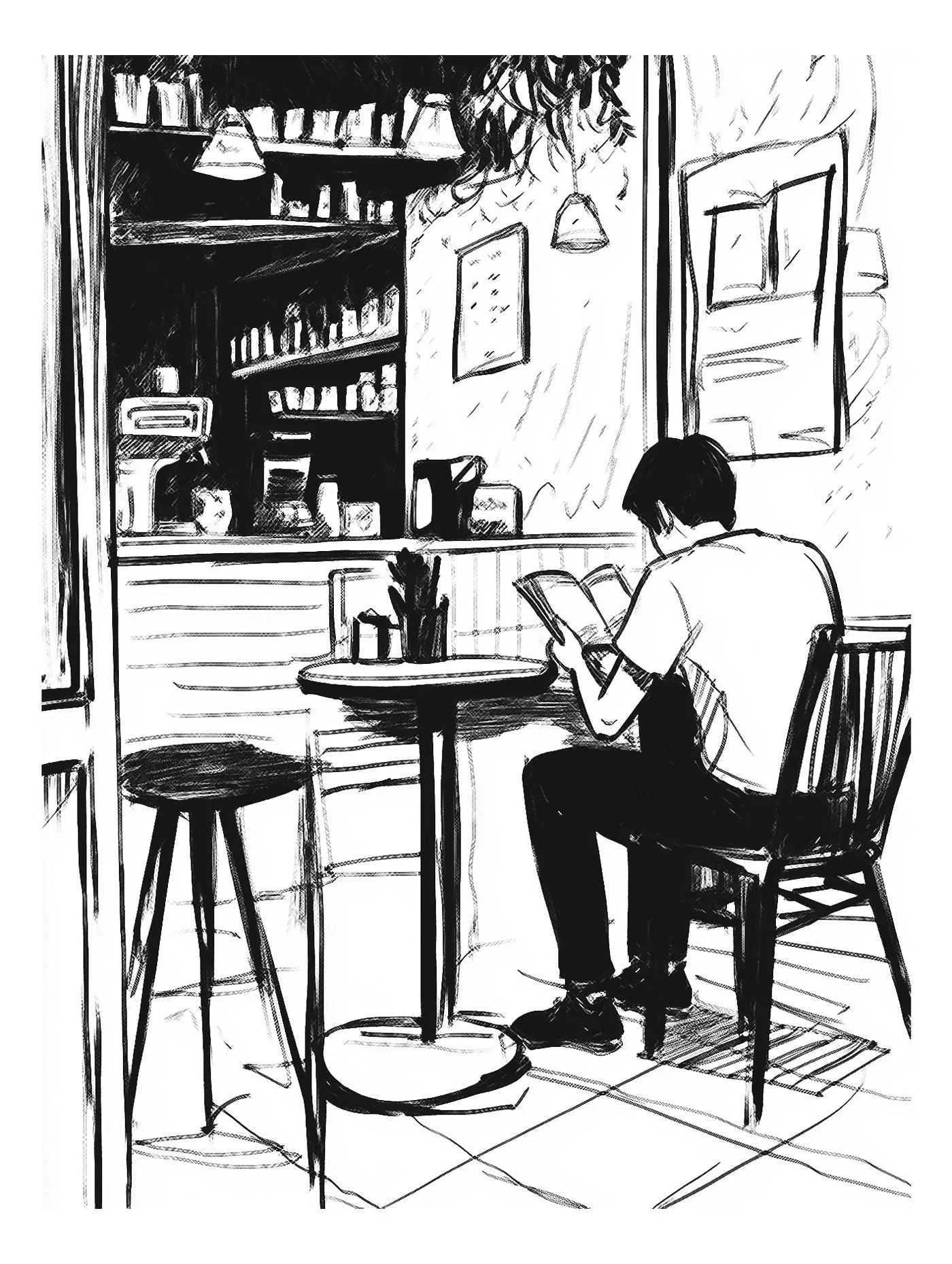
随着工作岗位的不断调整,我养成了看书看报的习惯。我家里有一间不断充实的书屋,它伴随了我的大半生。每到一地,我闲下来不是看名胜,而是逛书店,看中什么就买什么,一本书的获得就是一种缘分和经历。我喜欢读一些伟人、名人的传记,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性格等,领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风格;我的书架上有《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体会其中最高等级的文学性、洞察力和穿透力;我也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丁玲短篇小说选》等现实主义力作,使我意识到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还喜欢《百年孤独》《瓦尔登湖》这样的海外鸿篇巨著,它们或者魔幻,或者让你成为一个静静的隐者和思想者。当然,我读过贾平凹的《秦腔》,也读过池莉的《来来往往》,我热爱农村,更热爱武汉这座城市。现在回想起来,边工作边学习取得文凭固然重要,但挤出时间形成自觉看书的习惯更为重要。大小是个干部,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几十年来,读书、看书练就了我的两种“功力”:一是瞪功,就是眼睛好,瞪大眼睛看书可以从头看到尾,晚上躺在床头看书,再小的字也能看清楚;二是蹲功,说起来有些不雅,多年习惯于在卫生间看书,经常忘记了时间,为此也不知挨了婆婆的多少呵斥和嗔怪。
学以致用是我热爱读书的基本心得。小平同志有句名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我在担任县长助理期间,曾协助分管文旅工作,为“木兰故里”的树碑立传奔波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家乡毗邻木兰山,紧靠木兰湖,自小看电影就会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也读过那篇脍炙人口的《木兰赋》,开头便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中间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结尾惊叹“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记住了那个“扑朔迷离”的美丽成语。木兰山不仅是一个佛教圣地,还是一座英雄的丰碑。共和国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在木兰山留下了革命的足迹,“黄麻起义”失败后72壮士曾在木兰山蛰伏,徐图再起。但历史上的“木兰从军”究竟发生在哪里?原以为就发生在我们黄陂。其实不然,河南虞城已经挂出了“木兰从军”的招牌,修了庙、建了墓、立了碑、烧了香,正在申报“木兰从军”纪念邮票——这可是国家名胜古迹的铁证。形势逼人,必须弯道超车。那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所能找到的涉及“木兰从军”的书籍、典故、文章、诗词歌赋、戏曲文本、传说故事及宣传报道,梳理出较为缜密的文件、汇报材料等,确保向各级领导(部门)汇报时能够引经据典有理有节,来龙去脉侃侃而言,谈古论今信口拈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说服了时任国家邮政局局长刘立清亲自来黄陂木兰山考察调研。刘局长虽祖籍黄陂,但他不偏不倚。他表态说,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能断定花木兰到底出生在哪里,但对于河南、湖北两地都希望以邮为媒,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我们为什么不能都给予支持呢!领导一锤定音,终于分别于当年4月30日在湖北黄陂、5月1日在河南虞山举行“木兰从军”纪念邮票首发式。《人民日报》及省市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产生了相当成功的轰动效应。读书不仅实用,而且管用。
我在区人大常委会当了三届副主任。作为基层的人大机构工作者,我潜心学习法律体系中有关下位法的法律法规,努力做一名基本合格的执法者。退休后,司法部门以我的名字组建“胡炳基调解工作室”,我珍惜这个为民服务的机会,并被评为“金牌调解员”。街道和社区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有了矛盾不要怕,找到老胡有办法。”我听了莞尔一笑。
2021年初,黄陂区成立“‘木兰红枫’红色故事老干部宣讲团”,聘请我任团长。我组织大家实地探访当年黄陂苏区的各个红色景点,收集遗物,整理资料,编写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黄陂元素》系列特色党课,深入社区、机关、学校、企业、景区等地宣讲200余场,听众达3万多人次,受到了“学习强国”的关注。这些年,我坚持拾笔不辍,勤于写作,出版了专著《情溢黄陂》(60万字),主编出版了《快乐驿站》(100万字),正在撰写《黄陂风云人物录》《黄陂文化人物访谈录》两本书,不日出版。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读书伴我成长,学习完善人生。我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不在意生命的长度,而是要追求生命的厚度、温度和亮度,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编:王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