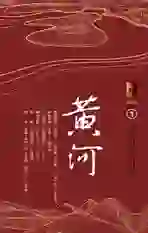大爱
2025-02-13刘小云
婆婆是上天赠予我的第二个亲娘。我十四岁时,我的亲娘暴病身亡。没娘的日子,无论我爸怎样尽心,也不如亲娘贴心的抚摸。
1971年底,我22岁,第一次踏进婆婆的家门。
老两口把我迎进来,他们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我呀,完完全全的学生样,两条落肩小辫,一副白框眼镜,不谙世事,傻乎乎样。大概也算可他们的心吧,他们送给我的是自家人的笑脸。
看到婆婆的第一眼,我的心头一震,恍如我的亲娘回来了!
她跟我娘几乎同龄,同样是瘦俏身材,大襟袄,剪发头,解放脚,慈眉善目。不同的是她操着一口地道河北方言,有些字眼接近北京话,还有的字眼仿佛在《红楼梦》的文字里见到过。
落座后,婆婆递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汤,上面静卧着两只白生生的荷包蛋。这么多年了,我在家,在学校,在单位,都吃食堂,到哪里能吃上荷包蛋?
“忙吃,忙吃!”碗到,筷子也到。
“还有饽饽,刚出锅的。”
我含着眼泪吃下了这碗饭,不知道婆婆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没有。
这顿饭和爱人给我手工制作的那只煤油炉,决定了我的婚姻,我将走进一个善良人家。
1972年5月,我结婚了。这年,婆婆即将跨入60岁。婚房是公公的友人帮我们借到的,就在距离婆婆家不远的市政大楼1单元4层。踏进这间屋子的那一刻,我惊诧到两眼放光。满满的情调,在那个年代,略显小资了点,桌子、椅子和床都是从单位借来的。桌上铺了一条浅色的台布,台布上放一排他常看的书,书的旁边还有一台绿壳电唱机,窗帘和床帏都是淡绿色带碎花的绸布,淡雅温馨。床上红红绿绿的鲜亮铺盖,一定出自于婆婆的巧手,每一件都是蓬松的新棉絮成,松软厚实,针脚均匀;两只大盖箱里,是为我们备的换季被褥和床单,还有为我量身定做的新棉袄。为了这一天,婆婆准备了多久?按票证供应的年代,她该省了多少自己用的,大概所有积蓄都用到我们身上了。
老两口将我当作自己的女儿,他们不叫我“小云”,直接就是“云”。我心里清楚,他们是可怜我这个没娘的孩子,后来我成了孩他娘,他们依然这样叫我。
与他们相处几十年,我在他们眼里心里,一直是被宠爱的“云”。
一
1974年2月,我的长子出生。这个月子,我跟婆婆住在了一起,我和儿子的吃喝拉撒都归婆婆脋饬。
也就是从那个月子起,婆媳俩结成了她唠嗑我倾听的结构。还别说,这个结构坚持了几十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我都是她唠嗑的倾听者。
她把她的家乡都搬给我了,尽管,我根本没有机会跨越太行山落脚华北大平原。这个月子,我的胃口大开,婆婆的几种带河北印记的“好吃的”,我不但尝鲜了,还吃得我下奶多多,孩儿吃得胖胖的,而且将其要领学到手,成了我们这个小家的传家特色饭,以至于俩儿子时不时会提请我满足他们的味蕾。
这个月子,大部分时间是我躺着,婆婆坐在一侧讲她的家乡和往事。聊啊聊,聊到该做饭的点了,她就在床上铺一层油布,摆上面板,她边擀面边唠嗑。她和面是真“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利利索索。圆圆的一团面,不大功夫便擀成了有棱有角的四方形,擀到纸一般薄时,抽出擀面棍,折叠成厚厚的长条形;然后,左手压面右手持刀,只见一叠面,随着手的轻移,而成条;再然后,她握住切好的面条轻轻抖动,面粉落下,把粗细均匀的面条放在一个用高粱杆制作的盖贴上。要知道,这面条从第一根到最后一根,一样的粗细一样的长短。这简直是绝活,整个过程,出神入化。
婆婆做的烙饼忒好吃,这个“忒”字就是《红楼梦》里常出现的词。就在这个月子里,我枕头边上放着全套《红楼梦》,目的就是想找公公婆婆口语里冒出来的“红”词。家里人隔三差五要吃婆婆做的烙饼,还禁不住边吃边感慨“忒好吃,忒好吃”。烙饼一层脆脆的外皮,数层嫩嫩的里囊,还有大油的香味,由不得我总是吃着手里的,还要算计盘子里的,能给我再留点吗?
有一天,我的肚子着凉了,婆婆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饭,她说,你吃一碗“饺子粥”,暖肚!哈,棒子面粥里,煮着几个饺子,还有红薯?这是什么饭?我从来没有听过,更没有吃过呀!饺子和红薯煮在一锅玉米面糊糊里,这该是什么味道?
我一口饺子,一口粥,再咬上一口甜甜的红薯,咸咸甜甜,还烫烫的。一碗“饺子粥”下肚,肚子里的凉气全消。几十年后,“饺子粥”成了我家的传家饭,儿子,儿媳,孙女,在寒冷的冬日里,经常要求我做饺子粥。
显然,面条、烙饼、饺子粥,是他们的家乡饭。
他们的家乡在哪里?我始终没有去过,但从婆婆口中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那里家家有地道,村连村户连户,地道连成片;婆婆还说,他们家无山有水,有芦荡。他们离开家乡时,正值发大水,就摇着船儿到保定。由此,我想起了孙犁的小说《白洋淀纪事》。婆婆还说,在老家时,我公公就加入了共产党,我就构思画面,公公就是白洋淀里的水生,婆婆就是水生嫂子,白洋淀里的故事,有他也有她;我还将公公想象为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在村子里带着大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前些年,我们还专程到保定,到白洋淀,到冉庄跑了一趟,目的是想将婆婆给我讲的一系列故事形象化。其实,婆婆给我讲的故事,并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她周围的人物也非常简单,简单到也不过就是一二三。
婆婆说,在老家时,不管在娘家还是婆家,灶台上的活儿都靠她,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下地回来,坐在炕沿吃的,站在当屋吃的,蹲在门槛上吃的,都会发出不间断的哧溜哧溜的声儿,婆婆心里不知有多满足。
婆婆是在乡下长大的,她的家乡在河北大平原上。娘家在任丘县的西汜水村,因为处在四条小河汇聚处而得名,她嫁到距此处十里左右马家村的杨家,当然是媒妁之言。婚前她对夫家一无所知,幸亏她嫁给一户门风甚好的人家,夫君识文断字还善解人意,她这一辈子,没有受过夫家人的气,心胸展展的。
她是家里的长媳,四世同堂,她用她的行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在她的唠嗑中,我掌握了这一大家子的辈分和名字,婆婆有公婆,还有两个小叔子,两个小姑子。不过,在我们的聊天中,她嘴边流出最多的是她的两个妯娌。大小叔子的媳妇叫大珍,二小叔子的媳妇叫秀阁,秀阁那时还没有生孩子。婆婆和大珍的孩子,夜里会躺在各自娘亲的被窝,但白日里,不分谁是谁家的,大点的带小点的,大人们就不用操心了。有一次,大珍的女儿带着婆婆的女儿在门前追逐玩耍,跑啊跑,经过了不远处的芦苇塘,掉进了水塘。婆婆扯出了女儿,大珍的女儿后怕,惴惴不安,生怕大娘训斥她。大娘呢?摸摸她的头,给她擦擦眼泪,安慰她,孩子哪有不碰不摔的?明儿,你还带她玩儿!
三个妯娌嫁到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无话不谈。那是她们的青春岁月。婆婆的社会交往圈不大,尽管她随夫到过东北和北京,最后落脚于山西太原;尽管她经历了战争,见到过日本鬼子扫荡,直视过日本鬼子用步枪对准了她和她的母亲及怀中的孩子;尽管她在夫家三兄弟分家后,面临着男人外出打工,她自己主持并请人盖几间瓦房的大事件,请短工帮着春种秋收打场,甚至踩着那双缠过又放开的小脚带着自己织的小布到张家口集市上去卖……但她始终出色地饰演着屋里人、母亲、大嫂、奶奶(姥姥)、邻家大娘这样的角色,在她心目中,没有形形色色这一说。我特别注意到,在可以数得见的关系中,只要提及大珍和秀阁,她就会绘声绘色。我在她的绘声绘色中,对大珍和秀阁还曾勾勒出一幅带有动感的图画,那是她此生相处最好的姐妹,值得一辈子回味。
我与婆婆心理融汇从这里开始,一位没有摸过书本,没有点滴文化的乡下女人,送给我一本厚重的书,此书荡漾着河北大平原上朴素的民风。
二
婆婆离开家乡后,自己刚刚主持盖起的这几间瓦房被冷落了。她时不时提起老家的三间瓦房和院子里的那株槐树,那是她的乡愁。她也曾回去过几次,每次离开时,都会自己问自己,那株槐树,怎么才能天天看到?于是,她吩咐她弟弟将这株树砍伐并锯成板材,她听说大儿媳妇的弟弟利生要开大卡车到天津办事,那就委托他顺道到任丘老家一趟,把这些板材拉回太原。
我曾在平房院里见过这些板材,似乎不关我什么事,也就是扫一眼而过。婆婆家搬到楼房里后,这些板材放到何处,我也没有操过心。
可是,有一天,老家舅舅的儿子小国从天而降。
见到小国,我还开玩笑:小国来看大姑啦?
小国说,我还要到嫂子家去一趟呢!
一头雾水,但我还是表示欢迎小国光临寒舍。
我们刚搬家,住进了新建的一套楼房里。那天,小国进得门来,拉开米尺,丈量起我们的卧室。我仍然不知他的目的。
过几天,小国画了一幅草图,说是草图,但很规矩,是一张漂亮的组合柜图,有高有低,中间还有一个桌面,算是我的书案。估计,老人跟他有交代,她这个儿媳妇是个书呆子。
图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标着标准的尺寸,他征求我们的意见,看这样的设计成不成?
原来,婆婆要把这株老槐树送给我们了,我们的新家,正需要这么一套组合柜。
打造组合柜,要拉大锯扯小锯,从板材到成柜,丁零咣啷,就在婆婆家楼前那块空地上进行。
小国将做好的组合柜,精心上漆,风干后,还是请利生帮着拉到我们家。恰好的位置,耀眼夺目,我们家的档次立时提高了。
那次,小国还悄悄地跟我们说,他最亲他大姑了。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套组合柜跟了我们近四十年,睹物思亲,该我给孙辈叨叨老奶了。
婆婆把她的最爱,给了我们这个小家。
她的心偏向于我们,左邻右舍和家里的第三代都有这个说法。说来说去,我知道,婆婆还是怜我没有亲娘,怜我是个捧书本的人。
婆婆有三个子女七个孙辈,早就说好,以她的力量,一家能给帮衬着带一个,可是,轮到我家了,婆婆的老主意松动了。
我的长子两岁多时,次子出生了。既然婆婆只能带一个,那次子就跟着我到单位,上单位的托儿所也可以呀!可是,有一个周日,我们带孩子回家,婆婆抱着孩子来回看,不对呀!这孩子的屁股是不是坐盆盆坐大了,不行,给我送回来。
也不知道婆婆怎么就能摸出孩子屁股被“坐”大了,但我知道,托儿所里孩子多,阿姨忙不过来,就一个孩子一个便盆,坐在盆上吃喝拉尿。那也不至于把屁股坐大呀!
婆婆下令了,我当然高兴,省我多少事呀!正好,长子也该上幼儿园了,那就换个个儿。
1982年的一天,次子感冒了。我接回来,带他到医院。医院的护士边聊天边给孩子注射,一下子,伤了孩子的神经,当下就瘫倒在地上。我没想到那么严重,还是把孩子抱回了家。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了,孩子站立不住,更别说行走了。我们带着孩子到儿童医院,未查出结果,又到华卫所做检查,确诊是坐骨神经受损,只好到北京,先后住在我大姐和爱人的堂姐(大珍的女儿)家,大姐给我找关系,跑了几家医院,都说是神经受损,最好是慢功夫针灸治疗。我们选择了北京儿童医院,一位非常和善慈祥的老大夫,坚持用漫长的三个月的时间给孩子针灸。
这三个月我们付出的辛苦自不必说,我婆婆也是经受了日日煎熬。
有一天,我在北京收到公公的信,我念了一遍又一遍,也给孩子念,可他太小,听不明白。许多年后,我将信找出来,发到我们自己家群里,已入中年的两个儿子都看哭了。
公公的信,抬头就是二民,二民是次子的小名。
信中说,你去北京已有36天了(多准确呀!),我们想念你,尤其是前一个时期,想得厉害,你奶奶都梦到你回来了。我每过你们幼儿园门口,还有每当英英、小波来找你的时候,心里就不平静了。有一天,电视里演北京儿童商品展销会,我和你奶奶瞪着眼看,看是不是你和你妈妈去了,看到有坐飞机、坐汽车的儿童,总想着有你们的镜头才好。后来看中央领导也去了,估计你们去的不是这一天。
我们家俩老人,也有天真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北京,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新闻镜头里,居然每天会眼巴巴地看着电视屏幕找他们的小孙子。
我们在北京时间长了,婆婆不放心,几次欲动身,亲自到北京来陪着孙子,似乎这样她才放心。期间有一天,我大姐到太原出差,专门到我婆婆家看望她,并向她汇报孩子治疗的效果,她才打消了亲赴北京的念头。终于,她度日如年般地将我们等回来,看到了她能活蹦乱跳的孙子。
我的两个儿子就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有一天,他俩不小心做了一件出格的事。
那天,婆婆到后边老王家有点事,这俩孩子居然自作主张,开火煮荷包鸡蛋。坐上锅,装上水,再打开煤气灶,看着水开了,俩人从冰箱里取出一小笸箩鸡蛋,你一个我一个,锅边上轻轻一磕,水水的鸡蛋就脱壳掉进了锅里。俩人玩得高兴着呢,根本不顾及往锅里甩了多少个鸡蛋。一个小笸箩呀,怎么也有十大几个甚至二十个,那是老人安排全家人个把月吃的鸡蛋。
老人回来了,看到热气腾腾的场面,欲哭无泪,俩孩子恍然间知道闯祸了,靠墙根站着,准备挨揍。可是,老人递给他们的只是瞬间的无奈。
俩儿子读中学的时候,每天午饭要回到婆婆家吃。两个壮小伙儿,饭量可想,还得不断变花样啊!要按时让俩孙子吃上饭,饭后,还必须留出充足的时间,让他们一人一屋睡个午觉,俩小伙儿初高中各六年,中间又有俩人同回奶奶家的时间,这该是多少年啊?那些年,老两口都是七十大几,接近八十岁,体力支不支?似乎我们都没有在意,真后悔。若干年后,当我看到公公的日记本时,才知道,这期间,老两口都曾感冒过,而且,公公还骨折过,可他们一天也没有中断过两个孙子的午饭。
婆婆八十岁的那顿生日宴,我们一大家子十四五口人都聚在家里,那年,我的长子已入大学,他为奶奶写了一封信,弟弟代他念;他还给爷爷写了一封信,爷爷自己念。我特别注意婆婆听这封信的表情,一脸的笑容,好慈祥,好满足,三家人依次举杯敬祝老人身体健康时,她都要站起身来,把手中的酒杯递至敬酒的方向,当她听到重孙子脆生生地喊她老太太时,尤为兴奋,脸上都放光了。
三
很多年前,婆婆到北京窦店去给妹妹过六十岁生日,妹妹递给姐姐一包石榴籽,说,咱们都这岁数了,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这包石榴籽,也就是个念想吧。她还说,这是中南海的石榴籽,结出来的石榴个大籽粒丰腴。
婆婆很珍惜这包石榴籽,回来后,将其撒在一只大花盆里。不久,嫩芽破土而出,长枝,须根,分杈,没两年,大花盆显小了,婆婆又将其移至浅缸里,顺手掰下一枝壮点的,插于原来的花盆里。这枝还长得真快,没多久,一株变两株,成小树了。树上伸出了弯弯曲曲梅树样的枝干,枝干上繁衍出数不清的枝枝杈杈,开满了清新靓丽的红花绿叶,就像精致的根雕有了鲜活的生命。老两口百般呵护细心捉弄,又在想,下一步该让其在哪里生长?就在石榴树4岁那年,公公单位分了新楼房,他们得到了一层靠西边的一套,前无遮拦旁空阔,阳光充足。老两口又在阳台外建了台阶,台阶的两侧有两片不足2平米的空地,他们便将此处作为石榴树的栖身之地。为了给石榴树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以吸收充足的养分,年近七旬,即将离休的公公用小平车从郊外拉回了熟土,换掉了原来修建楼房积淀的层层灰渣。之后,施肥,浇水,营养土壤,再将石榴树从缸中移出,植于其中。从此,随着季节的更替,两株石榴树竟各显其芬芳,成为家属院的一道风景。到了冬天,老两口又不顾寒风袭人,相互配合,用草垫子和草绳子将还不甚壮实的石榴树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以防受冻。为了不致石榴树孤单,他们还在阳台内外培植了许多种盆花,诸如君子兰、吊金钟、串串红、虎皮海棠、仙人掌、月季、文竹等。这些花种,大多是友人相送,不论什么习性,竟是栽一盆活一盆,四季都有色彩,四季都有芬芳。有一次,不知哪位路过的人,吃完一只杏,顺手将核扔到我家小园子,居然奇迹般长起一株杏树。
每年中秋过后,婆婆都会沐浴着暖暖的秋阳,观赏窗外挂满枝头的即将咧嘴和已经咧嘴呈现出成熟笑脸的石榴,她准备在上冻前采摘石榴。
清晨,她喊醒还在沉睡的我的儿子,祖孙俩开始动作。小的踩着凳子,从上往下,远一个近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弯腰伸臂煞是忙碌;老的一个一个接过来,小心翼翼放在备好的笸箩里。小的摘完了一株树,又转战另一株树;老的,放满了一只笸箩又找来另一只笸箩,双眼还帮着孙子搜罗“漏网分子”,晌午时分,将近200个石榴被婆婆精心分成若干份,数量不等。夜晚,趁着人们都在家,婆婆借着月色,迈动着小巧的金莲,按照自己既定的方案,将分好的石榴送到前楼后楼左邻右舍相处有缘、对她和老伴有过些许照顾的人家,用以回报或是沟通。这些年龄都不及她的同辈或是晚辈早已将我家这两株石榴树当做观赏物,春天里,枝繁叶茂如同碧波荡漾;夏日里,数不清的红玛瑙一样的花瓶般的骨朵上绽开着光华耀目的鲜花,目击者定然会从心中升腾出炽热的生命感受;金秋到来时,密密麻麻的骨朵怦然长大,金樽玉盏倒挂垂悬,忽然,有几只就像早恋的少女羞涩地咧开了樱桃小嘴,露出了里边的皓齿,既酸又甜的味道引诱着过往行人。当他们从老人手中接过为数不多、但情谊甚浓的石榴时,无不为侍弄石榴树的两位老人投以钦佩的目光。
自然,老人还是将大部分的石榴留给了自己的七个孙子一个重孙,并作等分。为了正在成长的后代,他们永远乐此不疲。
公公婆婆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家门前石榴树依然茂盛。前些年,小区物业整顿院内环境,楼前的栅栏一律拆除,但是,他们还是将我家的两株石榴树当“非遗”一般保留下来,这两株石榴树承载了这个大院里几代人的回忆,颇具风骨却又青春常驻。
四
公公先婆婆离别人世,婆婆一下子接受不了,受刺激而痴呆,曾两次走失,我们动用了电视台广告找回了老人。
不明白她为什么执意要出门,要远走,是不是她又念叨起自己的家乡?她从哪里来,也将回到哪里去?
第一次丢失,这个想法就得到了确认。她从上午就出发,不知疲惫和饥饿,从市中心一直走到城南二营盘附近。夜晚,乘凉的人们看到无助的她,跟她对话时,一位操着相同口音的中年人,跟她搭上话。她心里那个高兴呀,乡音即知音,好像是回到马家村。人家把她请到家里,给她喝水同她聊天,忽然间,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发的寻人启事,马上给我们电话联系,我们方才开车把她接回来。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哪怕是夜里。
有一次,我陪她过夜。她很精神,整理了一个包,对我说,你看好家,我去去就回来。没办法,我拦不住她,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我怕她摔跤,想扶又不敢,她交代我的任务是看家呀!当她走到大门口,看到铁门紧锁,竟然双手把着铁门,要翻门而过。那种义无反顾,真的阻拦不住。我想起我大伯子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当时,我大伯子跟她说,咱们回去套好车,一起走。这话,她听得懂,在老家出门时,不就要套上马车才能上路?我也这样说,还真起作用。回到家,她又把包儿打开,对我说,云,你记住,这个是给大珍的,那个是给秀阁的……
她的思维完全回到了青年时代。
她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外走,有过两次走失的教训,身边不敢没有自家人。我们都还在职,轮流着来吧。她每天走的线路基本是,出院门往西,拐入半坡东街,再拐到府西街,然后,进奶生堂,再到羊市街。少也有三五公里。回来的路上,她已经累得瘫靠在了我身上,一身疲惫的我,也只能用自己的身子把她拖回到大门口。给她买根雪糕,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稍稍休息后,她居然又重振旗鼓,欲继续走。这时候,我真的无奈了,可她还振振有词。有时候是街坊们用句分散她思维的话打岔,她才跟着我回家。
累了,她会乖乖地把双脚放进热水盆里,任我给她搓搓脚,脚心脚背地给她按摩一下。她懂得,我把左脚给她搓完,她就会将右脚给我伸过来。那个时刻,她又那么乖顺。我很难受,一双小时候缠裹过的脚,脚背凸起,脚心弯弓,五个脚趾有四个脚趾也残忍地贴在一起,连脚掌都看不到,怎么能落地?又怎么走南闯北的?临终这三年左右,她每天不知疲倦地走在同一线路上,那双脚该有多疼?如果心中无信念,她断然不会这样不管不顾。她真的是在想家,想她河北的老家。
我和婆婆相处几十年,非常了解她,她在家说一不二,所有的人都听她的。我没有见她吼过谁,有时候,她想说谁不好,顶多就是三个字话“那行子”,这三个字怎么写?字典里查不到,我也就只从她嘴里听到过。几十年,她对我说过最严重的一句话,是说我“烧包”。那是因为我想戴那只爱人给我买的梅花表。当初我舍不得戴,先让婆婆锁起来,当我想戴,跟她开口要的时候,她来了一句“烧包”。是玩笑,我先笑了。有意思,这只婚前爱人给我买的梅花表,是婆婆给我戴到腕上的。
婆婆一生没有进过医院,是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无疾而终的。那些天,思维总沉浸在遥远年代的婆婆,居然对我,她这个儿媳妇心中有数了,好像她知道我买好到了武汉开会的飞机票。她算好了日子,在我出发的前四天,在睡梦中静静地走了。那是2001年,她88岁。
知我者,我的婆婆,我的娘亲!
我的婆婆,名叫李大爱。三十年了,我在这个家庭得到的爱,是无尽的大爱。
【作者简介】刘小云,网名蕾怡,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陆家儿女》(合作)、文学评论集《云心思雨》、人物传记《层林尽染》、散文集《情到深处》《峰高水底清》《晓云秋语》《晓云散语》等。
责任编辑:曹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