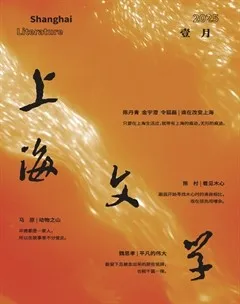前辈作家素描
2025-01-03陈世旭
题记:半个世纪的写作中,除了在大会上远远看到前辈作家或只是听到他们的名字,我有幸交往的极少。本文的记录,也仅是雪泥鸿爪。但他们给予我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刻的。
大爱
第一次获文学奖,是巴金老人给我颁发的获奖证书。与他瘦弱温暖的手轻轻一握,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再见面的机缘其实是有的。很多年后,我在省里的文学社团主事,当时全国各地作协纷纷建立文学院,我们也跟着有了想法,借重古人写《滕王阁序》的名头,成立“滕王阁文学院”,找到中国作协的朋友支持,请求巴金老人题写院名。起初以为只是痴心妄想,说说而已,不意竟得到巴老的同意。我反而有了迟疑,以我的写作状况,有何面目去见世纪泰斗?思忖再三,决定由社团秘书长纯粹作公务出差。
从上海返回,叙述巴老题写院名时的情景,秘书长十分动容——
病榻上的巴老由女儿小心翼翼地扶起坐好,预先准备的垫板在被子上放平,老人伸出颤颤巍巍的手,写了一遍,眯缝起昏花的眼睛仔细看过,觉得不满意,又让女儿抓住他抖得很厉害的手写了一遍。
巴老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种大爱:“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他从不以作家自居,不以名人自居,总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样一种“把自己烧在里面”的真诚,是巴金大爱的写照。而今,他抱病给一个外省文学院题写院名,无疑是期望每个追随他的写作者都好好努力,取得成绩。
巴金题写“滕王阁文学院”的两个原件,我后来交给了省档案馆,留下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时时感受老人“把自己烧在里面”的大爱。
风范
一九九三年。兰州。黄河岸上。
中国作协采风团近十位作家参差肃立,为首的是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相对于这个名字,他的笔名在中国妇孺皆知:光未然!他与冼星海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
这些被高昂壮阔的声音和旋律传送的文字,曾经响遍了中国和世界。
老诗人严峻如铜像,但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内心像黄河一样奔腾澎湃。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磅礴、雄浑、悲伤、坚强、愤怒、咆哮、抗争,强烈地撞击着我们每一个人。
第一次见到光年老,是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作代会的会场。他在远远的主席台上作大会报告。那不是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大话、空话、套话和教训、指点、要求的八股文章,而是生动、鲜活、睿智、雄辩、汹涌、恢弘、气势若虹的文艺宣言,充满了诗的激情。
现在,他这么近距离地站在我们面前。
除了历史偶像的光环,现实中的光年老是一个和善羸弱、平易随和的老人。
接下来是河西走廊漫长的日程: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每到一地,光年老都理所当然地被簇拥在人群中心,严肃地倾听,被请教,被请作指示,最后是几乎无休无止地“留墨宝”,常常要写到半夜——这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光年老有求必应,对所有的愿望都尽可能地满足。这让他每天除了坐车、吃饭、回宾馆睡觉,大多数时间都必须站着。不像我们可以随意溜达,随意聊大天,随意坐下甚至找个僻静的地方躺平。一同来的夫人和秘书心疼不已,但劝阻无效。
一行人到了酒泉,光年老终于支持不住,晚上在团团包围的求字者中书写时昏倒,被紧急送进当地医院。第二天我们知道时,车已开出老远。一行人只有嗟叹不已。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嘉峪关,到了敦煌,光年老居然赶来了。一下车就问常书鸿。
常书鸿,一九四四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到访的时候,他依然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在荒凉寂寞的戈壁沙漠中苦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他不仅是杰出的敦煌学家,还是优秀的油画家和艺术理论家。他与女儿常沙娜一起,将敦煌艺术推广到全世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
那天,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光年老再三说:我是特地来看望您的,感谢您为中国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常书鸿说: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当晚,光年老照例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狭小的会议室留墨。写的是显然酝酿已久的好几首吟咏敦煌的七律,律句工稳遒劲,墨迹飘逸典丽。见他依然一脸病容,我极力抑制住了求字的冲动。
没有想到,河西走廊之行结束,回家不久,我收到了光年老寄来的墨宝,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敦煌七律中的一首,横书竖书各一幅。
两幅字我后来交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留在身边的是一代杰出诗人和文学事业领导者的闪光风范。
直言
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颁奖座谈会上,中国文坛当时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冯牧讲话,近在咫尺听到他畅言“据说《小镇上的将军》之后,陈世旭就再也写不出作品了”,真是五雷轰顶。几天后住在北京一个防空洞中的招待所改稿,同房间一位宁夏作家煲电话粥,电话那头的人知道我也在房间里,脱口说:“他啊,就那样了,写不出了。”宁夏作家赶紧捂住电话对我笑说:“公刘,他夸你呢!”
深更半夜,听筒里的声音一清二楚,宁夏作家的掩饰更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公刘是我从小崇拜的诗人,我就读的中学有图书馆,每次我一进去就翻杂志找他的诗。他的话,我听着就像死刑宣判。
冯牧和公刘爱护和提携青年作者在文坛是有口碑的。两位老师的直言都没有恶意,他们依据的是文学界的舆论,当然不可能想到类似的舆论对一个好不容易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年轻人有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那时候,省里的好心人正在考虑顶住不同意见把我调回省城。自从十六岁下乡谋生,我在农场和小镇待了十六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带着妻儿回到日渐衰老的母亲身边。
幸好,调动很顺利。但两位大家的直言却像魔咒伴随了我的整个写作生涯。正是这种魔咒,激发了我生就的逆反心理,非要死磕到底!不管写作会不会有起色,不管会不会头破血流,撞了南墙也决不回头。
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大家的直言不讳也是一种提携。写作坚持到今天,虽然没有可以告慰他们的成绩,但我对他们始终满心感激。
严谨
一九八五年,我受省文化厅派遣,去当时的南联盟所属马其顿共和国做文化交流,参加他们主办的一个国际诗歌节。到达后我才知道与会的还有中国作协代表团,从北京出发时,我跟他们同机,只是互不认识。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听到他们向使馆官员的自我介绍:团长、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邓友梅,小说家刘绍棠,诗人张志民、邹荻帆,如雷贯耳。虽然读书少,我也多少知道刘绍棠老师上中学时就出了大名,张志民老师的诗“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更是我的初中课文。能遇上他们,三生有幸。他们年纪大,带的行李又重,上上下下我不声不响地主动帮着搬运。
到达目的地的次日,当地接待我的翻译因事耽搁,没赶上上午的活动。中午,主办方把当地记者拍的新闻照片洗印出来,放在宾馆大堂的长桌上,让与会者各人挑出有自己影像的照片,每张售价相当于人民币一元。身边的张志民老师挑了一大叠,我找到了跟我有关的一张,作为回国汇报的资料,请他先帮我付费,回头我有了当地货币后立即归还,或者我付给他一元人民币。出国前,省有关部门给了我八十美元备用,因为当地翻译没来,我无法兑换当地货币。另外按照协议,除食宿交通外,当地每天还会给我等同一百元人民币的零花钱。
张志民老师皱紧眉头沉吟了一会儿,很郑重地说:我请示一下。结果是午餐时,邓友梅老师认真跟我谈话,说,你是省里派出的,我们对你完全不了解,中国作协的经费不好随便挪用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误会,急了:我只是向张志民老师个人暂借,并且不知道你们买照片用的是中国作协的经费。不过我还是谢谢你们给我上了一课。
中国作协代表团的几位老师不了解我,我充分理解。我写作实在太不堪了,出了一篇就难以为继,无法让人有印象。此前不久在京开会,有天晚饭后,著名作家陈建功领着几位作家去接史铁生来开晚上的座谈会。我久仰史铁生大名,但素无交集,于是兴冲冲跟上。我把个头挺大的史铁生从他四楼的家背到楼下上车,中间他问过我的名字,过些时候,我看到他记叙这次参会的文章,很感动地写到那天背他下楼的是一位京城作家。我多少有点遗憾,但立刻就觉出了自己小肚鸡肠的可笑。
马其顿方面后来按协议单独为我安排了一系列参观采访活动,当地报纸关于我参与文化交流的专题报道,附了大幅照片,足够我回国汇报,根本不用买新闻照片。
从国外回来,我先后收到张志民老师和邓友梅老师的信。前者代他在《北京文学》当编辑的夫人约稿;后者特别肯定了我在国外的表现。
可惜我那时候写不出小说,对语言隔阂的外访也视若畏途。我没有回信。但一张照片的喜剧让我看到了老一代作家为人处事丁是丁卯是卯的严谨,让我牢牢记住了切不要随意求助,尤其在与金钱有关的事情上一定不要越雷池半步。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严谨,如今似乎不多见了。
勤奋
刘绍棠老师高且胖,走路有点吃力的样子。中山装的大口袋老是给香烟、打火机之类塞得满满的。手上永远抱着一只硕大的拉链皮包,里面的方格稿纸把皮包撑得拉不上拉链。不管是大会、小会、车上、餐厅、观光、散步、只要坐下来,他就从包里掏出稿纸,用皮包垫着,“刷刷”写起来,除了不时推一推近视眼镜,雷打不动。那些年,他的作品在全国文学刊物上铺天盖地。外访那几天,每次见到他,对我都是一种折磨:像我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文学小乞丐走在他身边,真是说不出的悲惨。
不过,刘绍棠老师偶尔也有放松的时候。有一次,在当地文学团体一位很优雅的女士家里做客,也许是想起了长满蒲柳的大运河家乡,他向女主人介绍说:邓团长年轻时是文工团出色的评剧花旦,扮相和唱腔都极美。随即就提议“邓团长亮一嗓子”。
邓友梅老师猝不及防,不便推脱,涨红了黧黑的脸,捏着小嗓子唱了一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唱得真是好。只是与他唐装里的壮实身体颇不相称,多少有点滑稽。
刘绍棠老师爆笑起来,特别洪亮,特别爽朗,头仰着,全身颤动,脖子和脸都极其饱满,让我头一次见识到:大作家除了有非凡的勤奋,还有平凡的可爱。
温暖
日前查找资料,从网上看到徐怀中老师五年前获了茅盾文学奖,一年前已经故世。怅然良久。
我与徐怀中老师只有一面之缘,第四次全国作代会,偶然与他同座。小学我就从邻居的高中生那里听说过他的《我们播种爱情》,心里惴惴的。看到我的代表证,他轻声说:看了你在《人民文学》发的《惊涛》,挺好的,可你为什么又接着发结构完全一样的《惊涛续篇》呢?艺术是最忌重复的!
我呆呆地看着他,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几年,是小说的黄金时代,文学的天空,群星闪耀。仰望星空,我眼花缭乱,说不出的惶惑和焦虑。作代会结束,回省后,在一次长久的枯坐之后,我忽然鼓起勇气给徐怀中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我写得特别苦,完全没有方向,写作始终是小镇业余作者的水平,无法达到社会期望的专业作家的要求,对小说的认知就停留在冯梦龙的时代,当时的“寻根”“先锋”“意识流”“身体写作”“私小说”“反崇高”“零度情感”“文体革命”,包括我仰慕的同辈作家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还有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以后的小说,我都看得云里雾里——虽然理智上知道,对文学发展来说,那都是有益的探索。
我并没有指望徐怀中老师回信,我写那些,只是一种被当代文学主流圈远远抛下的绝望的哀鸣。
徐怀中老师很快就回了信,说:别着急,你有那么多生活积累,多学习,多磨练,慢慢就会找到感觉的。别人怎么写当然可以了解,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子,自己觉得怎么顺手就怎么写。在不在什么“圈”不重要,重要的是言为心声,表达出真情实感。
我反复咀嚼那封信的一字一句。在徐怀中老师,那也许只是一位温厚的成熟作家很自然释放的善意,对我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也不好意思再写信打扰。如今,他已离世,直接听他教诲的可能性没有了。不过,虽然我的写作依旧没有长进,但他对一个几乎陌生的习作者简单明了的肯定和点拨,长久地温暖着我,成为我至今还没有放弃写作的一种动力。
方正
第一次见到李国文,是一九八○年他到庐山开笔会,我和他有过一两次短暂的交谈,在一群文坛大家中他给我的感觉特别随和。与会的云南作家彭荆风老师祖籍江西萍乡,私下对我说:我算是你老乡,提醒你一声,这么多大家来了江西,你该宴请一次,表示礼貌。我一时张口结舌。
那时候我在小镇文化馆,和妻子的工资加一块不到七十元,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不管怎样精打细算,还是月光族。《小镇上的将军》稿费加奖金四百元出头,早贴补了柴米油盐,绝对想不到大宴宾客,而且是如此众多的八方贵客。在当地几位穷哥儿的帮助下我后来总算硬着头皮,在一家低档的餐馆凑了一桌,比笔会主办者每天招待的伙食差得老远。
李国文显然看出了我的拮据,不久江西某机构邀请他和刘心武、王安忆讲课,我去宾馆看他们,见面他就说:坐一会儿你就回家吧,这次可千万别请客。
这让我有了给他写信的勇气。那时候没有电脑,我的字很潦草。而李国文的回信却几如印刷品:娟秀,工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沉着而端庄。让我吓了一跳的是抬头的称呼:“世旭文兄”!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李国文几乎是我的长辈了。他这样放下身段,暗含的是对晚生的爱护。
爱护并不仅仅表现在称呼上。一九八七年创办不久的《小说选刊》转载了我的短篇《马车》,同期有一则对《马车》的短评,二百多字,刚健有力,文采斐然。短评作为刊物言论,没有作者署名。收到样刊后我看到主编的名字是“李国文”,因而猜想,那则短评会不会出自他的手笔?以《马车》那样陈旧的写实,能发表的地方很有限。小说发表之前,已经历了一次退稿。好不容易发表了,得到转载,还有点评,我的窃喜是可以想象的。
我把那则点评反反复复读了几遍,虽不敢藉此就认为《马车》真的就像点评的那么出色,但至少给了我几分自信。
几年后我的一部长篇出版,出版社照例开研讨会,以广发行,让我也帮着找几位大家捧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国文。我心里很没有底,李国文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推脱的。那时候还没有“红包”一说,参会的人除我之外都住在北京城里,最多就是报销往返“面的”票——有公车的连这也免了。纪念品就是一册拙书精装本,一文不值,还挺沉。
但我的话刚完,电话那头立刻就传来了李国文极爽快的回答:“行啊,我去。”
那个长篇并非成功的作品,参会的作家、评论家也并没有太多谈论作品本身,而更多地认可了写作的认真。有一种前辈和兄长的温情在其中——他们希望我能挺住,能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半途而废。既然把文学看得神圣,就永不要背离它!
我跟李国文见面的次数不多。早年去过两次他的家。铁道部宿舍楼一楼尽头,一个狭窄的院落,百十来平方的室内,是一个洁净得似乎消过毒的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条,到处都纤尘不染,让进入其中的我有玷污之感。两次又都恰遇鸿儒满座,让我自惭形秽。以后也就不便打扰了。
好在我可以从文字里感受他的气息。“封笔”小说的李国文,转身成为随笔圣手。于说古论今、嘻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毫不留情。从他挖苦的那些死人身上,许多活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能自在。虚荣浅薄如我,领教这些文字,总不由得面红耳赤,如芒在背,“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枚乘《七发》)。
如果说李国文热诚的援手,给予了我坚持写作以切实的扶持,那么他人格的方正,则给予了我做人为文的模范。
后者更让我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