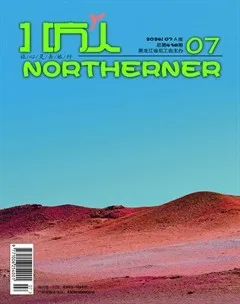没有卫星的古代如何画地图
2024-12-31差评君
由卫星和飞机拍摄底图影像,再加上车采、步采等实地测绘,最后将多个图层数据汇合后就形成了我们在地图软件上看到的地图。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绘刻于宋代,你会发现,该地图中河流的形状、走向和城市形态,简直能和现代卫星地图的精度相媲美。那么在没有卫星的年代,古人如何绘制高精度地图?
指南车与记里鼓车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献图投降”的情节,似乎地图是无比神秘的东西。古代管地图叫“舆图”,“舆”本意是车辆、车厢,所以“舆图”可以理解为坐在车上,将看到的地理信息绘制成图。这个字也表明了古代绘制地图的最重要方式——实地作业。
指南车是古代一种指示方向的车辆,也作为帝王的仪仗车辆。历史典籍显示,三国时马钧是第一个成功制造指南车的人。记里鼓车也是古代天子出巡时仪仗车队必备的典礼车,排在指南车之后。
指南车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行进,车顶小人的手臂都会永远指向南方。这是三国时期的机械大师马钧的发明,也叫司南车。整车都是机械结构,利用了齿轮的差速器原理:小人和车轮之间通过齿轮连接,每个车轮运动都可以带动小人转动。指南车直线运动时,两个车轮同步转动,小人保持静止不动;车子转弯时,外侧轮会比内侧轮转动更快,通过差速器小人就能反向旋转,所指方向就不会改变。制图师因此就能知晓自己的所在方位。
除了指南车,罗盘、指南针、天体方位、树木年轮等信息都会被用来判断方向。有了方向还不够,还需知道距离,所以记里鼓车就很重要了。记里鼓车的结构与指南车类似,车上有两个小人和一钟一鼓,还装有一组减速齿轮与轮轴相连。车行1里时,控制击鼓小人的中平轮正好转动一周,小人就击鼓一次;车行10里时,控制敲钟小人的上平轮正好转动一周,小人就敲钟一次。坐在车上的人只要听到响了几次钟鼓声,就能知道走了多少路程。有了方位和距离,就可以制作最简单的地图了。
比如要画一条河,沿着河走,在河流拐弯处用指南车记录变化的方位,同时用记里鼓车记录走过的距离,那么就可以知道这条河长度是多少,在哪一个地方转了弯,方向变化是什么。用文字记录下来类似于“河流长度100里,河流起点向西,10里后转为西南,再20里后转为南,再40里后转为西”——仅用两辆车就可以把河流山川的走向和特征量化了。
接下来就需要“美编”——画师把这些文字记录画到纸上。这里就要用到绘图工具“规”“矩”和“准”“绳”了。“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方的角尺,“准”和“绳”是测定物体平、直的工具。凭借这些工具和文字记录,再结合画师的想象力,就能完成一幅舆图。
细说《禹迹图》
但以上方法一般用来绘制局部区域的地图,如果需要绘制更大区域的地图,甚至是全国地图,该怎么办?那就要找很多人画不同区域的地图,最后拼起来。这时便需统一比例尺,不然就会出现海南岛比新疆还大的事故。
裴秀是魏晋时期名臣,在他的主持下绘制出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在序言部分,裴秀独创性地提出了六条绘制地图的理论,也叫“制图六体”。前三条“分率”“准望”“道里”是地图的比例尺、方位关系和距离三要素,后三条“高下”“方邪”“迂直”用以描述地形的起伏变化。这是中国古代首次提出,也是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到明清时期都被奉为圭臬。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临,标注经纬线的地图传入,中国的绘图方法才再一次革新。可以说,“制图六体”除了没考虑经纬线和地球投影,其他方面和现代地图学所考虑的因素相差无几。
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中的第一条“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中有一种叫“计里画方”的技巧。现存最早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就是开头提到的《禹迹图》。
这张地图横向有70格,竖向73格,一共5110格,方格边长1.1厘米,对应实际的一百里,因为宋代的1里约等于现在的444米,所以地图比例尺大约就是1∶400万。由此可以推断出《禹迹图》所涵盖的总面积为818万平方公里。这是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最科学的制图方法,地图中海岸线与黄河等河流的形状已和现代地图的测绘非常相近了。这套制图方法在13世纪传到西方时,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图学者采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称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但“计里画方”有个致命缺陷,就是测绘中心区域的精度相对准确,离测绘中心越远误差越大。误差产生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不知道地球是个球体,这个问题直到利玛窦来到中国后才解决。利玛窦为了传教,向万历皇帝展示了很多西方的“奇技淫巧”,其中就有地图投影法。用这个方法可以将地球表面的曲面转换到地图的平面上而减少误差。他还将东西方的地图汇编到一张地图上,而且为了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把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这就成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
但在中国的地图绘制史上,用到“计里画方”的舆图极少,大多数地图都不考虑精细的比例和方位关系。有些地图在画法上非常贴近山水画,没有把实用性和艺术性区分开。比如清初的《江西省舆图》,有山有水有波纹,甚至山边的云雾都描绘得非常细腻。但作为一幅地图,它的透视关系、方位比例都不明确。与现代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惯例不同,中国古代地图并没有这方面的制图限制,《江西省舆图》采取的便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设定,所以鄱阳湖位于地图底部。
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的是该时代对世界的认知边界,地图延展到哪里,认知也就到了哪里。地理大发现时代,地图引领着人类探寻未知,将地球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到现代社会,卫星和飞机让每个人都能像上帝一样俯瞰地球,这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过程又是多么艰难。
(摘自2024年第9期《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