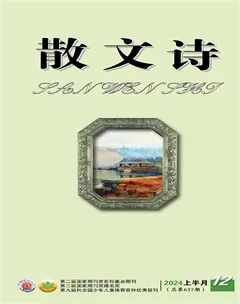坐看云起(外二章)
2024-12-28王志清
人生无非就是一场旅行。人生到处知何似?
一生都在行色匆匆的赶路中。
原先总以为老去离我很远,如今始觉得年轻已逝去很久。
红尘渐行渐远,我却没有驿站,也没有接力,因此也一直散淡不起来。
我来到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我来到了一个到处是路,似乎又无路可走的地方。
真不该有这么多的目标设定;也真不该有那么高的目标设定。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冥冥之中,耳畔响起熟悉的声音,来自诗歌最有统治力的唐朝。呵,这就是禅,是隽永的禅语,是要给我彻悟世事的禅意。
水穷云起,无非妙谛。走到水的尽头而不能前行,便坐看云起变幻。我学会坐下,学会了止念,不再执著于前行之一念,而将自己逼到悬崖峭壁,难再回头。
于是,也卸下了满身的疲惫,坐下来看云。看云起天地外;看云来绿岫中;看云涌如万匹追风的奔马;看云散如没有了轨迹的思想。
原来,可以水穷而不虑心;
原来也可以云起而不动念。
真该努力培养出“兴来每独往”的随性。
一路走去,一切随缘,一切听由兴致,一切听任自然,一切都是自然,一切又都是因缘,一切无非适意,一切皆无可无不可。
行止只是个过程,不问结果,也没有结果。
无论水之穷否,无论行走还是坐看。
没有空间意识,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没有时间概念,想走多久就走多久;不管是一路追随阳光,抑或阳光一路眷顾着我。
我兀自坐看云起。念天地之悠悠,求义理之无穷。
我注定了是个旅行者,虽然已无念进退。
乘兴而游,守道独行而不招负累。我在我的行走中,展示我生命的本来意义,也展示我人性的全部瑰丽。
我似乎这才顿悟: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修行!
空山鹿寨
空山不见人。
那些圈鹿的栅栏,空空如也,早已成为历史的标本,其中没有鹿,更没有人。
空山空得令人战栗,我仿佛一步回到史前,回到混沌之初。
凭着超人的视听觉,肯定能够闻有人语之响的,或许我也正是想要修炼到于无人处而闻有人语之响的境界。
在不见人的空山,闻有人语响,应该不是一种幻觉。
然而,人语之响却让寂寞变得更加寂寞。
我循声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什么,什么也没有找到,唯有内心作出了对于天籁的回应。
踏在深厚的青苔上,像是走进古老的诗歌文本里。
不经意间,有一缕夕照余光返照过来,那是经历了一种沧桑过后的轮回。返照之光,被过滤得一无瑕染的纯净,穿过灵魂,在思想的最穷幽之处烙下了思想的印记。
空山不见人,这是空中之有,还是化有为空?
人在空山,完全是一种绝去执念后的自由心境与闲适状态。
没有事先设计,没有预期目标,更不是苦心孤诣的追求,却让我摆脱了所有束缚,不为物累,不为形役,澹泊超然,在机缘凑泊的遇合中感受人生乐趣。
我在空无与实有之间跋涉,我在现实与梦境之间徜徉,我在静谧与喧嚣之间选择,我找到了与我灵魂对话的最佳方式与时刻。
我也能够消弭自然之理与人世之事的界限吗?
空山不见人,我来何为?我在追问我自己。
我在空山,找到了什么?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无中之有,有亦是无。
来过空山,心空如山,再也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失去自我,放下了内心诸多无谓的纷扰,从世俗的忧虑与烦恼中解脱出来。
若是重回喧嚣,面对尘世,自然也会更加从容和平静,因为,我已找到了属于我的节奏。
遍插茱萸
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流寓者,一遍又一遍地走向九月,又走到了重阳。于是,我就在书房里登高,西西弗斯那样地登山。
书房里有无数的山,中国的山和外国的山,远古的山和近世的山,陡峭的山和平缓的山,生长茱萸的山和不生长茱萸的山……
不是九月九,我也在登山。
我就是一个流寓者,因为,我走不出乡愁,也走成了个精神漂流者的样子。
走在乡愁里,最幸运的邂逅就是,撞见了王维忆山东兄弟的那朵茱萸。那是朵可以辟邪的茱萸意象,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引领,让我不会有寻找家园的畏惧和倦怠。
王维不堪乡愁,在辋川别业附近营造了一个茱萸游,他是怕在乡愁袭来时无茱萸可插。“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茱萸果从翠绿转为花样的鲜红,这朵王维的意象,唐诗的经典意象,也一定在我的心性里寻找到了滋养和葳蕤的美学渊薮。
也许正是如此,我也有了遍插茱萸而少我一人的感觉。
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王维深深的内疚,一种流传千古的深不可测的疚恨。这种疚恨和乡愁交加的乡愁,被古人说成是“加一倍凄凉”的思念,弥漫了古今,像是一些沉静而忧郁的阳光无处不在地弥漫,没有天老地荒地弥漫。
我已经不怕乡愁的感染。
我的最佳选择就是走向王维,寻找到寄托我漂泊灵魂的精神家园。
我奋力走过去,走向王维,走过千年,从诗歌文本走向自然山水,在实物茱萸和意象茱萸之间流连,从感性走向理性的登高。
仿佛我天天都在登高中。
我自故乡来,故乡的寒梅已经开过。
我没有被故乡放逐,却在放逐故乡,放逐乡愁。
我想到重操旧业,也写诗或诗样的文字,让这些诗将我放飞得远远的,远到天尽头,远到乡愁无法渡我。
我找到了我想要插的那株茱萸,似乎也找到了插茱萸的感觉。
呵,我在九月九那天登高。我天天都在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