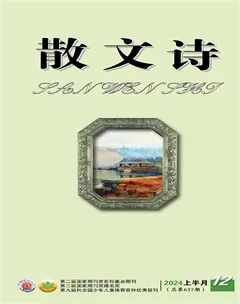风会不会像我一样想
2024-12-28徐金秋
翻找
不读书,不写字。
看所有花,不是花,所有景,不是景。这个春天,注定是用来铭记的。
借助一块荒芜的土地。拔,挖,每天重复,仿佛在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用尽所有力气,和悲伤。
拔到一棵草的根部,想问是否认识去年寒冬,被埋进土地的那个人,她的命也是草。
挖到最深处,有一股彻骨的泥土香。从来没像此刻这样,觉得泥土有多可亲。真想一口气将大地,挖成天大的窟窿。
不停地拔、挖。直到无声处时,雨点就落下来。
花都开好了,就差你
这是你常坐的地方。
她们都来了,一朵一朵笑在春的枝头。你是不是也来了,告诉我,哪一朵是你。若在其中,我就知道你是笑着来的。
若没来,就借一万朵花香,呼唤你——母亲。
原谅
她背着苦难的大山,一辈子,未走出大山。
也好,老了是一座大山背她,命运互换。
而大山背起她,是轻飘飘的。尽管她以肉身之躯,筑起一座小山丘。
夏日的密林,很快会淹没它。秋天的枯叶,很快会覆盖它。
渐渐,她成了大山的一员,融人了这座大山。
我这才学会了原谅。原谅了山,原谅了命运。只求一只蚂蚁,能绕过她;伸展过来的根须,也让一让——
成全她,做一回自己。
再次到同济
此处依然那么熟悉。“同济医院”几个大字,长廊,广场,来回滚动的轮椅,和花坛几树静默的花。
只是这开着的,不是那年的桃花,人也不是那年的人。
是的,那年病重的你,依然有望可期。桃花开得散淡,却与那年的春天是如此契合。因而,我们的缘份也在继续。
七年后的今天,我来了,仿佛该来的人都来了。虽带病体,但全是奔着生的希望。唯你不会再来,你只是停留在那年,此处,我记忆的一缕风。
人生很短,即便是母女,缘份也仅仅,那一点点。
看来往的人群,我忽然,泣不成声。
妈
妈,不是一个字。
是一个家。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门。出去时,有人守;回来时,有人开。
是喊时,需憋足气息,然后,自然放出一个轻声调:“妈”。
请小声点,再小声点,千万别和世上那个最疼你的人,大声说话。
年幼无知时,认为“妈”只是一个女人,和“马”谐音。有事无事便唤:妈,妈。
当我做了妈后,才知妈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自有了孩子后,甘于做牛做马的人。
直到老得爬不动了,我改叫娘。
只有像“娘”这样的,才称得上世界最善良的女子。
直到后来,喊什么都没了回应。
路过寨头
只要路过,我就会想起一个女人。
这里是她的娘家,自17岁离开,只成为了一个念头一
她的父母埋葬在此。她的兄弟在此生儿育女,延续王家烟火。心灵受到创伤,还有一个家可回。
她常常望向那条路。看有没有兄弟的影子,若是望见,大老远就会喊阿哥阿弟。
拿出家里仅有的,也是最好的东西,招待她的手足亲。走时,会相送几里,直至望不见,才依依不舍,返回。
一辈子只是远远地望,极少回娘家。
那个年代,“娘家”是个不能去轻易触碰的词。除非受到极大的创伤。除非被男人休掉。
回过几次,只有她自己知道。
回去,娘家嫂子将她当男劳力。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插秧、割谷、挑水、挖红薯。
对她翻白眼。
倔强的男人坚决不去接。
十天半月后,那个一生要强又要脸面的女人,在想儿女的夜晚,终向哭泣的泪水低头。一大早跑回来,背一身黑瘦和露水。
后来,男人打死她也不回娘家,只是望。
当那条路被碾压在我的车轮下,我会想起那段岁月,那个女人的路,已望断。那个女人就是我乡村的母亲,永不再醒来。
只留下两条又长又深的车辙。
豆角,是乌铜色
秋天的寒露在它们身上停留。秋天的暖阳也照耀过它们。
于乌铜色豆角,并不耽误每一寸生长,所以,存在并不矛盾。
乌铜色,粗短,出产率高。适合七八月份播种,生长期可延续到秋霜后。像极了山里人迟钝的反应,也像极了他们的命,清苦,寒凉。
一切与山里的气息,是如此吻合。一切,也是母亲的最爱。
她年年会种出这晚来秋的收获,像意外的惊喜,见人即夸。夸耀乌铜色豆角的同时,也炫耀犒赏一把自己。
那时候,我年少无知,经常翻白眼于她:“有什么好炫耀的。”
现在,我也种上了它。我的喜欢,像是她的重复,命运的重叠。风吹来时,无数根豆角在清凉的晚秋,微微颤动,像极了手指。
粗短,乌铜色。
可惜,我的喜欢太迟,母亲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风会不会像我一样想
风会带来一切,也会带走一切。
比如春天,比如秋天。大片大片的,而又那么不经意。
既粗犷,又细化。粗犷到山头田野,以至奔腾的长江黄河;细化到一缕炊烟,一粒草籽,以至抖动的一片叶子,一丝情绪。
温柔,暴躁。青春,衰老。鲜活,灰暗。笑容,泪滴。
相互渗透,纠缠交织,相互矛盾。
多么像一个人。一个女人。
那是他的恋人,妻子,我的母亲。
那是大地,月亮,倒映到水面上的蓝,和云朵。
那是凋落,飘散到冬日,干枯的样子。
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原来,这么久了,我依然害怕,不敢触碰“娘”这个字。
我让时间将之——淡化到一个女人,和她。粗放到一片旷野,细化到一粒尘土。
只有风吹过来时,我才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