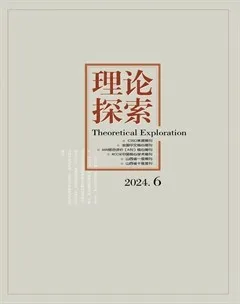“双碳”背景下我国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难题破解
2024-12-28任超田其云
〔摘要〕全球平均气温的不断攀升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共同关注的焦点。我国已将“双碳”战略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通过司法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愿望与行动,虽然有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等请求权基础的支撑,但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仍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违法性、碳排放与气候变化间的因果关系举证难、认定难等理论困惑与实施难题。各种阻却因素使得气候变化侵权诉讼至今未能正常进行。深入研究可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与认定,无需违法性这一构成要件,近些年不断提升的科技监测手段,可以确定碳排放与气候变化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相当因果关系说”也为此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进,对气候变化侵权责任违法性的认定观念得到更新,因果关系证成等理论困惑与实施困境被逐一破解后,建立与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制度可期可待。
〔关键词〕“双碳”,请求权基础,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碳排放的违法性,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4)06-0110-09
随着全球极端气象灾害的频繁发生,气候变化问题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积极行动,先后订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国际气候治理性文件。在此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提出了各自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标。我国政府于2020年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希望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地方政府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下,单纯通过行政、经济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显得捉襟见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显然不能脱离法治轨道这一基本框架。在此背景下,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早已进入国家规划之中,国务院于201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明确提出研究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并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进行了修订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司法实践中,“自然之友诉国家电网甘肃分公司弃风弃光案”②等涉及二氧化碳排放的案件在近些年逐渐涌现,虽然案件诉讼请求并未延伸至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但案件所涉及的碳排放行为导致的环境权益损害以及赔偿等问题,已逐步指向气候变化诉讼。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与应对气候变化民事诉讼相配套的法律依据,使得该案件经过七年的漫长审理,受理该案件的法院也仅能认定被告不全额收购风电、光电的行为,间接致使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违反了《可再生能源法》,案件最终只能以调解方式结案〔1〕。气候变化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表明,由于诉讼权利基础模糊不清、碳排放行为违法性认定存在争议、碳排放行为与气候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无法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上大步推进。通过对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责任成立认定所面临法律困境的剖析,破解相关理论难题,消除相应的司法障碍,可以探寻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实现路径。
一、气候变化诉讼的兴起与界定
自1979年在瑞士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③后,气候变化问题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气候变化”一词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也已被作了扩大解释,该概念已由过去的温度、降水、风、日照、辐射等导致的气候变化,指向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趋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的“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④。在大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场景中,“气候变化”一词排除了因自然原因导致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或降低,仅指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平均气温异常变动。因此,气候变化已由过去单一的自然科学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经济以及环境伦理等多领域交叉的问题。
自18世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以蒸汽机、内燃机、发电与电动机为动力的工业生产模式逐步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得到迅猛提升,随之而来的大机器生产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平均气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迅猛升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八大公害事件”⑤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轰动全球,引发了各国公民对于环境损害议题的热议。此后,随着全球平均气温的不断攀升,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这一观点被科学证实,法学研究者由此萌发了以司法手段控制气候变化的思路。
气候变化诉讼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美国,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后,气候变化诉讼在全球范围快速拓展〔2〕。作为一种新兴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意在通过司法手段,促使化石能源消费企业受到法律制裁,使气候变化受害者因此得到补偿。该理论及制度的产生,与全球极端气象灾害的频发,与人类对于共同居住家园环境的忧患意识的提升密不可分。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受惠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影响,气候变化诉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一般将“气候变化诉讼”分为“广义气候变化诉讼”和“狭义气候变化诉讼”两类。澳大利亚学者Hari Osofsky与Jacqueline Peel认为,气候变化诉讼不仅包括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焦点的案件,还应包括:(1)明确提出气候变化的问题,但气候变化并非核心事由的诉讼;(2)以气候变化为其动因之一,但并未明确提出跟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诉讼;(3)没有提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争议,但对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明显影响的诉讼〔3〕。根据该观点,案件内容只要涉及气候变化议题,均可以被认定为属于“广义气候变化诉讼”。与此相对应的是“狭义气候变化诉讼”的概念,部分学者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成为诉讼的中心而非边缘,它直接以应对气候变化、救济环境公益为诉讼目的〔4〕。狭义的气候变化诉讼,仅指直接和明确提出与气候变化或气候变化政策有关问题的诉讼,其诉讼目的在于通过追究行为人直接实施的气候变化的危害行为,以保护气候变化过程中受害者的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以下简称《统计规范》),首次设立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这一新的案件类型,“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被定义为“在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⑥。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以《统计规范》的方式,确立了我国司法机关采用“广义气候变化诉讼”的模式,涵盖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影响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类诉讼〔5〕。
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特有属性及本质属性的认知和反映。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6〕504在“双碳”背景下,对气候变化诉讼的概念采用不同的定义方式,将导致立法目的、保护对象以及裁判结果大相径庭。诚然,采用“广义气候变化诉讼”的定义模式,能够涵盖大量涉及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案件,使气候变化立法呈现出体系化的特点。但是,依据“广义气候变化诉讼”的模式将各类与气候变化有关联的案件,以兜底的方式堆放至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中,显然并未考虑到气候变化问题所具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必然使司法实践操作困难重重,甚至无法向前顺利推进,最终使得气候变化诉讼中最通用最多见的侵权诉讼,丧失其作为一种新型案件的存在价值和应有地位。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修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已将“碳排放权交易纠纷”“碳汇交易纠纷”纳入到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中,适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⑦。司法规范的制定者,将以追究当事人违约责任为目的的“碳排放权交易纠纷”“碳汇交易纠纷”纳入气候变化诉讼体系中,显然与司法手段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诉讼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气候变化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威胁,在国际协作、行政管理等手段不见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希望通过司法手段,追究化石能源消费企业对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成员损害责任的承担,进而反向制约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者的排放行为。而“广义气候变化诉讼”模式的选择,显然忽略了在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重大威胁时,人们更加强调温室气体排放者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成员责任的承担。
毋庸置疑,在目前我国“双碳”背景下的气候变化民事诉讼,必然是以民事侵权诉讼为主要形式的诉讼,诉讼动因是行为人的过量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受害人的利益遭受到损害,受害人则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因此,讨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最现实、最切合社会实际的当务之急。
二、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权利基础
截至目前,由于我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以及相应的民事判决,因而将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理念转化为司法实践,将会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过程,这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明确当事人因何而起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曾在其《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一书中谈及“谁得所向,依据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此种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Anspruchsnormengrundlage),简称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7〕41。请求权基础在气候变化民事诉讼中同样必要,依此理念可以认为其涉及三个关键问题:一是谁可以向谁提出请求;二是依据什么进行请求;三是具体请求的内容是什么。诉讼请求权基础作为司法审判的核心,首先得解决当事人依据何种权利提起诉讼的问题。正确理解诉讼请求权基础理论,是解决诉讼争议和保护诉讼权益的关键,涉及整个诉讼方案的构建。根据请求权基础的不同,环境民事责任分为传统环境民事责任和新型环境民事责任。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环境民事责任称为传统环境民事责任,侵犯环境权益的环境民事责任称为新型环境民事责任〔8〕325。在此基础上,域外国家在探索气候变化诉讼司法的实践中,法学研究者分别提出了以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以环境权为请求权基础的气候变化民事诉讼请求权。
(一)以人身权、财产权为请求权基础的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
在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人以环境资源为媒介对其构成污染与破坏,最终因环境污染导致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因此,受害人通常以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着重围绕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受到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审查,依据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决。与此相通,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化石能源消费者的碳排放行为引起全球气候异常,导致被侵权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损害。因此,以人身权、财产权作为气候变化诉讼的权利依据,为气候变化受害者的受损权益提供了损害填补机制,使其人身权、财产权恢复至权利被侵害前的原有状态。
与其他抽象请求权的概念相比,人身权、财产权作为各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传统诉讼请求权利,更容易被诉讼参与人接受。因此,受害者以人身权、财产权作为诉讼请求权基础,通过气候变化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案件广泛出现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2012年,美国阿拉斯加基瓦利纳原住民村诉埃克森美孚公司一案(Native Village of Kivalina v. Exxon Mobil Corp),原告基瓦利纳原住民村的村民认为,埃克森美孚等二十四家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侵蚀了原住民村的土地,使其居住地面临毁灭的威胁⑧。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埃克森美孚等二十四家公司,承担因侵蚀海冰而需要重新安置居民所需要的9500万至4亿美元的费用。该案经法院审理,虽然认定原告因不能证明温室气体排放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且气候变化问题属于政治问题,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但是当事人尝试以财产权益受损为由,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引入民事侵权责任以寻求司法救济,为探索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法律路径提供了实践方案。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推进,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气候变化受害人通过向法院请求化石能源消费企业承担因气候变化导致的责任,符合法律倡导的公平与正义理念。我国《民法典》通过专门的章节,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为以人身权、财产权作为气候变化民事诉讼权利基础,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及相应的法理支撑。除此之外,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以人身权、财产权为权利基础的责任构造要件,重视私权利的保护,符合审判人员和诉讼参与人的传统法律思维逻辑与诉讼习惯,使案件能够在传统的审理模式中快速审结。但是,受害人以人身权、财产权为基础提起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企业碳排放行为的违法性认定、碳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等诸多挑战,亟待法学研究者作进一步探索。
(二)以环境权为请求权基础的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
气候变化问题不但影响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将影响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起,环境权理论的发展,逐步成为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石,这也为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环境权强调人类社会具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和权利,在气候变化诉讼制度尚未健全的背景下,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类应有的起码道德权利客观存在。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型的法定权利,在实体上赋予民事主体基本的民事权利性质,环境权所涵盖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既包含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也包含因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公民向司法机关诉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9〕73。2005年12月,63名因纽特人以北美全体因纽特人的名义,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起对美国的诉讼。原告认为,美国未能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气候变化政策,拒绝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作出努力,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违反了《美洲人的权利义务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中赋予因纽特人的居住、活动、健康、环境以及良好生活和家园不容侵犯等权利,诉请美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⑨。此案最终虽然未能被泛美人权委员会受理,但是引发了学者对于气候变化与环境权理论的关注。环境权既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的基础〔8〕114。
近几十年来,极端气象灾害频繁出现促使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如果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问题最终必然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其权益。在传统环境民事责任中,强调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但以人身权、财产权为基础的民事侵权诉讼陷入因果关系证明等诸多困境,导致气候变化受害者难以获得司法救济。与此相对应的新型环境民事责任,则关注、强调和保护的环境权益,即使污染行为没有损害人身、财产,而仅仅损害了环境,也认为该污染行为应该承担环境民事责任〔8〕326。随着气候灾害的日益严重,气候问题导致的损害已扩展至整个社会公众利益,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分子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实施的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首次将“环境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并列成章,并在该章节中对“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规制,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提供了政策依据。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已经不仅是因温室气体排放而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更关系到人与环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气候变化诉讼的设立以环境权理论为基础,视为是对人类共同居住家园的整体利益考量,体现了人类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一致。与环境权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丰硕成果不同,环境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长足发展,我国《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并未设置关于环境权的相关条款。因此,环境权目前更多地停留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环境权难以作为请求权基础被承认。以环境权作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权利基础的立法理念,游离于我国司法实践之外,环境权更难以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得到实际应用。
三、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责任构成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及其破解
在环境保护思潮与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环境法学理论不断发展,部分法学研究者认为,通过追究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的侵权责任,有望成为解决气候变化民事责任的“灵丹妙药”。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大学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数据库统计,截至2019年12月9日,全球共有1667件与气候有关的案件,其中发生在美国的1340件,发生在美国之外的327件。在这327件气候诉讼中,296件被告是政府,31件被告是企业或个人〔10〕。欧美的气候诉讼中,行政诉讼的主要诉求为请求制定温室气体排放规则、制定或修改气候保护计划的开发,近些年一些著名的案件几乎是以行政诉讼的形式出现〔11〕。虽然气候变化诉讼在欧美国家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但是气候变化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数量较少,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迄今为止,立法上只有肯尼迪2016年的《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第23条明确支持这种诉请〔12〕。各国气候变化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获取的悲观统计数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针对气候变化民事侵权的全新诉讼制度,有必要对其所处法律困境的原因、面临的主要难题、破解难题的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剖析。
(一)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违法性认定的难题及其破解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环境侵权责任应当属于过错责任。一般而言,因过错所致的侵权责任,应当具备“存在侵权行为以及行为具有违法性、存在客观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在认定环境侵权责任时,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通常会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确定性构成要件,认定侵权责任的争议通常表现于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质证过程。然而,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尽管被诉方最终可能也需要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但被诉方的行为是否应当存在违法性,以及如何认定排放温室气体行为具有违法性?不仅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也是困扰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一个突出难题。
毋庸置疑,在传统侵权责任理论中,构成侵权损害责任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为前提。因此,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行为人排放二氧化碳的行为应当满足“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一要件。然而在现实中,化石能源消费企业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同时,也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二氧化碳广泛出现于能源保障、物流运输、食品加工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环节。温室气体排放者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远大于其排碳的负面作用,其行为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理念。即使是极端环保主义者,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能够完全禁止二氧化碳的排放。排放二氧化碳多为各社会主体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难以认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因此,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排放二氧化碳具有违法性作出过规定,《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仅仅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作出了协同控制的规定,并未将温室气体认定为大气污染物⑩。《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使命难以让其功能辐射至低碳领域〔13〕。
由联合国气候大会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案。《京都议定书》关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确立,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我国于2020年12月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规定,针对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等特定行业,且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单位,应被列入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向重点排放单位分配碳排放配额,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国家可以适时引入有偿分配。根据该规定,碳排放权来源于政府无偿发放配额或一定条件下的有偿分配,其性质与行政许可并无差异。重点排放单位在配额范围内的排放行为,得到了行政主管部门的背书,其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对于重点排放单位超出碳排放配额的行为,其依然可以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方采购碳排放配额,如此一来,重点排放企业的排放行为难以认定为普通侵权责任中的违法行为。而对于重点排放单位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等行为,根据情节不同,属于行政违法或刑事违法,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所限定的民事违法行为。
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环境侵权法律体系下,违法性作为成立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受害人如果无法举证证明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具有违法性,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诉求将难以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支持。更为不利的是,在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中,行为人往往是掌控着国家能源与民生的国有企业、大型私有企业,受害者多以受气候波动影响较大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生产者为主。气候变化侵权行为人与气候变化受害者之间,在社会地位、举证能力等方面相比,受害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此背景下,如果教条地、刻板地将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无异于加重了受害人诉讼的证明责任,让其去挑战不可能,这将致使以司法手段降低化石能源消耗企业碳排放行为的目的难以实现。
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致使环境侵权案件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环境侵权责任应当具备违法性的观点,越来越难以解决当今严峻、复杂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在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侵权案件中,行为人实施了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并不能因其排污行为具有合法性而免除环境侵权责任。由此可知,部分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非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实施的合法行为产生了环境损害后果,依然应当对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14〕。自18世纪60年代起,以大机器生产代替传统手工生产的工业模式,决定了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具有相应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此看来,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仅包含气候变化损害事实及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当事人行为的违法性不应当作为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否则,“违法性认定”将成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之桎梏,使得气候变化侵权诉讼无法进行。因此,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最终走出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及必由之路。
需要注意的是,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等于环境侵权责任人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为过错,不等于其行为后果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行为人实施了不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违反了具体的强制性规范,其内容是禁止实施具有某种抽象危险性的行为,例如在法律规定碳排放配额制度的情况下超出碳排放配额,其碳排放行为仍然是具有违法性的。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比例责任的方式合理分配碳排放者的侵权责任。
(二)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因果关系认定的难题及其破解
因果关系的确立,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果,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15〕65。在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中,如何认定化石能源消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难的工作。由于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寻找其中的一个或数个气候变化的原因,推导出这些特定原因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的联系。但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现实中难以将不同的行为上升为某个或数个特定的原因。
气候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全球气温始终存在着起伏波动。人们通过对动物骨化石、植物沉积物及其他遗迹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过程不但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还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可否认,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后,毫无节制地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累积叠加效应,确实导致全球气温的逐步升高,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受到地球轨道和天体位置的影响,地球本身存在着冷暖交替的周期。人类生存生活的地球家园,经历了距今约85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温暖期,也经历了距今约5000年的尧舜小冰期,这样剧烈的气候变化绝非人类活动的微弱力量所能阻止或推动。在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中,如何分配人为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各自作用的参与比例,不仅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理论难题,更是确定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司法难题。除此之外,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具有稳定的累积性。在我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大气中存在了数千年。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为因素导致的碳排放量增加,全球平均气温正经历着缓慢的、逐渐的增长过程。即使人为排放二氧化碳的行为被停止,气候变化极有可能仍然持续几个世纪,气候变化在人类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转的〔16〕。
公平,作为法学理论的基石,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即使是能源供应、钢铁冶炼这类化石能源消费大户,其碳排放量在整个人类工业文明过程中所占的排放比例仍然十分微小。通过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向化石能源消费企业寻求侵权损害赔偿,意味着当代人承担前人的排放致损结果,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法治基本价值取向。因此,在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中,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成是其成立的最大困境。当事人不但需要证明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还需要证明被诉化石能源消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特定损害结果的参与份额。受此影响,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在过去的各国司法实践中难以获得全面支持,司法手段难以对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进行有效制约管控。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前者在后者所占比重的认定、相应的举证责任及举证难度,都一直被认为是阻碍司法近乎无解的难题。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过去几百年间急剧增多,也带来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能够引起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观点已经逐步被科学所证实。这也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暖之间因果关系的成立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2023年3月20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AR6 Synthesis Report《Climate Change 2023》),以权威的方式,通过科学的视角对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进行精准阐释。报告中对“人类活动在全球变暖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的认识,措辞从之前的“可能”“很可能”“极有可能”“明确的”,升级为“既定事实”和“毋庸置疑”,即“毋庸置疑,人为影响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17〕。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前发布的五份报告相比,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首次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必然联系。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证明,推动了气候变化诉讼由理论构想走向司法实践。
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的责任认定中,如何判定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特定损害结果的参与度,虽然为气候变化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一大难题,但得益于科技手段在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这一难题有望得到解决。2015年,在卢西亚诺·柳亚(Luciano Lliuya)诉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RWE AG)的案件中,当事人诉称莱茵集团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致使其位于家乡秘鲁瓦拉兹(Huaraz)附近的冰川融化,冰雪融水引起帕尔卡查湖(Palcocha)水位上升,洪水风险威胁到瓦拉兹居民的安全11。法院在受理该案后,在科学研究者的协助下,确定莱茵集团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特定损害赔偿结果所作出的“贡献份额”。科学家分别选取全球不同的化石能源消费头部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每一企业消费能源总量进行统计,继而推算出该企业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经过对不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排名,最终计算出全球90家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累计排放了全球63%的温室气体。莱茵集团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名单中排名第23,排放总量占比为0.47%,莱茵集团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导致全球气温上升0.003摄氏度,对全球变暖的“贡献份额”为0.321%。科学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最终将莱茵集团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为与瓦拉兹(Huaraz)地区居民遭受洪水灾害之间的关联度提升到95%以上。然而,与自然科学通过模型建构推导出因果关系的方式不同,司法程序中因果关系的成立,依据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在卢西亚诺·柳亚(Luciano Lliuya)诉莱茵集团的案件中,当法院给予受理许可之后,该案进入专家评估阶段。科学家作出的莱茵集团对损害“贡献份额”的结论,也仅能以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的证据形式影响法官判定因果关系链条是否成立。侵权诉讼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最终依赖于法官的内心确认,法官才是因果关系成立的决定者。然而,可以明确的是,一旦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参与度可以被科学认定,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因果关系的定性和定量难题均可得到解决,这无疑会使各国相应的司法实践看到科技革命与进步为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带来的希望。
由于各国在处理侵权案件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案件的诉讼理由繁多,不同案件的因果关系链条也因此大相径庭。由此导致在各国成文法中,缺少关于因果关系成立标准的法律规则。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述,“关于因果关系各国法律未多规定,系由法院实务创造不同的概念或理论,以界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生损害,应负责任的范围,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或思考方法”〔18〕180。社会生活中因果关系链条的多样性,立法者难以对此作出细致的规定,法律原则就此成为补充法律漏洞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它可以使法律对规则空白地带的事项加以调整〔19〕124。由于侵权责任法中缺乏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明规则,法学研究者在理论探索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必然因果关系说”两种判定因果关系成立标准的法律原则。“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因果关系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构成适当条件,就成立因果关系。与此相对应,“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9〕186。根据“必然因果关系说”,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只有在足以证明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碳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必然因果联系,侵权行为人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无法排除自然原因等因素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可能性时,侵权责任无法成立。显然,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任何专业机构都无法对被诉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特定损害结果的参与度做出精准认定。如此一来,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就如同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望而不可及。然而,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气候变化侵权诉讼中,企业碳排放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要求达到完全排他的证明标准,只要法官在考虑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时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后,气候变化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即可成立。气候变化侵权行为由于具有累积性、持续性、潜伏性、公害性等特点,致使因果关系判定十分复杂。“相当因果关系说”,破解了气候变化侵权案件等涉及环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难题,在我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背景下,为走出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困境提供了法理依据。
四、结语
气候变化作为21世纪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涉及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受制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所需资金的缺口巨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分歧重重。立法者寄希望于通过民事侵权诉讼方式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继而补偿气候变化受害者的权益损失,这无疑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然而,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受制于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违法性认定困难、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多种难题及困境的影响,这也使得气候变化侵权诉讼始终停留在立法规划层面。
得益于环境法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以大气污染、水污染为代表的环境公害事件所产生严重后果的警示,在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行为的违法性”这一要件被逐渐淡化。2023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以权威的视角和确定的方式,证明了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的必然因果关系。域外国家经历了30余年的司法实践,通过自然科学模型建构的方式,可以证实被诉侵权行为人对特定损害结果的参与度。随着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不断积累和各国间的互相借鉴,气候变化诉讼中固有的因果关系、起诉权利依据等理论与实践难题均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样本和成果〔20〕。环境法学理论的不断革新以及科技水平的进步,也为中国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提供了破解难题的新思路。
化石能源在工业文明中的地位使得人类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对煤炭、石油的依赖,气候变化诉讼的立法目的绝非将所有碳排放主体引入至司法审判的聚光灯下进行审查。气候问题的严峻性决定了有必要对那些通过牺牲环境利益而索取巨额利润的能源消费巨头的碳排放行为,通过气候变化民事侵权诉讼的司法手段,进行必要的约束与规制。
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11月22日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提出我国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前期研究工作”的立法部署。
②参见:甘肃矿区人民法院公告(2019)甘95民初7号。
③1979年2月,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参会科学家警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从此,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④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数字图书馆官网(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691248?ln=zh_CN)。
⑤20世纪30年代起,部分西方国家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因环境污染发生的八起轰动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分别为: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⑥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4日印发的《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将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定义为:“在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
⑦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印发的法〔2020〕346号,《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通知,在第二级案由“十、合同纠纷”项下增加了“100.碳排放权交易纠纷”、“101.碳汇交易纠纷”。
⑧参见:Native Vill. Of Kivalina v. ExxonMobil Corp.,696 F.3d 849,858(9th Cir. 2012)。
⑨参见:Sheila Watt-Cloutier,Petition to the Inter 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December 7,2005(http://www.westlaw.com)。
⑩《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源头治理,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11参见:Saúl Luciano Lliuya v.RWE,(2017)20171130,Case No.2 O 285/15。
参考文献:
〔1〕张 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R〕.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3.
〔2〕杜 群.《巴黎协定》对气候变化诉讼发展的实证意义〔J〕.政治与法律,2022(07):48-64.
〔3〕Hari Osofsky,Jacqueline Peel. Litigations Regulatory Pathway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Lessons from U.S. and Australia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J〕.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13(25):208-216.
〔4〕张忠民.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范式——兼谈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J〕.政治与法律,2022(07):34-47.
〔5〕孙雪妍.气候司法法理功能的再思考〔J〕.清华法学,2022(06):194-206.
〔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0〕Juliana v. United States, 217 F. Supp.3d 1224(D. Or.2016)(No.15-cv-01517),p.279.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71d109b04426270152febe0/t/57a35ac5ebbd1ac03847eece/1470323398409/YouthAmendedComplaintAgainstUS.pdf.
〔11〕张 挺.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下中国气候民事诉讼的理论障碍与进路〔J〕.云南社会科学,2023(04):79-91.
〔12〕谢鸿飞.气候变化侵权责任的成立及其障碍〔J〕.政治与法律,2022(07):2-17.
〔13〕李艳芳,张忠利.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5(03):30-34.
〔14〕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5〕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16〕RetoKnutti,JoeriRogelj, The legacy of our CO2 emissions:a clash of scientific facts, politics and ethics〔J〕. Climatic Change,2015(03):361-373.
〔17〕The Core Writing Team Synthesis Report IPCC,AR6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23 〔R〕. Geneva: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23.
〔18〕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20〕高利红.我国气候诉讼的法律路径:一个比较法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1):167-176.
责任编辑 杨在平
〔收稿日期〕2024-07-17
〔作者简介〕任 超(1984-),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田其云(1966-),男,重庆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