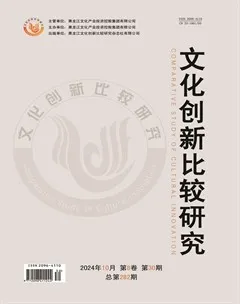语境研究的进路、困境与出路
2024-12-25李小红
摘要:语言学语境研究经历了三重进路,即语言语境研究、情境语境研究和认知语境研究。认知语境研究作为语境研究的新近发展,核心观点是视语境为心理建构体。以范·戴克为代表的认知语境学者,建构了理解话语的语境认知模型,认为语境是社会情景与话语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自范·戴克以来,认知语境理论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挑战正陷于困境。该文在梳理语言学语境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认知语境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并试图对语境研究的出路提出解决方案。语境研究从“解释框架”向“话语生态”的转变,可视为一种范式变革,它为语境研究开辟了新的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对语境研究走出困境做出了积极尝试。
关键词:语境;语言语境;情境语境;认知语境;语境认知;话语生态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0(c)-0015-06
The Approach, Dilemma, and Way Out of Contextual Research
—From "Cognition" to "Ecology"
LI Xiaohong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contex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namely linguistic context research, situational context research, and cognitive context research. As a recent development in context research, the core viewpoint of cognitive context research is to view context as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Cognitive context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van Dijk have constructed a contextual cognitiv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believing that context is an intermediate link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ituations and discourse. Since van Dijk, cognitive context theory has been struggling due to its own insurmountable challenge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linguistic contex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gnitive context, an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ttempt to propose solutions for the way out of context resear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xtual research from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to a "discourse ecology" can be seen as a paradigm shift, which has opened up new cont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contextual research and made positive attempts to overcome its difficulties.
Key words: Context; Language context; Situational context; Cognitive context; Contextual cognition; Discourse ecology
在语言学及相关学科领域,西方的语境研究存在三重推进,第一重是语言语境研究,第二重是情境语境研究,第三重是认知语境研究。范·戴克(Teun A.van Dijk)于2008年出版的《话语与语境》,被认为是语境认知转向的代表作之一。然而继范·戴克之后,语境应用研究成果不断累积,但基础理论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认知语境研究,包括范·戴克的“语境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其问题核心在于,持认知语境观点的学者,认同语言是心智的功能,但无法对心智本身进行科学研究,因而他们的理论在面对模型的科学性、实证性质疑时无法给予充足的回应。
1 语言学语境研究的三重进路
1.1 语言语境
语境研究的第一重进路是语言语境。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学者们深受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研究思路的影响。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言语活动=语言+言语。他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因为语言是从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实体,在抽象的过程中,必须把所有的个人要素和个人杂质排除出去,语言学只有纯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对象建立在有着内在一致规律并成系统的“语言”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故而,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语言内部,将语言视为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虽然索绪尔提出语言中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句段关系指语言的横向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的联想而产生,指语词的纵向聚合),但是“联想关系”这一蕴含认知语境萌芽的概念被后继学者忽略了,片面发展了“句段关系”。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语境并非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只是寄居在上下文关系及语篇修辞等研究中,语境的元理论属性未被发觉,甚至“语境”这一概念虽然早在1885年就被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Wegener)提出,但直到1923年被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再次提出才引起关注。
1.2 情境语境
语境研究的第二重进路是情境语境。局限于语义学的语言语境研究,逐渐暴露了它无法支撑“意义”理解的缺陷。在一段流动的对话中,语言和情境往往是耦合的,听者依靠情境理解字面上省略或者隐含的信息,而说者依据情境策略性地表达自己的意图。种种迹象表明,文本本身无法完成全部的意义建构,在语言语境之外,还存在对语言理解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而学者后来将这些由情境产生,并对语言生产和理解产生作用的因素称为“情境语境”。
与情境语境相似的概念,最早由前文提及的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他使用的是“情景语境”,其语境思想开创了语境研究的语用学路径。马林诺夫斯基的同事弗斯(Firth)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引入语言学界,建构了“意义的语境理论”,并且创造性地对“情境语境”进行了变量分类。韩礼德(Halliday)师从弗斯,是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吸收了情景语境变量的研究成果,逐渐把语境视为语篇之外的情景因素,提出了“语域”这一概念,包括情景语境组合的三个变量: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并认为这三个变量支配着语言的变体。韩礼德认为,“语域理论就是要揭示出支配这些变体的基本规则,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何种语境决定使用何种语言变体,这是使用中的语言变体的基本特征”[1]。
与韩礼德持相似观点的语言学者,一方面热衷于发掘、区分各种情境语境变量,如美国学者海姆(Hyme)就提出了SPEAKING理论,将语境变量分为8个项目;另一方面试图研究情境语境变量与语言形式选择、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情境与话语的关系。但是以韩礼德为首的功能语言学派,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无法解决“语境框架”问题,他们不是将情境语境变量划分得过少且抽象,就是将变量划分得过多且具体;二是受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在语境研究中排斥“认知”“心理”等主观因素,这使得他们的理论难以解答一个关键问题:情境语境何以能影响话语?
1.3 认知语境
语境研究的第三重进路是认知语境。1986年斯珀波(D. Sperber) 和威尔逊(D. Wilson) 出版了《关联:交际与认知》[2]一书,标志着认知语境的诞生。不过,随后范·戴克超越了他们的研究。
范·戴克指出,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者完全忽视了社会和语言使用之间的中介问题,甚至忽视了知识在文本和谈话中的基本作用。为了解答情境如何影响话语这个问题,范·戴克巧妙地在情境与话语之间设置了一个中间环节——“认知语境”。他认为,认知语境“主观地表达了交际情境的相关方面, 同时也是一种能够监控话语产生和理解的认知结构”[3]。 另外,范·戴克指出斯珀波和威尔逊的理论是形式化和哲学化的,语境应当用“模式”更清晰地表征出来,因而他在借鉴早期学者对情境语境变量的基础上,将认知语境图式概括为以下类别:
第一,设置:时间/时期、空间/地点/环境。
第二,参与者(自我、他人):交际角色(参与结构); 社会角色类型、成员身份或身份;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权力、友谊);共享的和社会性的知识和信仰;意图和目标。
第三,交际其他行动/事件。
范·戴克认为话语主体正是通过这些语境图式策略性地组织话语结构和适应整个交际情境。他将语境模式定义为“在参与(社会、互动或交际)情景时,参与者对该情景相关属性的一种特定的心智模式或主观解读”。在每次交际事件中,语境模式都会起作用,然而由于交际情境的改变,以及话语主体记忆内容和语境模式处理情境信息的差异性,每个人的认知语境都具有主体性、主观性和独特性。范·戴克还吸收了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共有知识”观点,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术语“K装置”(K-device), “K装置”就是大脑中的知识处理机制,在交际行为的每一个瞬间,“K装置”都在计算说者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被听者所共享。
以范·戴克为代表的认知语境学者,其研究残留着“情境变量”的影子,例如范·戴克的语境图式是有明确类别的,但他们的研究又超越了简单的变量罗列,意识到了语境本身是认知的——语境是“机制的”“动态的”而非“要素的”“静态的”,并试图说清这种认知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2 认知语境研究遭遇的困境
语境研究从语言语境、情境语境发展到认知语境,在理论的深度和解释力上都有所发展。但是认知语境研究也面临深刻的挑战,其挑战既来自自身的“语境偏向”,又来自认知语境模型的严谨性、完整性、适用性及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2.1 认知语境研究本身基于一定的“语境偏向”,因而不是全面的、最终的真理
范·戴克等人的语境认知转向,受到当时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但从其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范·戴克前期从事批判话语分析,早已关注到话语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完成《意识形态和话语》这本书之后才出版了《话语和语境》。他自身的“认知语境”决定了其语境研究的意图、主旨和重要观点,比如他建构的“社会—话语”模型,其中鲜明表达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以及认知语境如何起到意识形态理解和生产的作用。从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看,范·戴克的认知语境研究为其前期批判话语分析和意识形态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范·戴克的语境研究本身不是语境研究的全部,它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服务的,而纵观他的后续研究,语境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还是应用于识别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偏见问题。进而言之,任何人的研究只能是探究真理全貌的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为止的所有语境研究的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带有范式特征和学者个人偏向的,这注定任何一个理论本身不是完美的,不是最终真理,其理论陷于困境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2.2 认知语境模型从其自身的严谨性、完整性、适用性、理论深度来说,面临着难以回应的挑战
范·戴克作为全球知名的话语分析大师,其认知语境模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成为其他学者建构认知语境模型的重要参考。国内学者魏屹东、薛平也曾在《论语言的认知语境与语境认知模型》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的一般认知模型,即逻辑认知模型、社会认知模型、心理认知模型,以及语境认知结构“叙事事件(言语的、行动的)→语境影响→内心体验→认知形成”[4]。可以说,为语境研究建构合适的模型,是诸多学者的执着追求。但考察诸多模型,发现它们无一不是有缺陷和漏洞的。
以范·戴克的语境模型为例,它面临4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难以回答“语境框架”这个老问题,语境模式的严谨性不够。“语境框架”这一概念首先是在人工智能语境建模中提出,用于批判无法确定语境边界或语境变量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说,范·戴克对功能主义语言学语境研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与话语的互动关系和中介问题上,他的语境模式甚至保留了语境分类,从而种下了无力回应“语境框架”的祸根。范·戴克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难题,他多次使用“推测”一词来回应自己为何如此设计语境模式,并简单提及“由于语境模式持续地控制着话语和互动,必须至少部分地在工作记忆中保持活跃,因此它们必须相对简单,并且只具有有限数量的类别和子类别”。很显然,他的回应是不严谨的。随着“具身认知”在认知科学中兴起,身体作为认知处理器,其语境功能越来越凸显,而之前的语境图式分类中并没有“身体”这一要素。可以说,语境分类思想或许无关对错,但是语境变量的具体内容却从来都受到质疑。
第二,难以回答语境类别的权重、层次、结构这些一般性问题,语境模式的完整性不够。范·戴克的语境模式罗列了语境图式的类别,并一再强调语境模式将情境信息分成不同类别加以处理,从而高效控制着话语的理解和生产。但是纵观范·戴克的语境理论,就像他说不清为何只有这几个语境图式一样,他同样说不清被他挑选出来的这些语境图式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否存在权重、层次和结构关系,他只简单提及“语言使用者自己主观地解释交际情境的每个维度,并分配不同的相关性”[5],把语境图式的关系问题推给了每一个语言使用者。也就是说语境模式作为一个模型、一种机制,范·戴克只讲模型和机制的要素及机制运行产生的现象,却未曾讲清楚它的结构和运行,这显示出其理论的完整性不够。
第三,难以回答语境竞争与转换这些现实问题,语境模式的适用性不够。范·戴克在其《意识形态与话语》一书中,用一页纸绘制了一个模型,它表征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群体对事件的态度影响个体的事件记忆模型,从而对认知语境产生影响,而意识形态化了的认知语境控制话语的理解与生产,再生产出意识形态。这个巨大的模型能有效解释交际活动中的个体如何受到特定群体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持有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但这个模型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同一群体中的不同个体有可能接触到多种意识形态,而多元意识形态存在的竞争关系,也有可能反映在个体的认知中。更有甚者,原来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个体,由于其独特经历而在接触到异质意识形态时,发生了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这都是有可能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但是,范·戴克的语境模式无法呈现这一竞争与转变的过程,故而这一模式的适用性仍然不够。
第四,难以回答语境研究的“意识”属性与语境图式本身的“潜意识”属性这一深层次问题,语境模式的理论深度不够。语境如果是认知的,那么它隐藏在人们的头脑中,既然是隐藏的,那么对语境的研究就面临方法论的困境,即第三人称视角如何理解第一人称视角?最常用的方法是推己及人,研究者假设自身与他人具有相似性。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研究者本人是如何知道自己的认知机制的?“我”如何知道自己如何思考的?康德将“自我”视为物自体,它是不可被认识的,但是“自我意识”是物自体呈现的现象,是可以被自我感受和认识的。所以,语境如果真是一种认知机制,它是“潜意识”的,不可被认知,人们所能认知的是自己对语境的感受和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语境研究,实质是对语境意识的研究,而非对语境本身的研究。这里的巨大鸿沟是一个深沉的哲学问题。当前语言学领域的语境研究,还不具有探测这一鸿沟的方法。
2.3 认知语境研究既缺乏哲学理论基础,也缺乏认知科学的模型和实证作为支撑,其理论后劲有限
语境研究的认知转向从一开始就缺少哲学内涵,这使得认知语境的后续研究偏重于应用,而在基础理论发展方面后劲不足。此外,学界公认语言是心智的功能,通过语言可以窥探心智,通过心智探奇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但是语言学在和认识科学的融通过程中,明显缺乏独立研究心智的科学方法,而只能被动等待认知科学及其他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增进和改变研究方法和视角。语境在语言学界的认知转向,虽然突破了原有语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语境研究新范式,但是语境的认知转向,也使得语境的基础研究依赖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和成果。
有意思的是,在认知科学中“语境”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现流行的意识模型,如CODAM模型(Corollary Discharge of Attention Movement)、整合信息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IIT)、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 Theory,GWT),只有“全局工作空间”理论里将语境视为意识产生的重要环节,但巴尔斯(Bernard Baars)的语境概念是神经生物学意义上的,即“语境是专门处理器组成的一个稳定结合体”[6]。在人工智能领域,语境主要适用于建模,其使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目标导向的表征和自然语言的处理”“语义网络系统”“隐马尔科夫模型”[7]。但人工智能领域的语境建模,虽然可以帮助理解人类认知,但不能取代对人类认知进行直接研究。在国内,以山西大学郭贵春为首的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语境,在魏屹东、殷杰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语境论被发展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即语境主义世界观。但是从这几位学者的研究现状来看,针对语境的基础理论研究越来越少,而应用性研究、西方认知科学的跟进研究越来越多。这也表明语境研究不能脱离认知科学的发展,但认知科学的研究却并非一定要保留“语境”的概念,语境研究一旦得不到认知科学的支撑便难以推进。这也就是自范·戴克之后,认知语境研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
3 语境研究的出路
陷入困境的语境研究需寻找出路。当前,语境研究的出路有二:其一,继续深化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以此推进认知语境的研究;其二,变革语境研究的范式。需转变语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再将语境视为“语言的”“情境的”或“认知的”,而是将语境视为其他。
事实上,不论语境是“语言的”“情境的”还是“认知的”,都被视为语言的“解释框架”,语境是围绕语言的解释结构。语言与语境的关系,是“核心事件”与“支撑事件”、“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但是,可以提出一个看待语境视角的新观点:语境即“话语生态”,是一切话语存在的状态、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与支撑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语境研究的主旨是为多元话语创设合理的“话语生态”,以使不同话语主体能在其中自主、平等、自由地进行“对话”。从语境的“解释框架”范式到“话语生态”范式,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3.1 在研究内容上
“解释框架”视角下的语境研究致力于解释已存在的话语,而“话语生态”视角下的语境研究致力于研究话语为何存在及如何使多元话语存在。“解释框架”作为一种事后解释,是在话语已经产生之后,由“我”来找寻支撑理解此话语的信息,以期达到理解的目的。而学者们对语境的研究,往往是从建构的语境概念/模型/图式出发,或对话语的意义加以诠释,或挖掘其中目的、意图、意识形态倾向,或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搭建不同学科对话的平台。
“话语生态”视角与这种事后解释不同。“我”思考的是对方为什么能说此话,该话语为何能在此时此地于我们的对话中存在,这一存在本身释放什么信号。而学者的研究,则拓展为此话语是否从属于更大的话语体系;它与其他话语/话语体系存在什么关系,使得该话语产生的言说场合/社会环境具有哪些原则、规范和特点;是否能从话语“被言说”的角度,抽象出话语存在的“生态原则”。也就是说,新的语境观使我们由追问话语“是什么”,到追问话语“如何存在”“为何存在”“这一存在释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更具反思性、元理论的问题,我们从事后的解释转向预设的存在,并试图反向建构能使话语在普遍规范下“被言说”的话语生态。
3.2 在理论基础上
语言语境研究主要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情境语境研究吸收了自然科学中的变量思想,研究范畴包括情景变量与话语之间的因果关系;认知语境的研究基础跨越了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话语分析、科技哲学等多个领域。然而,不同于以上,“话语生态”视角下的语境研究,应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
首先,“话语生态”视角下的语境研究,既非单纯的语言结构研究,也非纷繁复杂的认知机制研究,更没有雄心确立一种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事实上,“话语生态”的底层逻辑仍然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是交往的产物,也是实践的中介,而“言语”则是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实践活动。话语内在蕴含“语言+言语”,因而“话语”亦可视为“话语实践”。话语实践与其他实践一般,都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话语生态是由话语实践建构而成的话语网络,对任何即将产生的话语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它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话语权”问题。
其次,是以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为代表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批判话语分析,以揭示话语如何延续和使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平和压迫现象合法化为旨趣,希冀通过增强人们的语用意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的实现。费尔克拉夫提出的批判话语分析模式,包括社会问题分析、话语分析和社会变革三个阶段。该模式把社会问题作为批判话语分析的切入口和主线,以话语分析为核心,将话语实践作为话语与社会的接口。在具体分析方法上,费尔克拉夫提出了话语分析的三维度: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8]。这一分析框架为研究话语生态的具体途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最后,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交往行为为载体,与“系统”世界的物质性、目的性和技术性相区别。交往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借助语言或其他符号媒介,通过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对话,达到的相互理解、获得共识的行为”[9]。交往行为有效性的要求是:命题或预设的命题具有真实性;合法调节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当性;主观经历表达具有真诚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及其交往行为有效性原则,为建构良好“话语生态”提供了思想资源。
3.3 在研究方法上
“解释框架”视角下的语境研究,主要采用语境建模法,将语境对主体的影响视为语境结构与主体之间的拓扑关系,其关键环节在于语境结构如何构成,以及这些结构化的要素如何在程度上和顺序上与主体产生关联[10]。而“话语生态”视角下的语境研究,则主要采用的是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语境被视为话语产生、发展、灭亡的生态系统,研究的是话语自身的状态、话语间的关系,以及话语与支撑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语境被视为任何话语产生的客观先在,而这一客观存在,本质是由人类交往建构的,因而人类能够能动地干预语境的创建,其宗旨不在于研究某一具体话语的意义,而在于如何建构话语生态以协调话语间的关系,为多元话语的产生提供良好的“抱持环境”。
例如,在心理咨询事件中,来访者向咨询师诉说了一段他未曾向其他人透露的个人经历。针对这一事件,首先要考察的是这段经历是如何被诉说的,诸如它是被以怎样的风格,怎样的情绪状态诉说的,描述是否完整有序,是否存在异于平常的叙述视角、言说方式等;其次要考察的是这段经历为何能在此时进入对话过程,它与其他话语处在一种怎样的衔接或断裂的关系中,其他话语为其登场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它背后隐性存在的话语关系是什么,该话语是否在为更为深层次的对话做准备等;最后要考察的是这段经历为何只能在心理咨询室里才能被提及,心理咨询室这一场所预设的环境特征有哪些,这些预设特征为该话语产生创造了哪些原则和规范等。
以上这些考察内容,不论是“听者”还是“研究者”都同样适用,这些反思不仅能帮助理解“说者”说了什么,还能帮助理解他这样说的深层次原因,有时甚至是潜意识动力,从而更好地做出回应,能动性地改善局部话语生态,增强“对话”的有效性。而作为研究者,其任务尚未结束,研究者要从该心理咨询语境中跳脱出来,横向比较它与其他情境中的“对话”存在哪些话语生态的共性和特性,哪些共性能支持主体在不同语境中自主、平等、自由地言说,这些共性的原则和规范是否能在普遍的交往中推广。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话语生态视角下的语境研究,其旨趣是指向社会交往的,它以建构交往行为、交往理性为目标。
总之,与“解释框架”视角下的语境研究不同,当语境被视为“话语生态”时,研究不再纠结于“情境如何影响话语”或“认知机制”这些问题,而是将话语放置在其存在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这是一种需要练习、刻意为之的分析行为,是能在对话中即时使用的策略,并能帮助研究者发现对话中隐藏的原则和规范,从交往理性出发建构合理的对话机制。
4 结束语
不论是语言语境、情境语境、认知语境,都是在为理解语言寻找“解释框架”。语境研究出路有二:其一,继续深化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推进认知语境研究;其二,变革语境研究的范式,将语境视为“话语生态”,可以为语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在这一新范式下,语境研究的主旨是为多元话语创设合理的“话语生态”,以使不同话语主体在其中自主、平等、自由地进行“对话”。这一新的语境观,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三维度、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为思想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做了相应创新。总而言之,“语境”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语言学语境研究的三重进路及正面临的困境,需要融合多学科视角,创新研究思路,突破原有范式,建构新的语境研究共识。
参考文献
[1] 周淑萍.语境研究:传统与创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5.
[2] SPERBER D,D.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 nition[M].Oxford:Blackwell,1995.
[3] 王璐,殷杰.范戴伊克的语境论思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31(1):34-39.
[4] 魏屹东,薛平.论语言的认知语境与语境认知模型[J].哲学动态,2010(6):52-56.
[5] 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24,220,223.
[6] 伯纳德·巴尔斯.意识的认知理论[M].安晖,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26.
[7] 魏屹东.语境与人工智能[J].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1):43-52.
[8]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8.
[9] 王凤才.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出发[J].外国哲学研究,2024(1):118-130.
[10]殷杰.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研究纲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