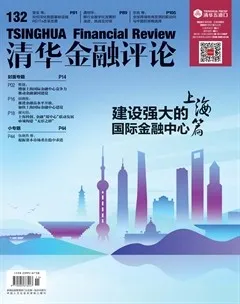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我国产业蓝图
2024-12-10方奕郭胤含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载体和表现形式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中呈现的高级形态,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新动能。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载体,科技创新需要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相辅相成,一方面,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亦要求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涵盖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涵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以及未来产业的培育,这也为我国产业体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注入新动能,是能够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具活力的革命性力量。
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产业区位布局
遵循规律,尊重差异,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一重要论断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遵循。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强劲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建设需要实现的是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新模式的快速涌现,这依赖于人才储备、产业资金和科研成果转化等。“因地制宜”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强调了在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区不可套用一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人才聚集、经济基础、自然禀赋、创新资源和产业基础等不同情况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的发展,实现各区域发展的差异化定位,优化资源配置。
“因地制宜”既是尊重差异性实现产业分工,更是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在各区域实现产业分工,发挥特色科技创新功能的同时,区域间和产业间的科技合作和产业融合也将形成,这是创新链条各环节差异化区位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结果。不同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更是为了实现全国区域发展的“一盘棋”,在区域间融合互动中拉长自身长板,协同推进地区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跨区域融合和错位竞争,从而在全国层面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更好适应83c74720c939d442aa18ccf8acfd64dd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通过新质生产力产业布局,可实现创新城市重要突破、核心经济圈全面布局、中西部地区特色发展。结合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词频,以及卢江等(2024)的测算,当前全国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且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内部的层次分化十分明显,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等东部地区经济腹地以及交通要冲区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正稳步抬升,且已接近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山西、黑龙江和吉林省作为传统的资源型工业区和老工业区,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明显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份。而从整个的西部地区看,整体水平虽相对落后但整体保持积极态势,省份间分化并不明显。往后看,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笔者预计将呈现出创新城市重要突破、核心经济圈全面布局以及中西部地区特色发展的产业布局。从当前各省市的产业布局以及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新质生产力的表述上,创新城市正在实现尖端产业领域的突破,北京主要聚焦在数据要素、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技术,上海主要布局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广东则主要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方向。而从核心经济圈上,则更多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这些重点区域更具备创新要素聚集、人才资源富集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优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圈上更容易形成多级点支撑、多层次联动以及网络化发展的格局,核心经济圈将有望成为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以及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主要承载地。而对目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欠缺的中西部而言,更适宜根据自身的创新资源禀赋以及产业基础发展更具特色的产业方向,同时聚焦细分赛道发力,着力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如陕西依托自身产业基础进一步强化其在航空航天以及新材料等领域的优势,兰州依托自身的原料资源优势、风电绿色资源发展降低生产成本的资源优势,以及“一带一路”枢纽节点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
“三大产业”科学布局——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驱动,是由生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而催生,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海外对中国的科技制裁层层加码,全球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正在加速重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构筑产业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也是顺应当前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纵观工业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浪潮,新兴产业均是率先进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先导产业,当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赛道新领域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效应强,能够及时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正是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主要产业。从产业发展逻辑来看,两者核心区别在于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新兴产业主要是指已具备了较大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和较强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关键性支撑与引领作用的产业。而未来产业则更加前瞻,主要以颠覆性创新为特征,有望在未来实现产业转化,并可能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作用。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未来产业发展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经的发展阶段,两者均具备创新风险性、技术前沿性和发展战略性的产业特征。
“传统”与“新兴”并非割裂,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的“新”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而非只涵盖新兴产业。从海外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国家经济转型,培育新兴经济增长动能的过程中均重视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加快过剩老旧产能出清的同时,对传统产能进行节能化以及效率化的改造。当前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占比超过80%,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底座,也是我国能够保持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的基本盘。看似“旧”的传统产业实际上正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依托。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为传统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高端化重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这是促进制造业补短板、锻长链的关键所在,将增强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体系的协调性,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智能化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实现“中国智造”的基础。而绿色化则强调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树立传统产业“绿色标杆”。
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助力我国产业加速发展
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金融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血脉,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十分关键。但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仍存在着不匹配。一方面,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特征的融资需求不匹配。银行信贷对于投资风险的容忍度较低,新兴产业发展具备轻资产属性,难以提供银行信贷所依赖的传统抵押品,如土地等。同时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也难以准确衡量科技创新企业的价值和风险。银行对企业风险的判断主要依赖企业的信用记录和财务数据等,对于高技术产业的专利、商誉等价值缺乏科学评估机制,这导致了新兴产业信贷可获得性较差,难以获得充足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上仍显不足。从投融资形式上看,风险投资更适合新兴产业高风险的特征。但我国创业投资市场起步较晚,市场深度和广度仍须提升。同时资本市场的产业资本和耐心资本的供给并不充足,资本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难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支持。
建立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实现金融赋能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金融体系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以及风险配置中的作用,以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在直接融资方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其一是进一步深化科创板改革。已出台的“科创板八条”从上市机制、企业发展以及投资者保护切入,深耕科创板“试验田”,后续发行承销、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以及交易等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二是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完善投资退出机制,如优化并购重组政策,畅通IPO渠道,形成从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融资支持体系。此外,也应积极发展科技创新债券、绿色债券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在间接融资方面,银行业应加快转变传统信贷模式。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建立专门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将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市场前景等纳入评估指标,提高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风险容忍度。另一方面,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发挥引导作用,可以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基金、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等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此外,银行业应积极推动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投保联动模式,将信贷、保险和投资有机结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支持。
(方奕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郭胤含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策略分析师。责任编辑/王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