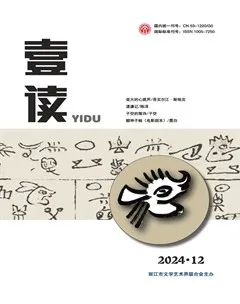清欢
2024-12-10李晴虹
盛夏灼热的阳光里,坡地上一大片一大片洋芋长得壮硕茂盛,墨绿的叶片挨挨挤挤,紫色的花朵恰似一顶顶王冠。母亲看得满心欢喜。花谢后,枝枝蔓蔓便挂上了珠子似的绿果。山地洋芋在夏天成熟,地上的茎杆开始衰枯。这时候母亲和乡亲们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匆匆吃过早饭上山刨洋芋去了。
他们会在山上忙碌一整天,到天黑才挑着满满两筐洋芋结伴回家来。我们村的山地离家十多公里,山道崎岖,道路狭窄,布满石块,极不好走。筐里的洋芋越走越沉,男的力气大一边走还能一边吹牛调侃。女的却要歇很多回气,慢慢落在了后面。极少数人家的条件好,有马匹或小毛驴,驮着几袋洋芋“得得得”从后面走来,很快就轻松地超了过去。这样的人家走过,总是引人注目,让人羡慕。
我七八岁的时候——也许更早,记不大清了——傍晚时就跟着族里大些的孩子,背一只小背篓去迎大人。农村的孩子很能干,稍大些的孩子背的篓也大,有的手里还要再加一只提篓。我们常常要走六七里路,直到大坡沟才能遇到大人。小伙伴们在队伍里找自己的爹妈。一个大妈看到我,告诉我:“你妈还在后面。”我就朝后面去找。很多人家都是爹妈一起上山劳动,我家却是母亲一人,父亲在城里读书。恢复高考后,父亲考上了曲靖师专,毕业后在城里学校教书,只有周末才能回来。
我找到母亲的时候,看到她被沉甸甸的担子压得更瘦小了。她两只筐里的洋芋堆得尖冲冲的。我有种错觉,觉得母亲看到我的时候要哭了。母亲歇下担子,把她筐里的洋芋往我背篓里装,装好又帮我把背篓凑近让我背上,我明显地感到了沉重,但我还是让母亲再给我加得满满的。母亲太累了,她于是又给我加了些。我含着胸,走在母亲身边,感觉到她的欣慰。月光明亮地照着苍茫的大山,长长的队伍,精神足的人还在开着玩笑。人们担着丰收的喜悦,快乐地朝家走去。下坡的山路和重力,使人们步伐齐整而仓促,“嘿哧嘿”(一二一),“嘿哧嘿”(一二一)。在寂静的月色里,显得悲壮和苍凉。村子还在远处,人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和目标迈进,走在生活的深处,不曾被命运压跨。有一个大爹在队伍里夸我,说:“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小三说晴虹又是全班第一名。这娃争气呐!”小三是我的老师。我害羞不言语,母亲很高兴,我们走路都觉得轻快了许多。
饿肚子的记忆于父亲那辈人刻骨铭心。大集体劳动时,三伏天大家出工挖田,晒得冒汗,人也软塌塌的。这时如果有人说:“我回家去泡壶糖水来大家喝。”不管多累,大家都欢喜地应着,心甘情愿连同他的那份田也一并挖了。父亲常爱讲一个村里的笑话,说村里有一个光棍汉叫来福,好吃懒做,人们逗他:“来福,要粑粑吗?”
来福饿得有气无力,说:“掰半个来嘛。”
旁人接着问:“来福,要洋芋吗?”
来福说:“掰半个来嘛。”
“来福,要屁吗?”
来福还是说:“掰半个来嘛。”
哈哈哈!人们笑成一片,笑得浑身力气都添足了三分。来福也不恼,甚至有些半推半就半配合。他知道,如果他有个万一,最终冲上来帮他的,还是这些人。岁月艰难,并无恶意的戏谑,是乡亲们苦中作乐的刚强。
那时候,母亲已怀了我。数米而炊的日子,饭煮熟时,父亲总先舀出一碗给母亲,然后“哗”地倒一笸箩菜到锅里,剩下的米饭粒粒可数。有一回,家里实在没啥吃的,父亲想去姨爹家碰碰运气,不巧姨爹家已吃过饭了,他们并不问父亲吃饭没有,连虚情假意地客气一声都没有,却让父亲跟他们一起去挖田。
父亲还常说起初中一个男生,跟别人打赌一顿饭能吃一斤,吃起来果然如风卷残云,惊呆众人。侄儿小时不懂事,听完闷闷地说:“怪不得那时穷,都是吃穷的。”父亲纠正道:“是穷了饿了才吃得的,肚里没有一点点油水。”看到侄儿挑食,父亲叹道:“我年轻时要有这么些好吃的,还不够我一个人吃!”
我在许多作品里读到过关于饥饿的描写。路遥的《在艰难的岁月里——一九六一年纪事》,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了建强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唯一的高中,饥肠辘辘,贫困潦倒,“每当下午自习时,饿得头晕目眩,忍不住咽着口水。”“饿得连路都走不利索。”受到同学们许多奚落和嘲笑,甚至被当作“做贼心虚的小偷”,“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对我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下午吃过晚饭(我只买一碗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常饿得人心火缭乱。”“我想站起来,但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胃囊在痛苦地痉挛着,饥饿像无数利爪在揪扯着……”故事最终是温暖的,但煎熬却太心酸。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写到了异常的饥馑。白孝文的媳妇“通身已经黄肿发亮,隐隐能看见皮下充溢着的清亮的水,腿上和胳膊上用指头一按就陷下一个坑凹,老半天弹不起来”,她最终也饿死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饥荒里同样死了许多人。家家烙白土饼充饥。“孙克贤的肚皮叫白土烙饼撑成了一面鼓,硬硬的,一碰就碰出鼓点子。公社卫生所的卫生员用肥皂水给他灌肠。灌了肠在他肚子上捺、挤。孙克贤成了叫驴,叫得地动天惊。叫了一个多小时,他死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年的河南旱灾,灾民3000万,饿死300万,触目惊心,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也有残酷的饥饿。萧红也是经过饿的,她孤独困在旅馆里,饥寒交迫,“桌子能吃吗?椅子能吃吗?柜子能吃吗?”后来看电影《黄金时代》,汤唯为了演出萧红饥饿窘迫的状态,忍着不吃饭,穿着单鞋和薄棉衣在户外受冻,被称为“自虐表演法”。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仅活了31岁。她在《王阿嫂的死》中借妇人的口形容王阿嫂的悲苦:“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
幸得有土豆。我们习惯称洋芋。
父亲常说,每年到刨洋芋的季节,人都能胖几斤,因为能坦坦地吃一阵饱。不用米饭,光吃洋芋就很好。
劳力强的人家,收获的洋芋小山似的堆了一满楼板,足有两吨。我们家也有六七百斤。这些洋芋,全靠母亲肩挑手提淘回来。她粗糙的手掌上,布满老茧。老茧还长在脚上、肩上。一根扁担磨得溜滑锃亮。从来没有听母亲抱怨过。那条乱石林立、荆棘遍布的山路,母亲来来回回走了多少遍,她用脚步丈量岁月,走成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有一次背着洋芋,下坡路滑,石头一滚,我摔了一跤,手掌蹭破了皮,洋芋摔撒了很多。母亲放下担子,拉着我的手轻轻吹,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我却笑了,一个劲地安慰着她,找着地上散落的洋芋。
春天的时候,我跟母亲去山上排过洋芋。先要挖地,挖地很费力气,通常要挖几天。我想帮母亲,不一会儿,手上就起了水泡,亮光光的。不理它,过一阵水泡就磨成了血泡。血泡破了,疼得“咝咝”吸气,疼得使不上力气。山地贫瘠,石头多,有时一锄下去,挖在石头上,“铛”地一声闪出火星。母亲会心疼锄头好一阵子。大多时候,母亲是在挖好地后,才带我上山。她在前面理沟,我把发酵好的粪草和化肥按比例捧放在沟里,隔一段距离放上一块洋芋种。母亲用锄头抓上土把洋芋种盖住。洋芋种是在家切好的,一个洋芋切成两块,每一块上都得有芽眼。春天风很大,有时放在地边的谷箩都会被吹跑,我和母亲赶着去撵,有时感觉自己也要被风吹跑了。午间的时候,吃两块早上在家里烙好的麦面粑粑,喝几口军用水壶里的水。大山很静,听得见松涛呼啸。我有时候会觉得害怕,想起那些买卖人体器官挖人心肝的传闻。风才吹干身上的汗水,就又得赶紧劳动了,要赶在天黑前种完面前的地。忙一天下来,觉得腰都要断了。
山地洋芋种上,就全靠老天照管了。没有水浇灌,也不会再来追肥。洋芋种在土里睡足了觉,几场雨后,便蓬勃生长。它们吸纳天地日月精华,经光合作用,变出一大个一大个滚圆的洋芋,埋在地下,不用担心鸟雀偷食,也不会有野兽毁坏。季节到了,人们来刨,从植株旁边一锄挖下去,一翻,一拉,一大簇洋芋缀满根须,大的像箩筛,小的如铃铛,更多的如拳头,白白胖胖,浑圆饱满。
人们通常把洋芋切丝炒,新洋芋脆爽,油放得不多,要加些水,有稠稠的汁,拌饭很好吃。或者配茄子炒。普遍的做法是酸菜烧洋芋汤,酸菜黄爽爽的,家家每年都要腌几缸,酸味纯正,开胃得很。小一些的洋芋就用来焖饭,不用切,圆溜溜的,粉都包在洋芋里没有流失,焖熟后洋芋面嘟嘟、沙噜噜的,吃两碗都不够。煮饭前,不管去哪家,女孩子仿佛都在刮洋芋,手指灵巧,动作利落,脸上还溅着点点白浆。刮洋芋前淘净泥,刮下的皮连同水舍不得倒掉,煮熟喂给猪吃。刮子多半是块碎碗片,锋利直截。有一次,我刮着刮着,就瞌睡起来,一不小心就把指头刮出血来。更严重的一回,我在砧板上切洋芋,人小,不会正确使用菜刀,切着切着,一刀下去,竟把左手小指头尖的肉圆溜溜地切下一块,几乎就断了,只粘住一丁点,鲜红的血霎时涌冒出来。我一人在家,那时没有创可贴,瞬间的反应就是立即把肉合上,用左手大拇指摁住,右手从药抽屉里翻找出一颗土霉素擂成末敷在伤口上,又从妈的针线篮里扯块碎布,缠在指头上,挣一根线,一端用牙咬着,另一端用右手哗哗缠绕,最后将两端捆扎起来。农村孩子不娇贵,做完这些,翘着小指头照样继续做事。过了几天再看,布上还是留着血印子。我不是疤痕皮肤,但直到现在,还看得见左手小指顶有一圈圆圆的接头,像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伤口太深。
洋芋堆在一起,中间不透气,少量的便开始沤烂。堂姐说,她最爱吃快烂的洋芋,吃得出甜味。烂洋芋剁碎了喂猪,不烂的半边煮了人吃。洋芋太多,一时吃不完,就做洋芋片。把洗净刮好皮的洋芋切成片,在一个大盆里淘去粉,捞出,将一大锅清水煮沸,倒进洋芋,搅拌,煮到八成熟,捞出,一片片晒在大太阳底下的草席上。我去晒,母亲接着煮另一锅。我按母亲教的,把洋芋摆放得秩序井然,煞是好看。全部洋芋铺好,我就负责照看着晒,防止小狗小猫破坏捣蛋,连吃饭都会端着碗坐在席子附近。中途要再翻一个面。
盆里的洋芋粉厚厚地沉淀下来,篦去水,和洋芋片一起在太阳下暴晒。傍晚时,洋芋片和淀粉都干了,洋芋片缩小了一圈,收的时候“咵嚓”响,用袋子装好,可以成年吃。有时候我会怀疑,这是不是子弟土豆片最初的灵感。洋芋粉干了我们称为小粉,白生生的亮眼,炒肉、炸圆子放上一点,肉嫩不柴。熬粉吃是最奢侈的,晶莹透明,稠稠的能拉出丝,类似现在的藕粉,平时都舍不得吃。有一回我生病了,又吐又拉,母亲心疼地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小粉,母亲调了半碗来,坐在床边喂我。才吃了两口,我又吐了,吐得干干净净,一脸泪水。
时间放长的洋芋蔫蔫的,白嫩嫩地往外冒芽。掰掉芽,洋芋照样吃,刮开皮,里面是绿色的。按现在科学的说法,这样的洋芋有毒。父亲说,老辈子吃了那么多年代,不见有问题。或许人们早已有了抗体。过年时洋芋芽有一指长了。有一年,我城里的小叔又来我家玩,因为他在家也常吃半饱,来我们家至少可以吃洋芋。但他吃过饭就歪斜在门前的柴垛上,晒着太阳,昏昏沉沉睡了一下午,怪异地不理人,醒来后猛喝水。好多年后想起来,才惊觉那该是轻度中毒了。
父亲读师专的时候,有一个周末,几个同学跟他来家里玩。父亲炒了水煮洋芋片给他们吃。我放学回来,一个叔叔看见我,捻起一片洋芋对我说:“快来吃,太好吃了!”他问父亲,怎么会把洋芋炒得这么好吃。父亲笑,说:“洋芋怎么炒都好吃。”
母亲后来随父亲到城里,开一小店,卖早点、杂食。母亲勤劳能干,把洋芋做出花来,她煎洋芋粑粑,炸洋芋坨坨,碳烤洋芋,清水煮洋芋,老酱抹洋芋,粗盐蘸洋芋……人人爱吃。母亲又自创了凉拌洋芋丝卖,清水煮熟的洋芋丝放凉,拌上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盐、味精等调料,一角钱一小袋,买的人络绎不绝。我惊讶于他们的良好胃口。人不多时,我舀一碗坐在角落里吃,亦吃得津津有味。
电影《钢琴师》,改编自波兰犹太籍音乐家席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再现了二战期间纳粹铁蹄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和艰难求生的故事,梦魇般的经历在钢琴师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印迹。电影里有一句台词,钢琴师的妈妈哀伤地埋怨:Potato!Potato!I hate Potato!(土豆!土豆!我讨厌土豆!)生活艰难,没吃没喝,还要随时担心被枪杀。由此我看到全世界最饥饿的时候都靠洋芋续命。这部影片后来斩获多项大奖,饰演钢琴师的阿德里安·布罗迪更是藉此加冕奥斯卡史上最年轻影帝。
洋芋营养丰富而齐全,含有的维生素C(抗坏血酸)远远超过粮食作物,是接近全价的营养物质。体内缺乏维C很可怕。几百年前,长期在海上航行的人,由于吃不到新鲜蔬菜水果,很多患有坏血病,身体极度疲乏,牙龈出血甚至腐烂。16到18世纪,坏血病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
大约8000年前,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就开始种植洋芋,直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洋芋被当成胜利品,搭乘西班牙的船队,走向欧洲,费尽波折,才使土豆为宫廷接受,并最终广泛种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洋芋拯救了世界上数以百万计人的命。据资料记载:洋芋的传播,在1700年至1900年间,至少引起了旧大陆四分之一的人口增长。在1845年到1848年间一场“晚疫病”袭击了欧洲洋芋种植业,爱尔兰至少有100万人因此死亡,超过200万人出逃。一枚小小的洋芋,成了生命坚强的捍卫。据说洋芋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
短短几十年,中国让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摆脱温饱困扰,创造了世界奇迹。尽管生活好了,但母亲对洋芋情有独钟,我们也对洋芋爱不释手。母亲还是会用洋芋焖火腿,煮洋芋鸡,洋芋炖牛肉……十个人站出来,九个是洋芋宝。带几岁的小孩出去外面餐馆吃饭,只要炸盘没有辣椒的椒盐洋芋,他可以吃得很乖。吃洋芋,长子弟。人们戏称洋芋是乡下的鲍鱼。丈夫说:“三天不吃洋芋,浑身没有力气。”苏东坡发明了东坡肉,是个美食家,可他生活的时代没有辣椒,没有洋芋,现在想来,还是差一味。网络小说《庆余年》中,穿越到古代的范闲带着大家飞雪的夜晚在府中吃涮火锅,春暖花开时去郊野烧烤。没有洋芋的火锅、烧烤,多么寂寞。
奶奶八十多岁时,全口只剩三颗牙。老奶洋芋便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母亲把煮熟的洋芋撕皮,剁碎,油欢,下入辣椒面、葱花,一并爆香,再下入洋芋末,撒盐,炒匀,出锅时加少许味精,佐料不复杂,清爽可口,最可奶奶的心。奶奶慈眉善目,儿孝子贤,九十二岁离世。
五年前,我搬新家,新房子冷凉,父亲感冒了。面对满桌好菜,父亲坚持只要一碗酸菜洋芋汤,酸菜须是母亲自己腌的,黄爽爽,酸味纯正。酸菜洋芋汤上桌,风华立时盖过帝王蟹,成为最硬抢手菜,还剩半碗,表兄抬起来就往自己碗里倒,侄女着急道:留点给我。引得一桌人爆笑,撑着额头的父亲都看笑了。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喜欢母亲焖的洋芋饭,色泽金黄,有微微的锅巴,香喷喷,面乎乎。喜欢母亲煎的干锅洋芋丝,切出来的丝,细得丝丝缕缕,慢火焙出生活的芬芳。人间至味有清欢,想着母亲做的可口饭菜,满心都是暧意。
我家乡的洋芋,宽厚内敛,朴实无华,它在黑暗的土地下生长,历经日月洗练与岁月磋磨,顽强的生命孕育着最柔软的内核,显示出低调的丰盈,多像父辈虔诚于命运又沉默抗争的禀性。当我展开双手,我不能说,哪个洋芋长成了我的一道骨节,哪个洋芋合成了我的一片指甲,但我知道,洋芋与我,不可分割,我吃洋芋长大,天长日久,洋芋以其细腻绵密的内质,生我肤发,长我筋骨,包括洋芋在内一蔬一菜的滋养,和着血脉亲情,使我面色红润,肌肤紧实,健康茁壮,幸福绵长。
这些年,去过许多地方,尝过许多名吃,可每次从远方回来,最怀念还是母亲做的酸菜洋芋汤。一碗酸菜洋芋汤下肚,酸酸辣辣,汤汤水水,酣畅淋漓,打开每一个毛孔,这顿饭仿佛才圆满。这是儿时的滋味,蕴藉着故乡的气息和父母的恩情,引领着我回家的路。
责任编辑: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