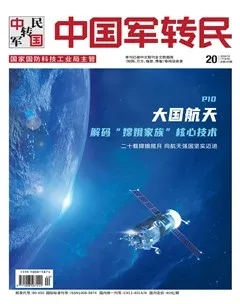商业航天背后的另一场技术赛跑
2024-12-06陈彬
2023年,中国发射了67枚火箭,居全球第二。有意思的是,其中属于“国家队”的火箭为47枚——这意味着来自民营企业的火箭,已经占据中国火箭发射的三成,发射次数比第三名的俄罗斯还多。
2023年被科技界视为中国大模型发展的元年,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年同样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元年。例如来自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就曾两度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仅在12月,“民间队”就发射了3枚火箭,完成了至少2次火箭试验、3次试车。年底,国内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也在海南落成。
在时间进入2024年后,“民间队”进一步加快了脚步。年初,蓝箭航天推出了可回收火箭朱雀三号,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完成了首次点火试验。9月11日,朱雀三号VTVL-1可重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试验箭,又进一步成功完成了十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
众所周知,在商业航天的舞台上,美国的SpaceX长期是唯一的玩家。星舰每次点火,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引来一片欢呼。然而,随着蓝箭航天等中国“航天新势力”坐上牌桌,这场以经济体为单位的太空产业竞赛正出现新的变数。
发动机的竞赛
国内商业航天如火如荼的同时,SpaceX也一点没有停下。到今年7月,SpaceX在2024年发射了足足68次猎鹰9号火箭,平均不到3天点一次火,将火箭发射做得跟飞机起飞一样平常。直到第69次发射出现了故障,导致搭载的20颗星链卫星全部损毁,这台“劳模火箭”才被迫“休假”了一段时间。
“火箭航班化”的背后,来源于SpaceX成熟的火箭可回收技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火箭都是“一次性用品”。但在马斯克看来,丢掉用过的火箭,约等于每次飞行后扔掉一架波音747,成本昂贵且效率低下,因此SpaceX一直致力于相关研究。
实现火箭可回收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发动机。推进系统一直是火箭硬件成本最高的一环:一级发动机占了一级火箭硬件成本的54.3%;而在二级火箭中,发动机占比也有28.6%。过去的“老古董”火箭,基本都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研制难度小但几乎没办法回收,每次发射都是放烟花。因此,如今的火箭几乎普遍改用液体燃料发动机,但在燃料的选择上却有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例如猎鹰9号所使用的技术方案是“液氧+液氢”,优点是动力足、可重复使用次数多,但成本相对较高,且在燃料稳定性、使用安全性上存在一定隐患。而最新的技术路线是“液氧+甲烷”——可多次重复使用的同时,解决了前者高成本、不稳定的缺陷,被业界普遍视为下一代液体燃料的主流选择。目前,押注“液氧甲烷”路线的既有SpaceX的星舰,也有国内玩家。
去年7月,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遥二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成为世界上首款成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的液氧甲烷火箭。不久前完成试验的朱雀三号,也搭载了液氧甲烷发动机。几乎同期,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星际荣耀”)在去年年底将传统的固体运载火箭升级为液氧甲烷路线,其“双曲线二号”液氧甲烷可重复使用验证火箭首飞及复飞试验任务均取得成功。到了今年年中,九州云箭(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九州云箭”)龙云液氧甲烷发动机也在酒泉东风发射场完成10km级“飞行-回收”试验。
在以经济体为单位的科技产业赛跑中,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正在给航天领域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技术创新。然而,新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商业航天等科技领域的竞争,比拼的并非只是技术。从研发新技术到落地量产的过程中,实际需要规模庞大的资金支持。
科技领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基础研究、开发中试、工业生产这三个环节,所需的资金配比是1:10:100。也就是说,企业每进一步,都需要花费10倍于前一阶段的资金。这意味着对资源有限的民营企业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试错空间;一旦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前期的所有付出都可能前功尽弃。
事实上,即便是今天无限风光的SpaceX,也曾因资金问题,一只脚踏入过鬼门关。2008年时,由于猎鹰1号火箭前三次发射都以失败告终,SpaceX融资出现问题,马斯克一度得靠借钱来发工资。直到第四次发射成功,说服NASA拿到订单后,SpaceX的现金流才开始好转。
对仍处在野蛮生长期的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来说,其面临的挑战,其实并不比当年的SpaceX轻松。但好消息是,它们不必独自面对。
技术与金融
在科技改变人类社会的壮阔叙事背后,往往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两者实际互生共荣。今年以来,商业航天领域融资动作不断,深蓝航天、星际荣耀、东方空间(山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空间”)等多家企业宣布获得最新一轮的股权融资,通过引入外部资本,加速火箭技术研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一级市场融资总额达103.6亿元。目前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增加。
然而以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对于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正如前文提到,商业航天领域拥有诸多特点:一是高投入,充足的资金支持是确保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二是长周期,单以一个发动机的研制时长,就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从试验成功到商业化试运营、最终实现盈利,产业都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产业+金融”三者正在深度融合。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理应也应当扮演重要角色。
在过去十多年间,参与诸多高科技领域的爬坡与升级过程的主体,其实是外界想象中与高科技绝缘的“传统金融机构”。在面板、光伏、存储芯片等多个领域,都能看见产业政策与商业银行的推动力。
在面板这类面临巨大资本开支和残酷价格周期的行业,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神秘力量”始终贯穿其间。然而,民营商业航天的兴起又给银行传统的评审模型带来了新的挑战。抵押贷款由于业务规范程度高、具备确凿的风险兜底措施,是银行业的主要贷款品种。以前述面板、光伏产业而言,固然是高科技,但对银行来说,厂房、设备和制成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抵押物,并没脱离一以贯之的风险定价逻辑。
但商业航天企业的特点是“两高一轻”,即高研发投入、高人力成本、轻资产。其核心资产是学术论文、专利成果等,一直难以用传统方式定价。围绕火箭发射升空场景,面向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授信产品服务,以及与之对应的一系列内部组织与治理改革,也在时刻倒逼着商业银行。
据了解,在蓝箭航天的成长过程中,招商银行在其扩充产能的关键阶段,高效批复了数千万元综合授信,缓解了资金缺口。同时,招银国际领投了蓝箭航天的D轮融资,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本力量。
来自招商银行的支持,是当下国内科技金融发展如火如荼的缩影。相较于过往侧重于技术的成熟度及其商业价值和实现路径,银行当前愈发重视企业的原创研发能力,也承受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止是金融
众所周知,一项新技术的壮大往往离不开下游应用场景的爆发。尤其对高研发、高投入的硬科技产业来说,早期的订单可以转换为更多的研发资金,从而加速技术的成熟。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任天堂、雅达利游戏机的热卖,曾给萌芽中的半导体产业提供了第一桶金,并推动了集成电路的进化。
如何把专利与论文变成实实在在的商业应用,是任何新兴产业都要攻克的难关。
当前大规模卫星组网发射需求井喷,带动了火箭“热”。像蓝箭航天这类以液体发动机为研制方向的企业,简单而言,商业逻辑就是通过研发可回收火箭,以重复利用提升发射频率、减少研制成本,进而降低整体发射价格、提升行业竞争力,获得更多的商业发射订单。而当发射运力、价格不再是行业发展掣肘,正如一份专业研究报告所言,“当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低成本运载系统后,将激发更多的空间基础设施需求,航天发展将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商业航天不仅将带动火箭发射、卫星制造、卫星通信、卫星导航以及卫星遥感应用等,还将对其他行业赋能,带来更广阔的增量市场空间。比如,火箭发射拥有太空货运、太空旅游的商业想象;高精度卫星导航将支撑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卫星通信技术可以在网络容灾的场景中实现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助力智慧信贷建设等等。
以“商业航天+银行”为出发点,想象空间可以无限广阔。商业航天中的卫星数据可以运用到经济预测、实时监测、事件追踪、风险预警等多个场景。以遥感卫星为例,其技术原理是利用遥感技术收集地球表面的信息。当下,民用遥感卫星的分辨率已经可以达到0.5米,这意味着只要是尺寸大于0.5米的事物,都可以被卫星图像记录下来。
新兴产业的成长在于下游是否有可以转化为实际订单的真实需求,从这个层面看,商业银行不仅仅是新技术的“投资者”,也是“支付者”。
如今,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对“硬科技”与“金融”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但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例如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第一的这十年间,金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当下刚刚兴起的民营商业航天,也是如此。企业由小变大,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浇灌和呵护。
众所周知,企业成长发展的资本投入有着“微笑曲线”的存在,初创及成长期的企业需要沉默资本的投入,以及耐心资本的陪跑;在步入产业化进程相对成熟的阶段后,再由商业银行、资本市场通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这样在各方合力下,围绕科技企业,方可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性、接力式的金融服务生态。
推崇科技固然是件好事,但同样,我们也要正视产业发展的规律,给每一位发光发热的角色以合适的评价。激发“科技+产业+金融”的澎湃动能,中国航天才能走向更深更远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