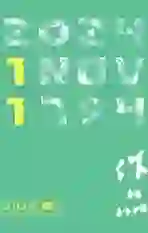艺术触觉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疯长(评论)
2024-12-03张燕玲
读完这六篇(编者注:实际刊发五篇)习作,顾骨在我眼里便成为一位天真而感伤的青年写作者。我探究如此年轻的他,为何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书写一重重幽微的存在,那些充满南方生机和语感的弃儿生活,以及缺失爱和生存的艰难,令人想起高尔基《在人间》的故事,总有一抹挥之不去的忧伤?他的意绪缠绕而灰色,哪怕明朗一些的题材也以感伤作结,甚至虽不明写,那份残酷青春的惘然、对世事愤懑而漠然的感伤却又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只有心向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人事,以及向往未来,才有一束穿越雾霾的微光,虚无而现实,灰暗而依稀,异质的文字散发出缕缕的人间光亮。
是的,年轻顾骨的作品是以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去书写自己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现实里不为人知群体的人生。虽然作者的独语诉说沉浸于形而下的主观情绪,使得小说缺乏生活细节、人物形象,因为生活实感不等于小说叙事,但作者颇具陌生化的个性写作,可圈可点。比如他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好坏,还时时把人物主次的界限模糊,有着在垃圾堆里做道场的努力,显示了顾骨不俗的文学潜力。
六篇小说的异质性不仅在叙事上,鲜活又陌生化的方言时隐时现,还体现在人物异类和故事奇异,多是一段段正在进行时的青春和曾经如梦魇般存在过的少儿记忆。故事在小说中时隐时现,作者沉浸于个人生活的小世界里,在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里挖掘人性的微光。敏感的少年伤痛如影相随,家庭的悲剧,离异与出走,卖身与堕胎;南方的溽热潮湿和疯长的植物,县城灰暗的茶楼,杂乱的自建房,或铁皮出租屋;有时是孤寡老人、古怪男人、瘫痪少年、私生子和以出卖身体为生的女性,有时化为寻找母亲和姐姐的焦虑,有时化为被沦落于风尘的女友、母亲和姐姐们,有时对母性和异性的渴望如火燃烧,冥想世界里上天入地。作者探求那些与人物生命息息相关的普通人的悲喜,向个体尤其自我精神内部深处开掘,也可以说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融合对故乡家事、时代与自我的些许感知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呈现了原生家庭和童年经验对于人的精神人格的巨大影响,当人生有缺憾时,聪慧的青年作家用写作抒发情绪和填充。尤其顾骨叙述语言的陌生化,那些磕磕绊绊,似乎有语病的言语充满着南方的生活气息和异质性,第三人称的“他”并非作者,而是所有被遗弃的孩子们,那些在灰暗生活中寻找亲情和家园,乃至气味相似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喧嚣世界的孤儿。
《获虎之夜》养老院老人因志愿者学生读报的一则新闻引发的人间悲剧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人物间的情感疏离、隔膜和孤独感,以及底层微尘人物的人性微光。养老院的老人回望过往岁月留下的伤痕,一些时代特征一一显现,比如与年轻人格格不入的代际感,关心报纸新闻时政的生活习惯等,尤其关于逝去妻子的梦魇一直缠绕他的余生。妻子杀鸡时,死鸡在妻子的手里发出长鸣,而成为妻子过不去的心结,加之男人日常的吼叫,“有像百灵鸟那样歌喉”的妻子不仅不再吃鸡,而且沉默到抑郁出家了,直到早逝,老人在自责与怀念中独自过了几十年。在养老院的关怀活动中,志愿服务学生的载歌载舞,这些时代孤儿的老人并不愿看,而是关注外面的世界,请志愿者读报,得知动物园一只壮年老虎出走山里的新闻,老人当夜梦见进山出家的妻子把自己送到虎口了。梦醒时分,思妻心切的老人出走养老院也进山,并遇到熟睡中的老虎,久失温暖的老人“松开拐杖,任它掉在地上,随自己瘫进虎怀中”,“老人学习梦中的妻子,缓缓拥抱那只老虎,从虎腹一直摸到虎头,那些历历在目,虎也不改其色的纹路,在他的触摸中给他掌心提供一种温暖”。熟睡的老虎只呼了一口暖气,并不理会老人的恳求“求你了,咬我吧,像当时咬我媳妇那样咬我吧”。老人抚摸着依然酣睡的老虎,以他想象的妻子逝去的方式睡死在老虎怀里。一切似乎偶然,却蕴含着必然,熟睡的老虎何尝不是老人梦魇里吃了妻子的“不改其色”之虎呢?令人想起田汉先生《获虎之夜》,老人也成了莲姑那句著名台词所言说的,认为老虎出走,“它是催我的命的”,只是老人不同于莲姑的恋人黄大傻愤而自戕,而是将自己一生的疲惫瘫躺在老虎怀里,舒舒服服地在梦里到天堂与妻子相会了。当然,微尘人物之死无人探究,包括读报的志愿者小记者,也以世俗样貌继续功利的报道生活,现世的荒诞使文本的叙事也在此闭合,余韵绵长。相对而言,此作是六篇小说中完成度最高的。
如果说老人与田汉笔下的莲姑与黄大傻有意象和对应关系,标题也有向《获虎之夜》借鉴之意,那么《童谣1990》可以说是向1980年代的经典曲目《童谣1987》的致敬之作,青春的烦恼和对未来的向往,可谓精神血脉相通。《童谣1990》以一个个被遗弃孩童的视角看卖身母亲的人生和孤寂无助的童年,在一片被侮辱的空间里开启自己最初的人生,意绪缠绕。灰暗,无助;孤独,无语:“我和母亲住在茶楼三楼的某一间房里,房间是用三夹板切割出来的。三夹板把这里拼成蜂巢,我认得里面的每一只蜜蜂,每个格子间里都有很多个母亲和我的母亲一样在采蜜。当然,那些母亲大都没有真正成为母亲,就像我的父亲始终没有成为我的父亲一样。”人物大都是被暧昧的五颜六色的彩灯“照在本就面如死灰的人们脸上再照出另一层死灰来,让他们像我一样丑陋”。作者以“蜜蜂”的意象,怜惜这群夜里卖身,又早早起床给来喝茶的人们做卷筒粉卖早餐,她们如蜜蜂般辛勤劳动,是一群可怜的如草芥般坚韧的女性。而无数的“我”在这样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如野草般生存,或怯懦或忤逆或自强,作者还写了其他弃儿,以不同的视角,唱出这些被遗弃孩子的童谣:“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无怨吗?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当孙燕姿重唱并流行于2016年时,它是如何深刻影响彼时15岁的少年顾骨的。是的,他与笔下的少年渴望“亲爱的爸爸给我一个窗口,给我留一片还没有污染的天空”“亲爱的妈妈给我哭闹的时间,让我迟一些才学会标准的笑脸”,然而,生活不是理想,在灰色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有欢笑也是一地的藏污纳垢和残酷的少儿世界。童年的天真快乐是所有人的理想,一如流行歌曲《童谣1987》,“让我快乐地画一幅自己的向往”。顾骨尽管有些沉湎于生活实感而忘了抽身,在叙事逻辑和结构把握上还不够清醒,有些凌乱,此现象在《沥青蜻蜓》《收拾》《马留》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毕竟生活实感不等于小说叙事和审美,那是年轻顾骨的未来之路,这并不妨碍他深切地为这群人间的孤儿录影,书写不为人知群体的生活本相和向善向阳的期待,记下他们对未来的向往,因为理想主义是文学不变的底色。
比如《墨山壁虎》的生活实感也是浓烈的,三章南方故事内在相连,是“我”发育成长的过程。“我”在孩童时期,就与被毁容的镇上最美的女子“雪姐”为伴,尽管知道她的过往与现在,甚至与跳楼死去父亲的当年暧昧,但是她却是世上唯一关爱孤儿“我”的人。“我”依次从“吮指”的童年,到渐次理解了“人很不错”的“雪姐”,甚至以“入墨”隐喻她被毁的面容,使人物与故事有了智慧和审美光芒;第三章“成山”是五年后回家再见“雪姐”,成人的“我”对她的嫌弃与辱骂,主人公也汇入了世俗的功利社会。多年后“我”终于自省到:社会病态的一面,全镇男人都以被“雪姐”选中为荣,但所有男人当面又虚伪地与她划清界限,“每个人的影子都是黑的,黑得像一座墨山”,《墨山壁虎》在垃圾堆做了道场,“我”也完成了一个少儿疼痛的灰色成长史。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最后一只墨山壁虎断尾自卫的故事为小说作引,隐喻延宕,意味深长。充满瘴气的墨山“毒虫、蕨类、地衣、苔藓、壁虎”等遍布老林,而当人类肆意猎杀壁虎取尾卖钱,最后仅剩一只却永远被猎手包围,这只墨山壁虎为了活下去自行断尾:“每天,都在目光之下练习主动断尾,而后立刻转身吃掉自己的尾巴。只有这样子,它才能在人类到来时显得自己从未有过尾巴。猎手会放过失去价值的壁虎,它因此侥幸活下来,却又始终找不到有尾巴的同类。”“最后那只壁虎最终死在了咀嚼自己尾巴的过程中。”从此,世上再也没有人见过墨山壁虎。在某种意义上,“雪姐”们也是那只墨山壁虎的近义词。于是,“墨山壁虎”意象的隐喻与寓言性,使作品有了批判意义,也充满了悲情和悲悯。
wYD7ZEwwO33mKep2GmKngwv5jxs5nqZl/fRoK5dpmB4=青春写作大多书写着个体各异的青春孤独和身心成长,书写并获取自己对世界万物和社会人生的认知力量。顾骨的成长小说不仅个人情绪强烈,还注重拉回到个体生命最深层的涌动的灵魂,这个灵魂会敏感于南方炎热潮湿的时空,敏感于在尘埃的喧嚣中捕捉生活的声响、梦境里的声音、电话声,或是在唯一的属地——那张出租屋的大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梦魇,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更煎熬的还有临窗马路浇铺滚烫沥青的机器声和热浪,微尘的人生野气成长,野蛮或低空地生长着。
《沥青蜻蜓》是棚户区里充满沥青味的生活中,“我挥动翅膀,在贴地飞行的过程中,与你相拥。”“我”渴望一丝一点的爱意,并寻找在关爱中蜕变成长,哪怕空间相隔:“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房间从来没有三夹板做隔。三夹板区分的从来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和世界……明明我们都关着窗,但沥青的味道又出现了。我们将永远被这个味道缠绕了。”“我们在黏稠的沥青中耳鬓厮磨,目睹白蚁和蜻蜓像雪花般纷纷飘落。在满世界的昆虫雪中,我们将会目睹父母,以及南方的家从我们身上蜕脱。”
《收拾》李山在寻找女儿过程中,发现生活使女儿沦入风尘。一个个不可名状的电话,生活的无序杂乱,如顾骨小说无数的梦魇,演变到《马留》里,已成了植物人马留悲伤的一个个噩梦。马留(粤语是“猴子”之意)在似梦非梦中,还原了生活的一个个悲剧,车祸后离异父母各自的绝望,同为车祸早逝的姐姐归来的魂魄,父亲的太息,他的心跳声、鼻饲时流质的声音、父亲替他翻身时肢体与被子摩擦的簌簌声……“听到自己在枯萎的声音,疑心自己身上覆满了青苔与蘑菇,或者爬满了蛆虫。这一念头可以让任何人失声尖叫或痛哭,而马留能做到的却只是失声。六年以来,他躺在床上,宛如死般安详,却比谁都更固执地用意念咬住声音与记忆,不敢有丝毫怠惰。他生怕自己一旦再次坠入昏迷之中,就再没机会醒来,因此不断地打磨着知觉的牙齿,请求它们不要停止感知事物。”
于是,马留在梦境里,爱马留的姐姐灵魂归来与他贴身而梦,她是一把能切开梦境的刀,能够替他切开安然坐立的噩梦,让他醒来。但这把刀是有代价的,他想,姐姐的结局不尽然不是一种噩梦。因为,姐姐也在挥刀,“切断自己与亲人的联系,也顺手帮马留切断自由行走的梦。他们三个人如是互相冷暴力着对方。”马留姐弟和父亲三个亲人却各自哀伤决绝,刀锋闪烁。只是马留相信了姐姐在梦里说的,自己就是马留,瘫在床上将孤独地永远在蛮荒的人世间,而且,他和姐姐都是马留(猿猴),就像传说中的马援将军,变成石山永远驻守在南方蛮荒的山峰上。
纵观六篇小说以及作者的文学小世界,这些疯长的对灰色生活的沉思,卑微而善意,残酷而犀利,悲伤而悲悯, 如此的文学潜力,假以时日,相信顾骨将来定能走向广阔世界与人间烟火,提升还原生活的能力和跳出自己主观意绪的能力,并最大程度地与具体的生活细节交融,赋予叙述以细节以叙事,使书写更具象,让人物形象挺立起来,拉回在目前叙事的云山雾罩里走失的读者。
顾骨是热爱南方的,他以陌生化的语言呈现了万物蓬勃,鲜花果实与野草毒虫疯长、烈日普照与旺盛活力的南方,他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必定向世界散发出他独有的文学生命力,因为从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目标都是要走向世界。同时,期待顾骨“长大后不会对着灰色无奈”,面对世界,寻求到一条自我觉悟之文学道路,尽管天真于自我,尽管成长孤独,尽管言语磕磕绊绊的,但是他正以自己的南方的异质性写作发育成长着。希望他早日建立自己的文学表达,因为“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规矩地唱”,相信他会走出出租屋在广阔的视野中去书写,让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觉深入人间万物,在生活细节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审美光芒。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