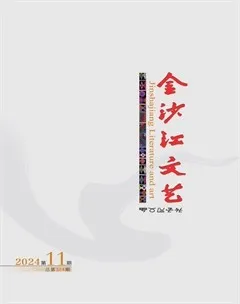烟火小巷(外一篇)
2024-11-27胡晓华
如果要给这个小巷拍一张照片,得用一个超大广角的镜头俯拍,才拍得下它的壮美。
狭长的小巷,被各个摊位上或是茶壶,或是煮锅里袅袅的白气装点得仙气飘飘,那些个身着红花碎步的上衣、印着海绵宝宝的围裙、工厂里淘汰下来的磨得有些粉蓝的工装、背上印着某某村小组和巨大号码的运动短褂的小贩,以及和我一样光顾小巷生意的顾客,都是这条小巷不可或缺的角儿。这条狭长而又陈旧的巷子,灰暗的色彩为主的背景色,维持和固定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是两边斑驳的墙。有的石灰墙面都呈现了赭石和红土颜色,定然是时光的杰作,可能也有屋檐漏下雨水冲刷的功劳。能想得到大雨光临小巷时,那些在油布或是三色塑料层上或嘭嘭嘭、叮叮咚、唰唰唰或是咻咻咻的声响下面,在各色塑料凉鞋或是雨鞋中回环反复后,在一些较为平坦的地面,雨水们就干脆不走了,就留下了我现在看到的石灰墙脚上或深或浅的线条。有的变成波纹或是抽象画派的线条,则是人们争着到屋檐下避雨或是奔跑溅起的水花的“画作”。墙面上有几处木窗,早已见不到深红色或是土黄色的本色,岁月把他们的颜色褪了下来,变成了很淡很淡的红色或是仔细看才能识出的黄,在不抢眼睛,甚至似乎故意想躲起来的这种陈旧和慵懒的背景下,显得那么协调。它们旁边走过的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夫妻,步履蹒跚、相互搀扶。老头的肘部和膝盖被洗得有些白,几乎就要破成看得见的棉线了,但是他脸上却有着岁月积淀的沉着。老妇轻轻搀着他,花白的头发把他的布满皱纹的脸也映衬得白净。装菜的布袋很旧,但显得特别有质感。几根大葱的叶子不安分地探出脑袋,旧和新、沉寂和鲜活顿时充斥在这个画面里。
如果初来,你会觉得在这普通且狭长的水泥地板之上,一场厨艺大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是战得正酣,两溜儿排开的锅碗瓢盆、炉子、水桶……人们掌着铲、勺、瓢轮番上阵,乒乒乓乓在小巷里交响起来。激烈的“鼓点”之后,定是高手闪亮登场。只见做饺子的阿婶憋足了劲,面团被抛起,然后重重落在案板上。硕大的面团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白色的面粉营造的氛围中,阿婶的目光如炬。这边一只粗壮手臂抡刀在空中旋出一条弧线,似乎能听到刀锋在空气中“嗖”的声响。一块膘气十足的猪肉在砧板上弹了一弹,似乎在展示自己的新鲜。那条弧线在它复弹起之前猝然而至。随着如疾风般密集的哒哒哒声,鲜肉末在砧板上跳跃、飞舞,一如音浪般起伏,引来观众无数的目光。阿叔似乎也不甘示弱,黄灿灿的大饼,以平底锅为平台,在空中飞起,落下,弹射,再飞起……不曾想一条普通的小巷竟然有如此之多的隐世高手。
小巷小,以至于摆不下一张可以供人们搁置饭碗的桌子,一只高脚的塑料凳就是桌子,而较小的则为凳。排队的既有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上班族俊男靓女,也有着背心、人字拖鞋的市井百姓,在排队后取得一个包着粗纸的大饼而去,也有可能取得一碗鲜肉帽子的早点,找地方坐下,摒弃了焦躁,静静坐着不时吹一吹,筷子挑起袅袅白气的食物。从他们眉眼间的动作不难看出,这美食慰藉了他们的肠胃,也丰富了他们已经开启的早晨。
小巷比不上王府井那般大气,也不如宽窄巷子那样出名,却并不妨碍人们每天来这里聚集。有很多人还是这里的常客,甚至有的人已经和这个小巷有了几十年的交集,每天到这里感受、品尝、采集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想,小巷里的很多人终究会离开的,但离开的很多人都会想念这一条叫不出名字的小巷,会因为想念不得见而神伤,抑或会因为时时积累的想念会再回到这里。那时,哪怕只是极短的相见,也会为接下来的历程积蓄更多力量。
我也会时时想起巷子里的人、巷子里的样子、巷子里的味道。一个小巷竟然能容太多太多,三教九流,各种阶层的人都能受到悦纳。我欣赏小巷不仰视、不俯视,不媚上、不欺下。我敬仰小巷的真诚善良、脚踏实地,在去留随意、不疾不徐的呼吸中,让小巷的人在从容平静中,感受人间烟火的美好!
市井长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
有 待
我小时候有很多趣事: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老师无意说一句柳枝插在土里就可以长成柳树,下课便第一个冲出教室到河边折了枝条,放学就插到家里的院子,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它浇水,每天一回到家就冲去看它有没有发芽,有没有长高,只是可能因为浇水太多,终变成了炉灶里的柴火。听说番茄籽扔在土里便能收获小苗,于是每次家里要吃番茄我都争着洗菜,待娘切菜的时候我就守在旁边,小手从砧板上摞得几个籽便飞奔放到屋外墙根,第二天便迫不及待想看看有没有发芽,接连重复了许多天,每一天都过得有所期待。现在想来,每天上学回来先去看它不正是现在很多人说的“仪式感”吗?所幸后来发现还真的发出嫩芽、开出花朵、结出果实来。
正如我在等柳树长成、番茄累枝,种子生根、发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需要吸收足够的阳光雨露,需要用充足的时间去耐心等待。有时候,生活有没有意义,可能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等待的事情,或者有没有有意义的事情在等待你。
每次要出几天门,我都会洗两件自己喜欢穿的衣服,那些不同的物料伴着洗衣液的泡沫摩挲着手掌,如果遇到天晴的日子,那些泡沫衍射出的五颜六色的色彩,让人想起穿着这些衣走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以及当时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把它们挂到阳台上,看着不同色彩的布料如旗般在微风中飘扬,像极悠闲自由的旅人。然后在出门的几天里,除了做预订的事情,还会留一点时间想想家里等我的人、还有待干的衣服,回到家自然首先是奔向家人,然后把阳台铁线上的那些斑斓色彩取下,放在鼻子面前细嗅。我喜欢阳光晒了几天后的衣服,除了喜欢洗衣液的味道,还喜欢淡淡的阳光的味道,每每这时,我的心里都会泛起阵阵涟漪。
我喜欢抄写,我会把自己看到的好文章、句子用笔记本抄下来,笔记本的格子一定要极宽,好让我不用纠结会不会超出“界限”,可以让我边抄写时边想象文字中的那些个场景或是意境,哪怕写到文字歪七扭八,待哪天再看这个文字的时候,扭曲也变成了一种情绪和态度,竟然觉得别有生趣,纸张一定是要摸上去很舒服的那种。我一直以为,美的文字只有躺在舒服的地方才能在相互滋养中变得更加有趣、有味。以每天一段话、半把页的积累,让文字变厚,等待些时日,文字的凹凸让笔记本变得略厚,再待些时日,它们变成了一摞书。在百无聊赖的午后,懒懒地靠在沙发上,懒懒地抽出其中一本,让这些文字来浸润自己的心,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初见这段文字的那天。
我还喜欢存酒,我所谓的存酒不是世人所知的把那些个茅什么、什么液的,也不是那些除了英文和看不懂的图案装饰的进口红酒,而只是一些乡下烤出来的粮食酒。正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连心情也是这样,工作、生活都会给你找些麻烦,有时候甚至困在里面许久走不出来,这样的时间多了我就想到了存酒,乡下的集市上随时有的土罐我会买上一两个,在所谓的至暗时刻以最常用的塑料桶到老乡家打上一桶,然后烧几根稻草焖在其中,以冒不冒烟判断罐体是否完好,然后用稻草擦洗土罐,待晴时抱到屋外烤太阳,到外面找玉米把子,辅之以干净的塑料布,制作适合土罐的“塞子”,然后倒酒入罐,封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贴签。签上可不是什么名家写的“酒”字或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之类的名句,而是记录某年某月遇到了某事情。忙活完这些,那些烦心的事,都被看得开了一些,再待口一封、签一贴,就如同那些糟心事也早就被封压在里面了。待过一两年,好朋友相聚时取出,伴着醇厚的香味。在把盏言欢至微醺后把这坛“酒”背后的故事笑着讲出来,又是几番觥筹之后一饮而尽,那些当时看来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也随之灰飞烟灭。自己因酒后的几句话,俨然成了朋友眼里的“哲学家”,待下次酒后听朋友“复读”自己的这几句话,譬如“人生哪能都圆满,不圆满就不走了吗?”“成年人的难就难在即使是磨脚、流血也不能停下来,等伤养好再向前走,纵是含着眼泪、咬着牙齿也要把路走完”,譬如“那些不愉快,何妨把它们攒起来?纵使当时苦酒一杯,但是只要你善待它们,做好自己,假以时日也有可能是美酒一坛。”……
在有的人眼里,生活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换个角度来看生活就是一个期待接着一个期待,哪怕所谓的期待只是“等苦难赶紧过去,好日子就会来临”,也就是说,人生一定要有所期待,正因为有了这些期待,我们才会觉得日子有盼头,未来才会有希望。这些期待、这些盼头、这些希望,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大海上的灯塔,指引我们驶向更光明开阔的地方。
所以,让我们把保持期待作为人生的常态。只是这样的常态,还需要有一种理性的心态和豁达的胸怀来助攻。那就让我们缓缓而行,久久有待,让这些期待使得我们的生活生机勃勃、多姿多彩。
责任编辑:余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