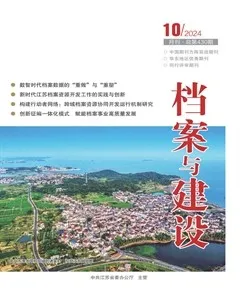档案行政复议的制度实践与路径优化
2024-11-26张健王筱盈
摘 要:通过对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的1200起案件样本的讨论发现,行政复议作为与行政诉讼相比肩的化解档案行政争议的法律渠道,在促进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仍存在作为化解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有待提升、监督与纠错作用有限,以及档案馆的角色定位有待明确、档案开放申请人缠讼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未来应当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为契机,多措并举,不断完善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档案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关键词:档案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档案主管部门;权利救济;监督
分类号:D922.16
The System Practice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Zhang Jian1, Wang Xiaoying2
( 1. 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2. School of Law,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Through a sample discussion of 1,200 cas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9, it was found that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s a legal channel for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n comparison wit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awful administration of archival authorities, substantially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nd so on. However, the current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as a main channel for resolving disputes, still needs to be enhanced in its functions, and its roles of supervis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are limited. Moreover, the role of the archives needs to be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problem of repeated malicious litigations made by applicants asking to open up the achieve(s) is relatively seriou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t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ly revised Administrative Review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opportunity to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view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view system in solving the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Keywords: Archival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Right Relief; Supervision
2023年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新《行政复议法》”),新《行政复议法》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次《行政复议法》的修订从明确行政复议原则出发,完善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理及做出决定等程序,并强化了行政复议监督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作用。[1]
在档案领域,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道,在法律层面共同构成档案行政救济的“两翼”,拓宽了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行政诉讼有明显的“民告官”特点,而档案行政复议的优势在于其简易的程序以及较短的时间周期,可以提高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然而,学术界既有研究大多围绕行政复议体制及其改革对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影响[2-3]、某一特定地区的档案行政复议工作实践展开[4-5],而关于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研究较少。文章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政府网站收录的1999年《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以来的1200起案件为样本进行讨论,全面考察二十余年来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变迁,归纳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同时,由于新《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与实施将对档案行政复议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也将对新《行政复议法》中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分析相关规定对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带来的影响。
1 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意义
1.1 强化档案主管部门内部监督与自我纠错能力
行政复议是反映法治政府建设质量的“晴雨表”,是行政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倒逼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助推器”,对于推进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就执法而言,依法治档的关键是档案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这不仅需要从外部利用行政诉讼等机制对档案主管部门进行监督,也需要从行政系统内部对其进行规范。行政复议正是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做出相应决定的一种行政活动。《行政复议法》确立的制度框架有利于上级机关或者本机关充分发挥自我监督与自我纠错的作用,通过对个案中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情况的审查和评价,对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督促其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同时,通过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在对下级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同时,也能不断自省,不断提高自身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1.2 有效预防与实质性化解档案行政争议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途径,在解决档案行政争议的过程中比诉讼专业性更强。档案行政复议制度是档案主管部门内部层级的监督制度,如果下级档案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存在错误,行政复议机关作为上级行政机关有权依法进行纠正,及时把争议化解在萌芽状态,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并减少档案行政争议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实现了档案行政争议在法治轨道上得以化解的目标,这对于实质性化解档案行政争议、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3 保障公民合法利用档案与寻求救济的权利
相较于行政诉讼,简便、经济和快捷是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优势所在。同时,在审查标准上,行政复议制度审理强度更大、审查范围更广。随着法治中国的全面推进,档案行政复议制度更多地为公众所了解、所掌握、所信赖,并被公众主动运用于档案行政争议的解决过程中,日益成为社会公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不少地方的复议机关积极采取举措提升复议便捷度、降低行政复议成本,使档案行政复议成为比信访更具法律效力,比诉讼更高效、便民、经济的渠道,有利于全面保护公众权益。
2 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实践图景
2.1 复议案件数量稳步增长,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作用凸显
《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这一途径解决争议,档案行政复议案件不断增多,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数量从2000年的4起上升到2022年的76起。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在公众层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断提升,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优势不断显现。这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随着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公众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意愿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不利于自己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寻求救济;二是过去的二十余年,土地、农牧林水、建设规划等档案领域执法案件不断增多,尤其是土地、林木、草原等权属纠纷与公众切身利益联系紧密,行政复议作为政府监督部门的有效手段,必然得到更多公众的使用;三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权威性与便利性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例如不少地方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了行政复议窗口,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的申请方式,能够更加公正、合理地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四是律师或相关团队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档案行政纠纷,各地探索出了较为成熟的诉讼服务模式,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数量的增加。
2.2 复议案件所涉事项出现变化,强制命令类行为占比降低
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即因何种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二十多年来,档案行政复议案件的事项类型涉及诸多种类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不过,这期间的案件所涉事项类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自2000年至2009年,传统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单方命令性行政行为以及行政不作为等案件始终在档案行政复议案件事项类型中占据较大比例,其中,行政处罚争议最多。但2010年以后,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类案件数量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而信息公开、政府不作为等方面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其中,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行政复议案件中最高的一个类型。这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有一定的关系,民众有了申请获取信息权利的同时,相关争议也不断增多。伴随着给付行政时代的到来,政府管理方式更加多样化,老百姓也更加青睐于选择行政复议这一高效又低成本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知情权与财产权。
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传统的行政处罚型行政行为案件占比不断下降,而政府信息公开和举报投诉处理类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持续增长,在2022年的案件数量上分别位列第一、二位。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在传统的行政处罚型行政行为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政府信息公开、举报投诉以及行政不作为等事项类型。由此可见,档案主管部门逐渐从社会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公民个人权益的给付者,鉴于社会公众在行政管理中的角色逐渐由被动的被管理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档案主管部门所要保护的公民的权利范围也不断拓展,愈加需要注重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知情权。
2.3 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纠纷呈攀升态势
样本案例中,2021年,全国范围内共有49件档案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案件,占同时期档案行政复议数量的81.7%。该类案件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行政复议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数次修订为档案行政复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档案主管部门的档案信息公开力度不断增强,档案信息复议的案件数量也随之增多;二是相关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解不透,困惑较多,纠纷随之增加;三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本身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解释性空间,各级档案主管部门遇到复杂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在合法地应对和处理上存在不少困难;四是当事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进行维权的意识逐渐增强,主要是先提起行政复议、诉讼收集证据,再跟进及开始第二轮复议、诉讼。
从样本总量来看,档案信息公开案件的数量占到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总量的近八成,其所涉及的领域广泛,但是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征补、政府公文、历史信息和城乡规划五个领域。这五个关乎民生的重点领域的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又占据了档案信息公开案件总数的79.9%。以下对案件数量较多的前三个领域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土地档案信息资源是解决土地资源使用纠纷的重要参考依据。尤其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旧城区大量改造改建,几乎每个环节都涉及土地档案信息。例如,张某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从××市城乡规划局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张某户征地红线图》复印件后,认为“红线图”与提交的申请材料显示的并非同一块土地,所获材料系伪造,便向××市档案局提交《查处申请书》,市档案局在核实后告知申请人无误。张某不服,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得到了维持行政行为的决定。[6]第二,房产档案信息是界定和保护房地产权属的重要信息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登记身份信息混乱,档案没有实现标准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使得在房屋拆迁领域引发的档案行政复议案件数量较多。例如,王某认为××区房地一中心存在伪造魏家胡同×号房产档案的违法行为,向××区档案局举报。该档案局做出了未有证明××区房地一中心存在其举报的违法行为的答复。王某不服,向市档案局提起复议申请,市档案局做出了维持行政行为的决定,此后该案当事人申诉至最高人民法 院。[7]第三,政府公文类档案信息在有效听取社会意见、接受公众监督与维护公文严肃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政府信息公开责任主体之间存在推诿现象,各部门间信息共享效率低等问题对于民主行政和互动性行政目标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例如,田某、吴某、孙某三人分别在××市××区拥有合法房屋,为核实有关部门对其房屋进行腾退的合法性,向××区人民政府申请公开“××市××区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指挥部”具体职能、设立机关以及该指挥部人员编制及组成情况等政府信息。××区人民政府告知其文件已移交档案馆后,三人又向档案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告知该文件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作保存,建议其向××区信息公开综合服务窗口咨询,三人不服,向市档案局提起行政复议,但是复议结果维持了原来的行政行为。[8]通过上述对案件类型较为集中的前三个领域的分析可知,虽然档案信息公开的相关权利人有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的权利,但是大多得到了复议维持的结果,可见相对人的实体诉求并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
2.4 复议(诉讼)结论:绝大多数档案主管部门行为合法无过错
在1200个档案行政复议案件中,不乏经过复议后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从复议的决定与判决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档案主管部门的行为合法无过错。具体表现为:1143起案件的复议(诉讼)结果呈现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驳回复议/驳回诉讼请求、维持原行政行为/判决,占案件总数的95.2%。可以说,在行政复议或者诉讼中,大多数档案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且程序合法适当,无明显过错。在57起档案主管部门有过错的复议(诉讼)案件中,有36起属于程序性过错,主要包括作出的答复决定超过法定期限,或者答复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21起为实质性过错,表现为应当公开被申请的信息却不公开,或者事实不清、答复不当等。比如,康某诉××市人民政府、××市档案局一案[案号:(2017)渝0103行初45号],原告前后两次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档案局申请公开由其保管的原告祖父信函,但被告市档案局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未依法向原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告市档案局拒不履责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告市档案局履职。但是,被告市政府没有调查,没有查明基本事实,直接驳回了原告的复议申请。法院认为被告市档案局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职责应予以确认违法,相应地,被告市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亦应予以撤销。
3 档案行政复议存在的问题
从实践来看,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在社会公众层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断提升,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优势不断显现,但是现实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3.1 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作为化解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有待提升
档案行政争议日益增多与行政复议受案数量徘徊不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有待提高,行政复议作为解决争议主渠道的地位还需进一步稳固。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档案行政复议工作宣传的力度和深度不够,社会知晓率不高,部分行政相对人不知复议、不会复议,仍然习惯通过上访或诉讼途径来解决争议,影响了行政复议化解档案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档案行政复议刚性还不够强。推进“以案治本”的覆盖面还不够广、落地性不够强,一些档案主管部门对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不到位,对相关改进执法的意见建议落实反馈不够及时。
3.2 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监督与纠错作用有限
从理论上说,行政复议是非常重要的行政执法监督环节,但是不少案件在经过了行政复议后,又进入了诉讼程序。就样本案件而言,以下三种情形值得注意:第一,档案行政复议发生在行政行为之后,即便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错误,出于避免行政风险或维护档案主管部门形象的考量,复议机关甚至会忽视对该行为的纠正,简单交代诉权,把当事人推向诉讼。第二,个别档案主管部门作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在收到复议答复通知后,消极懈怠的态度明显,对争议行政行为不加调查,简单答复,应付复议办案人员;或者不愿与复议申请人进行沟通,宁愿被复议机关纠错也不愿意调解,没有把复议工作摆正位置,造成争议解决难度增大。第三,按照以前《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对有关组织和人员进行调查,所以复议机关在审理复议案件时多数只作书面审查,而没有真正到实地对档案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复议流程流于形式,这导致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更谈不上发现错漏和纠正了。
此外,档案行政复议机关独立性不足。目前,我国档案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并不多,其中一个因素便与档案行政复议机关的依附性有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这种组织结构通常导致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到裁决的公正性。[9]当复议机关的某些内部部门负责审理与自己隶属的行政机构相关的案件时,其弊端尤为明显,这不仅损害了档案行政复议的权威性,也削弱了公众对整个复议制度的信任度。此外,档案行政复议机关在组织架构和法律规范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其附属地位,复议机关往往难以摆脱上级部门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复议过程中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现行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复议机关在处理复杂案件时的实际需求,导致复议机关在面对一些复杂情况时难免“力不从心”,档案行政复议的纠错、保护、监督功能发挥受限,便民之法的公正性难免受到申请人的质疑,有悖于立法者的初衷。
3.3 档案馆的角色定位有待明确
机构改革后,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整体要求,档案局馆的职能落实在公民档案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角色混乱现象。[10]根据《档案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档案局是负责档案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其作为档案行政诉讼案件适格被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一直以来,档案馆是否具有行政主体地位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实践中,档案馆多以被申请人的角色出现,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的缘由多为不服档案馆做出的“未查询到相关信息、不由本馆接收和保管,故无法向申请人提供该信息”等回复。比如,××省档案馆作为集中保存、管理档案的事业单位,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姜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省档案馆不是适格的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姜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被驳回。[11]正如本案显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档案馆基本不会被复议机关认定为适格的被申请人。申请人在寻求救济时将档案馆作为被申请人,是其出于不正确的认知做出的判断,其后果则是档案馆被当成了适格的替代品。即在档案行政复议案件中,适格的被申请人可能是档案局,可能是移交档案的档案形成者,亦可能是档案馆隶属的同级政府。由此,在局馆分设的档案管理体制下,当申请人向复议机关提出权利救济时,档案馆“代位”成为了被申请人,复议主体的错乱导致申请人的救济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3.4 档案开放申请人缠讼现象较为严重
在我国档案开放步伐加快、开放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档案开放的申请人只需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既可向档案主管部门提出开放档案的请求。档案开放申请的低门槛设置在实现为民服务效能的同时,也导致部分当事人曲解档案开放的意义,甚至恶意滥诉缠讼。具言之,应当根据个案考察当事人是否具有提出复议的利益以及实质要件,挖掘有关档案信息公开引起的档案复议的具体内容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诉求。若当事人反复申请信息公开,并不断提起复议的目的在于发泄情绪、引起社会关注或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应当取消其申请复议的权利。此外,当事人是否有提起复议的必要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能够判断该当事人是否存在缠讼行为。如果可以通过诸如申请信息公开等形式解决诉求,或者明知该申请不属于应当受理的范畴,当事人仍然选择反复缠扰档案部门,显然缺乏提起复议的必要性。以范某与××市档案局、××市人民政府一案[案号:(2020)苏04行终161号]为例,范某明知“市政府让其向市档案局管理的事业单位申请”,仍选择向市档案局多次申请公开相关文件,并提起复议和诉讼,而非向××市档案馆查询相关信息。由此见得,范某并非为了获取该文件信息,而是滥用诉讼和复议权利,故而导致纷争出现,属于出于个人利益而占用司法资源的典型案例,我们需要对此类现象进行规制。
4 以新《行政复议法》实施为契机,完善档案行政复议制度
4.1 多措并举发挥档案行政复议化解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一是以新《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大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宣传力度,对应当公开的行政复议工作内容,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尤其是行政复议受理途径、受理程序及决定文书等;积极通过普法宣传,提高档案行政复议参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广度与深度,扩大社会公众对行政复议的熟悉程度。二要提高档案行政复议制度的监督刚性。推动行政复议监督效能充分延伸,以有效举措强化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避免公众“赢了案子得不到实惠”。持续推进“以案治本”,综合运用各类手段将问题和压力溯源传导给档案主管部门和一线执法人员,通过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的方式督促改进工作。三要加强档案行政复议合意型机制建设。加强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探索和规范调解类型与方式,开展行政复议案件全过程调解,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四要进一步提升各级档案主管部门的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对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执法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依法行政方面的系统培训,提升其法律素养,增强其厉行法治、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切实提高其依法行政的意识,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产生。
4.2 推进档案行政复议制度改革
第一,完善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方式。首先,完善行政复议告知告示程序,凡是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均发出受理通知书予以告知;凡是不予受理的,均出具正式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告示复议申请人的相关诉讼救济权。其次,全面推行听证、质证等方式审理案件,规范行政复议证据审查制度,加强实地调查力度,及时通知复议申请人查阅相关案卷材料,保证复议结果公平公正。再次,推行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对于新类型案件以及事实认定存在争议、法律适用存在分歧、社会影响较大等疑难复杂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必须集体讨论,经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做出复议决定,以此提高行政复议的办案质量和效率。最后,从讲清“法理、事理、情理、文理”角度完善行政复议决定书说理内容,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在政府法制信息网向社会公开。
第二,增强档案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全国范围内的档案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较少,这与复议机关的组织设置和运作模式有关。虽然现有的复议机关能够应对目前的工作量,但为了确保这些机构能够更加高效和公正地处理案件,有必要增强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尽管不需要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中独立出一个新的部门,但需要对现有复议机关进行改革,以确保它们在行使职权时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并有效地发挥监督、救济和解决争议的功能。[1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上级管理部门应当考虑适当放权,减少政府部门和档案主管部门对复议过程的潜在影响,降低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裁决者的依赖,从而避免“程序空转”和“暗箱操作”等现象。
4.3 明确档案馆的角色定位
对于档案馆的行政主体资格认定,现行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新修订的《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条例》”)均对档案管理机构关于向社会开放档案、提供档案的法定职责进行了规定。具体来讲,《档案法》规定了综合档案馆拥有开放审核权,《档案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赋予了国家档案馆对于档案开放范围的决定权。《档案法实施条例》在三十四条中还将提供利用档案的决定权赋予国家档案馆。这些权力均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的实现直接挂钩,所以,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也理应受到监督和制约。
档案馆的角色定位是以事权分离为基础的,虽然在实践中只有少数案件承认档案馆的行政主体资格,但从多数以档案馆为被告或者被申请人的案件中可以得知,档案馆已然成为影响当事人行权的直接主体,根据“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说”,档案馆应当具有被申请人的资格。[13]但是,如果按照教义法的严格标准进行阐释,新《档案法》中将档案局定义为行政主管部门,档案馆只是接受监督的行政相对人。这意味着虽然档案馆不是行政主体,却做出了影响公民实际权益的法律行为。即档案馆承担行政主体的职责,却拥有事业机构的外观,其履行着行政管理的职责,却披有服务单位的外衣。如此,档案馆面临着角色不明、职权模糊的现实困境。未来应当明确档案馆的角色定位,畅通当事人的救济渠道。
4.4 提高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缠讼成本
在坚持“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指导方针的前提下,我国档案开放、查阅便民化程度不断提高,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完善更是为申请人提供了权利救济的途径,但实践中不乏同一当事人重复提起复议或者诉讼的情形,如此具有情绪宣泄性的行为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故提高缠讼成本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具言之,档案行政复议费用应由财政予以保障。档案开放与信息公开关联紧密,尽管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办印发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建立了收取信息处理费制度,但是需要缴纳的费用与期待利益严重失衡,我国也并未规定滥诉缠讼的惩戒机制,亟待合理可行的举措规范档案滥诉缠讼现象。一方面,创新档案行政复议滥诉的惩罚机制,针对劝阻未果,反复以诉讼、复议等方式恶意缠绕档案部门,妨碍其履职的,不予受理其复议申请,从源头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对于涉嫌滥诉且拒不悔改的人员,实行信用惩戒机制,严厉打击滥诉缠讼现象。
4.5 积极调解,力求实质性化解档案行政争议
新《行政复议法》的一大亮点便是在法律上确认了调解这一解决争议的重要途径,并对调解书的制作与生效作出了明确规定,再次印证了复议调解制度符合公众参与原则与利益衡量理论的要求。[14]此外,新《行政复议法》在立法方式上将调解范围从正列举条款明确为基本原则,这反映出发挥调解实质性化解争议的立法意图,实质上扩大了调解的适用范围。即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就可调解结案。相应地,档案行政复议机关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寻求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是坚持不违反公共利益原则,国家授权给行政主体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档案行政复议案件的调解不得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三是发挥各部门的合力,讲清法理、情理,对部分案件调解停滞不前、当事人申请终止调解,或在调解协议生效前反悔的案件,应及时恢复审理,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项目编号:23FTYB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贡献说明
张健:提出选题、设计论文框架、修改论文;王筱盈:撰写论文、修改论文,收集与处理资料,本文通讯作者。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姜明安.建构和完善兼具解纷、救济和监督优势的行政复议制度[J].法学杂志,2023(4):20-32.
[2][13]马秋影.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对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1(3):47-50.
[3]袁光.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档案行政复议职责[J].档案与建设,2002(9):25-26,33.
[4]马秋影.北京市档案行政复议北京市档案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研究[J].北京档案,2019(10):23-25.
[5]王惠,胡文苑.行政法视域下国家档案馆行政主体资格辨析——以胡某诉杭州市档案馆行政复议案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9(6):35-41.
[6]参见(2018)闽08行终145号。
[7]参见(2016)最高法行申1722号。
[8]参见(2018)京02行初202号。
[9]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82-383.
[10]陈忠海,刘东斌,吴雁平.机构改革背景下档案局馆协同机制探讨[J].档案学通讯,2021(4):4-9.
[11]参见(2019)湘01行初599号。
[12]曹鎏,冯健.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的困境与变革[J].中外法学,2019(5):1217-1233.
[14]王青斌.论行政复议调解的正当性及制度建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4):145-153.
(责任编辑:冯婧恺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