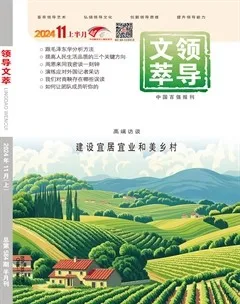六先生邵逸夫
2024-11-20蔡澜
在六先生(邵逸夫)身边那些年,我学习到一件事: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地去做。
六先生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到最后能以英语对答如流,都是因为他认真地去做、去学。
六先生后来能够那么长寿,也得益于他很有规律地健身,如学练太极拳等。他的那种毅力,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坐上他那辆劳斯莱斯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后座那盏小灯看报纸。我问他为什么只看某报,他说:“时间已不够用,世间发生的大事只有那么几件,看一份报纸已经足够。”
六先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上了年纪后,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一定会衰退,就在西装的口袋中装上一盒硬卡纸。那是四角镶金的牛皮硬板,中间塞上白色的纸张,他一想起什么事,即刻用铅笔记下来。他的字写得很小,但非常用力,常常透到第二张纸上。做过什么承诺,他一定会记下。
回到办公室,他就叫秘书把小纸片上写的事输入备忘录。他有两个秘书,一个专记中文,另一个专记英文。英文秘书是位来自英国的女士,用的是速记方法,用蚯蚓一样的符号迅速记下他的一言一语。
六先生还有厉害的交际手腕。六先生很爱开派对,他在片场中建了一座别墅,但自己并不住进去,只是用来宴请一些嘉宾。别墅中的戏院,常放映一些新电影。那些电影都是未经电检处审核的,片中的大胆镜头也没被剪掉,常被观众津津乐道。
他吃的东西非常粗糙,家佣们做的餐也照吃。六先生认为,西方人都不太会吃。他用的餐具倒是很讲究,比如,他有一只此前没人用过的碗。这只碗有可以拧紧的圆形银盖子,下面可点蜡烛加热,这得到了“洋人”的叹赏。
他喜欢喝一种叫普伊富赛的白葡萄酒,一箱箱地往家买。当年那酒也便宜,但外国朋友感觉非常高级了。
设宴之前,他一定自己走一趟,检查会场有什么不妥。我曾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一次,他检查时,刚好发现一个银幕的控制开关坏掉了,转头跟我说:“要是没有亲自看过,到时候从哪里找电工来修理?”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邵氏片场每年得制作四十部电影,才够维持一条院线的运营。六先生说:“什么戏都要拍,这种题材的戏观众看厌了,就换拍另一类的。观众永远不会满足,永远要用新的片子来喂饱他们,这样我们才能生存。”
“那得拍些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可拍,就是不能拍观众看不懂的,不然他们会背叛你。”他说。
六先生的眼光很准,也许是他在这一行已经做了很久的缘故吧。
“万一有一部失败了呢?”我问。
“很少有万一的情况。”他说,“就算有万一,票房不会骗人。如果第一天放映时没有人去看,那么就得马上换片,保住这块招牌最要紧。”
后来,他还叫人在片尾添加上一行字幕:“邵氏出品,必属佳品。”
年轻人都喜欢看一些带艺术气息的片子,我年轻时也对电影有一点儿所谓的抱负。我跟六先生说:“一年拍四十部,就算有一部有艺术性但不卖座的片子,也不要紧呀。”
六先生笑着说:“一年拍四十部,为什么不四十部都卖座,一定要其中一部亏本呢?”
“好莱坞也是商业电影为主,但他们的作品也有些是很有艺术性的,市场也能接受的呀。”我抗议。
“你知道他们的市场有多大吗?”他反问,“当我们也有这种市场,我也肯拍一两部来试试。我不是没有失算过,在观众看厌了黄梅调时我就转拍刀剑片,当观众看厌了刀剑片我就转拍功夫片。总之,动作片最为稳当,从默片《火烧红莲寺》开始就是这个定律。”
“要是观众把武侠片也看厌了呢?”我追问。
“那就得拍其他片了。”他说,“如果你爱电影,像我那么爱电影的话,你就会了解,你想在电影行业中多忙几年,什么题材都得拍,就是不能拍艺术片,那是另一种人才拍得好的。我是商人,做商人就要做到底,不能又想做艺术家,又想做商人。电影这一行,是‘烧银纸来讨好观众’的,不‘烧银纸’的话,就很难赚到观众的钱。”
(摘自《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