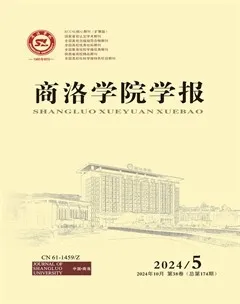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零K》中的后人类生命政治:从“向死而生”到“不死之死”
2024-11-10王瑜镜张春燕
摘 要:唐·德里罗的科幻小说《零K》展现了影像技术、生物技术和合成技术铰接下的后人类生命政治图景。在“人体冷冻项目”中,生命被敲零打碎,成为多重现代技术重构的对象。其中,影像技术着力于矫正记忆,屏幕中的虚拟影像入侵人类大脑,将记忆褫夺为数字的阵地。生物技术消费身体,生命被降格为商业王国内用于“生产消费、售卖购买”的物性生命。合成技术更是直接打造出一个死亡剧场:被历史放逐的生命主体以死神之语言说“他者”之死,致使人类陷入“不死之死”的拓扑境遇。作者德里罗借小说中的“人体冷冻项目”表明自己对永生论调的消极看法和“向死而生”的生命自然终结论立场。
关键词:《零K》;影像技术;生物技术;合成技术;后人类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I106.4;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47-07
引用格式:王瑜镜,张春燕.《零K》中的后人类生命政治:从“向死而生”到“不死之死”[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47-53.
On Post-human Biopolitics in Zero K: From Living Towards Death to Undying Death
WANG Yu-jing, ZHANG Chun-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25, Sichuan)
Abstract: Don DeLillo's science fiction Zero K presents a post-human biopolitical landscape articulated by image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nd synthetic technology. Through human freezing program, life is fragmented and becomes the object reconstructed by multiple modern technologies. Among them, image technology focuses on correcting memory and virtual images on the screen invade the human brain, stripping memory of its digital position. Biotechnology consumes the body and life is reduced to a material life that is "produced for consumption and sold for purchase" within the commercial kingdom. Synthetic technology directly creates a theater of death: the subject of life exiled from history speaks in the language of death about the death of the "other", which leads human beings into a topological situation of death without death. The author DeLillo uses the human freezing program in the novel to express his negative view on the argument of immortality and his position on the natural finality of life which is to "live to the death".
Key words: Zero K; image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synthetic technology; post-human biopolitics
《零K》(Zero K)是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于2016年出版的科幻小说。该作品呼应当今数字媒体、基因改造和人类永生等热点话题,以“‘我’认知中的人体冷冻项目”作为主要叙事动力勾画出集影像技术、生物技术和人机合成技术于一体的后人类生存图景。在后人类视域下,对该作品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之主体性[1-3]、科技带来的物化及异化问题[4-5]与对生死概念的重新界定[6-7]等。事实上,对生死界限的再界定是生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因为生命政治关注生命、生活和生存方式(life, living and ways of living)[8]。通过探讨生存的逻辑(the logic of living)[9]进而探讨后人类时代的人类生存境遇,正是德里罗在《零K》中着意关注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0]24认为,生命政治肩负着对生命进行“监视、干预、扶植、优化、评估、调节和矫正”的重任。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1]116-117认为,“类似于祭祀仪式的实践以排除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拓扑空间”,这个空间则是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础。尼古拉斯·罗斯(Nicholas Rose)[12]3的“分子生命政治”更是将生命解读为“人类与非人类跨物种的普遍生命力”。也就是说,三人都认同如下观点,即生命可以被技术(或某种特定过程)干预和设计。这与德里罗在小说中极力呈现的吊诡生命过程是极为契合的。本文认为,在小说《零K》中,记忆、身体与死亡作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载体,全然落入技术的牢笼。生命成为被干预与设计的对象,其结果是记忆以矫正之名被影像技术篡改、身体以优化之名被生物技术消费,死亡以永生之名被合成技术制造。
一、影像技术矫正记忆
在小说中名为“聚合”的多层建筑内,“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巨幅电子荧幕。它们在走廊里出现,然后消失在天花板里[13]68。需要说明的是,这块屏幕是在这一层除墙壁和“后面什么都没有”的门之外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屏幕起初一片纯白,但突然间播放起剪辑好的一段视频。这组视频展现了“聚合”外世界的失控状况:狂热的信徒看到同伴已被熊熊大火包裹而急不可耐地擦燃火柴;灭火飞机在烧焦的树梢上洒下一片浓厚的化学烟雾;巨大的海浪冲垮桥梁和灯塔;灰烬和熔岩从地壳开口处喷发而出;人们戴着口罩抵御空气中的病毒,目光呆滞地向前走……
灾难片式的视觉冲击一遍遍在“我”脑海里“植入”外部世界的惨状。信仰破灭、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病毒肆虐等一系列现实都转化为屏幕里闪动的数帧。然而,外部世界固然有种种生存危机,但并不是生活的全貌。巨幅屏幕与所播放的灾难视频占据整个空间,人所见之处尽是危机四伏的外界惨状。如此一来,在一遍遍的视觉强化下,人对外部世界的记忆只剩恐慌与逃离。这与福柯在论述生命政治时提及的全景敞视装置对人的视觉规训如出一辙。在“我”所在的走廊里,这种规训进一步升级,中央区和周围区的物理间隔消失,“我”甚至可以触摸到屏幕。这是超越视觉承载、波及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的全方位规训。数媒技术导向的生命政治弥补了全景敞视装置过度依赖空间的劣势,并进一步拓展了规训的对象。另外,在占据所有空间和时间的屏幕前,人丧失了自主选择视域内所见之物的权利,因而被动“闭上眼”,按照无形的指令接收信息。这种数字规训已然内化为我将自己封闭的自我技术,甚至完全沉浸在摄像式的影像记忆中而不自知。其结果是,福柯口中由巡逻过程散布于敞视空间中“机警的监视目光”[14]211也悄然藏身于拥有上帝视角的监视器后。虽然全景敞视空间的物理结构被“敲零打碎”,但发挥的监视功效则更胜一筹。
大屏幕上迅速切换的影像合集是对世界的碎片化感知。通过将世界的完整图景打碎,并筛选出灾难等引发人们对外部世界恐慌的片段加以编辑,使外部世界成为灾难与末世的代名词。巨幅电子屏幕是外界信息的唯一输入源,而影像技术将外界世界构建成恐怖末日,其作用是以视觉符号暴力垄断信息输入,并促成现实向图像的转化。屏幕上播放的影像片段将发生在世界各地不同时段的灾难场景重新编辑,并将各自分离的多线程时间剪辑拼贴为相互耦合的单线程进程。影像技术通过塑造现实幻象入侵过去,进而矫正人类记忆,诱使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困于末日灾难,催生其加入“人体冷冻项目”的想法。
以屏幕上的影像片段为代表的信息接收看似是让人拥有了超级感官,即使人看到发生在自身时空体之外的事,但实则是将信息筛选过滤,有选择性和目标性地让人的感官系统接收过滤后的符码,迫使人保留一种残缺的感官。
感官残缺进一步导致意识与认知的模糊,最后使得意义落入无主之地,这集中体现在意识融合的吊诡事件中。由于不与人接触,“我”的意识发生恍惚,竟在自己无窗的小房间里闭眼冥想时看到了继母紧闭双眼的样子。“闭眼”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自我封闭的一种形式,即过滤外界输入的一切信息,这与那块巨大显示屏运作的逻辑如出一辙。另外,在继母的临“终”遗言中,她不断提到记忆里“某天淋浴间里浴帘上缓缓滑落的一滴水”,而如她所言,“那一刻本该被遗忘。”[13]14正是媒体技术入侵人的记忆,使得“我”与继母意识融合,使得“我为那滴水赋予了一种生命。我把它弄活了,把它变成了动画。”[13]13本该模糊甚至被遗忘的那滴水,幻化成巨型屏幕上静音的影像,成为一种数字记忆般的存在。继母的记忆被高清化,恰如高清慢镜头下呈现的影像映射在“我”的意识中。显然,这是一种感官过载。看似高清的记忆实则前置出一种失焦的无解之境:“我”在意识里看到的那滴水究竟是哪一天的哪一滴水?由于在人真实的视觉范围和记忆范围内,不可能精确储存某天的某一滴水,因而这种由过载感官承载的记忆将意义推入一个无主之地。
同样陷入无主之地的还有“漂浮的能指”与“延异的所指”。较为典型的是,“我”只知道“聚合楼”位于中东的某片沙漠,但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即使询问作为该项目负责人的父亲“我们”究竟在哪儿时,也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答案。父亲说,“离‘聚合’最近的大城市是比什凯克,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第二近的城市是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的前首都,哈萨克斯坦现在的首都是阿斯塔纳。”[13]22父亲的回答看似呈环状指向位于中心的终极答案,但却一步步走向答案场域的边缘。即使父亲做出详尽解释,但最精确的描述也只停留在“最近”的相关概念的指涉上,且越多的信息只会使回答越偏离最初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意义发生延异。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我”不懂什么是“卖鱼妇(fishwife)”而查字典追查其意义的事件里。在父母的争吵中,我听到父亲称母亲为“卖鱼妇”。“字典上说,这个词指粗俗的女人,泼妇。于是我又得去查泼妇(shrew)。字典将其解释为好骂人的女人,出自古英语里的地鼠。我又去查地鼠,结果字典又把我送回了泼妇。”[13]19在追查“卖鱼妇”一词的意义时,能指和所指之间相互转化,追求聚焦的过程反而造就了意义的失真。这是当下人类生活的缩影,即在后人类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数字媒体与影像技术不仅渗透了视觉领域,还占领了语言符号体系,切断意义能指与所指的一切关联,使人类陷入认知瘫痪。
迈克·费瑟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15]61认为,折中的符码、混和怪异的并置和没有规则的能指是后现代生活的一个窘境。德里罗借“刻意并置的灾难影片”与“指涉失灵的语言系统”言说技术能重组现实表象却无法触及内里意义的后现代窘境。超真实的虚拟影像入侵人类大脑,将记忆褫夺为影像技术的阵地,这是作者意图展现的第一重生命政治困局,即因超真而导致失真。由媒体技术摄取的后人类景观作为人类后现代境遇的一个生动侧写,展现了媒体技术对人的生命政治治理途径。媒体技术从视觉符号出发由感官入侵记忆,深入语言和思维系统改写个人体验以矫正记忆,达到塑造数字生命的目的。其结果是生命落入技术的牢笼,具有商品的可复制性,这将问题导向以身体为介质的生命物化进程。
二、生物技术消费身体
小说中,人体冷冻项目全面投入商业生产并形成规模。选择人体冷冻项目的每个人都必须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观看巨形屏幕里的灾难片、与即将进入冷冻舱的人共享意识、手术时间多次延期等。“我”虽然在挣扎中惊悟所看到的影像“全都是计算机生成的数字比特,数字代码,没有一样是真实的”[13]123,但同时也深知,“这走廊肯定都在受着监视,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正在静悄悄的房间里扫视着监控显示屏。” [13]18人作为监视器显示屏中一个被捕捉到的信号,悄然落入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口中“监视资本主义”的圈套,即“我们面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强大的新型资本主义欲望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关于资本积累的新逻辑”[16]14。正是监视资本主义视角让“我”清晰地知道,处于上帝视角的隐蔽摄像头能清晰捕捉各种真实的身体反应,并将其以数据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就这样,影像技术悄然向生物技术过渡,成为第二阶段生命政治开展的主要工具。
“聚合”楼里的第二部分可被称作展览,里面存放了一些有关冷冻项目的展品。在第一阶段媒体技术的矫正之后,参与者需参观第二阶段生物技术的成果。这项展览既展示成品,也毫不避讳地展示废品。“我”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走到一扇有把手的门前,“推开门,走进了大地、空气和天空之间。”[13]98“我似乎进入了自然的属地,花草树木、天空大地,然而却惊觉“这里的树皮、草叶和每一种花朵——上面好像全部都有一种涂层或是瓷釉。”[13]98然后是一个高大橡树下的身影:“他生下来就是这么苍老。他整个一生都在这条长凳上度过,他是这条长凳的一个永恒组成部分。”[13]107这个老人即是本项目获得成功的重要例证。他由自然生命创造,直到选择加入人体冷冻项目的那一刻又接受了生物技术的再造,成为一个永远都活成“这样”的人。他的身体就像涂了釉料的花草,无限逼真于真实生命,但却从质的角度有别于会死的生命,因为“这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身体,坐在一座玻璃钢的花园里。”[13]107随引导员的带领沿走廊而下,我随即进入一个“地下墓穴”,里面看到的即是废品。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该项目“先驱”的一些存在物。“一个没有面部特征的东西,赤裸身体,没有性别。” [13]107 “各种肤色的人,均匀地放置着,闭着眼睛,两臂交叉在胸前,双腿紧贴在一起,没有赘肉的迹象。” [13]210 “一群人像陷在一个大坑里,一大堆人体模型,扭作一团,身体赤裸,双臂伸出,头部可怕地扭曲着,头顶上光秃秃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人形纠缠在一起。” [13]109巨大地下坟墓里的展品将主人公拖入死亡剧场,展现了生命静止而时间流动的惊悚场景。
这是消费主义布下的陷阱。通过展现图像而售卖冷冻技术,运作整个项目的人在试探消费者的底线。本着“后果自负、买者当心”的售卖原则,“消费行业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进行试验的许可。”[15]序言x也许深处其中的人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以为只是偶然的机会,殊不知这是每一位进入这个实验室里的“顾客”都会被展示的图像景观。所有能看到和接触到的都是精心安排的预设,顾客看到任何一个事物的即时反应都会通过肢体呈现,被无孔不入的摄像头监视,人成为被数字信号捕捉的信息素。作为消费这项技术的消费者样本,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生成对应的电脑数据并录入样本库。电脑算法根据身体数据推演出下一位观展者的意愿,例如,哪些反应是表达出愿意、犹豫或不愿意的行为。如果不愿意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相关人员会调节周围环境而使愿意的可能性增加,促进购买或参与人体冷冻项目的意愿,从而最大程度达成消费。在人体冷冻的展演环节,身体成为一种展示样品,为潜在消费者展示人体冷冻项目的消费须知。在基于身体、面向消费的生命政治视域下,看似拥有审视权和选择权的消费者实则只是被试探底限的对象。
由身体特性样本采集得到的数据联通了身体与人口概念,具身肉体如数字媒体背后的代码一般成为抽象概念与数字符号,这一过程涵盖了人由个体到集体的完整领域。项目的成功率就如自然人口中的生存率、死亡率和致残率一样,成为一种参数,供前来消费的消费者考量。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技术全球化成为一种新殖民化形式,“它通过工具性将理性强加到各处”[15]序言xvii。小说中,人体冷冻项目让身处纽约的富豪前往中东沙漠,这表明技术打破了原有地理界限,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暂时存于技术装置的一个“座架”上,它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持存物。人体冷冻项目恰似新殖民化的一种外显方式,它没有既定的殖民宗主国和对象国,而演变成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现代性对人展开的生命政治性掠夺,即控制出生率、死亡率,并让这一数值吻合冷冻生物技术演化的速度。
至此,在后现代消费主义语境下,福柯口中基于出生率、死亡率等稳定常数作为实践依据、面向人口概念的生命政治转型为消费身体本身的身体政治。“科学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更加小心,甚至放宽了安全标准的管制”[15]102-103,这使人类走向一种人类世灾难。人类世是一个由人类对地球的干预所定义的地质纪元,其标志是人类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不可降解、无法自然消失,例如微塑料和微碳。当人本身成为一种污染和垃圾时,人类该走向何处?德里罗借地下坟墓中的废品景观呈现与面对以废弃物形式出现的身体废品时“我”的反应,向读者抛出了一个“人类世”式问题,即迈克·费瑟斯通所谓的“新的发现和发明必然会带来益处,任何有害的影响都会在以后被发现和解决。这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思维方式么?”[15]序言x
另外,生物技术使对生物生命性负责的责任主体由政府和医疗机构转到个人,即“管理自己的事物,谨慎地着眼于未来自身获得的安全。”[12]4在后人类时代,个体获得授权,以第一责任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影响人类种群的各项事物,而之前通常都是国家政府机构掌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物样本和基因库。个体获得了擅自改变种群样本库的权力,这先天导致安全标准的降低。自然生命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受到外力侵扰并做出一定的身体反应,由于这种侵扰意味着不“安全”的状况,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生命走向某种无序。简言之,生物技术看似通过大脑和身体给出不同的储存反应而尽可能提高安全系数,但实则是通过降低安全准则以迎合生产消费需求。
人体冷冻项目研发的初衷是防止标识自我的大脑连同腐朽的具身身体一起消失,延缓衰老进程,与疾病抢夺生命。但问题是,如果这些报废的身体被视作等同于制作过程中有瑕疵的零件,被随意丢弃在储物仓里,那么身体将成为一种产品,成为无异于生产车间内输送链条上的零部件。其结果是,以肉身存在为载体的生物技术转而成为谋杀精神自我的利器。因而,以消费身体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展现了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后人类时代,生命无法避免地被降格为生物技术产品,成为被囚禁于“生产消费、售卖购买”商业王国内的物性生命。
三、合成技术制造死亡
技术对人的铭刻已经向生命内部探进,小说中的合成技术实则是数媒技术与生物技术合力催生的“生命政治”高级形态,即在改造身体的生物基础上,将数字技术植入身体系统中。生命全方位受困于各项技术编织出的“美丽新世界”。李思[3]指出,该小说不遗余力地揭示将主体单纯还原为意识的做法的狂妄。事实上,这种狂妄性在于在“新世界”中,看似“我思”之精神力量全然覆盖“我在”之身体实践。如小说所述,线路完备、数字神经发达的大脑之下可以是任何一具躯体,且躯体仅发挥维持人体存在的支架作用。困于技术牢笼中的生命实则印证了“我思‘固’我在”的扭曲生命形态,这种扭曲具体体现为生命的同质化与时间的可编辑性。在二者的交织推进下,“向死而生”的自然生命规律被废止,人生生世世困于“不死之死”的美丽新世界。
如果说生物技术以身体资本的方式推动生产与消费,那么作为生物技术2.0版本的合成技术借商品的同质化生产实现了新型人类社会的“安全”。就新型人类的构造而言,具身身体完全成为可随意组装的机器,一如全球化背景下一台计算机的组装零件来自世界各国。在德里罗笔下的新世界中,大脑会保存在隔热容器里,“有时那些人的整个头部会被从身体上割下来分别存放,而大脑在里面完好无损。几十年后的某一天,这个脑袋会被嫁接到一个健康的纳米身体上。”[13]119大脑与身体的匹配机制本质上遵循着如下逻辑:即使组成一件成品的各元件零散分布,只要保证各个原件都严格按照生产图纸制作,并按组装流程进行拼装,就一定能组装出如效果图所示的最终成品。这是一种机械的、不考虑各个要素之间潜在相互作用的思维,而这种思维被用于人体的拼装时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即人成为没有个性的同质物:“是不是所有复活的生命都会被这个过程本身修剪得整整齐齐,全都变得一模一样呢?死的时候是人,重获新生时则成了形体相同的机器人。” [13]119
人类社会处于动态的运行模式中,而去个性化的同质生产则会使人处于相对静止的凝固时空内。这种相对静止无疑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完全不会有异常分子的出现。作者德里罗还着意在语言这一思维的产物上做文章,设想将语言植入新型人类系统中的场景:“他们将会讲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和其他语言没有任何联系。”[13]105“我们将会把它教给某些人,而其他人,那些已经处于冷冻保存状态中的人,我们则可以将它直接植入体内。”[13]105与其说是“教”,不如说是“交”,就像将一个存储信息的优盘插入计算机usb接口内,完成信息的转交和递交。被植入大脑的语言已经自成体系,不再有大脑加工和信息生成的环节,而是从信息库中直接调取数据并呈现。语言之死是零K世界中合成技术对主人公“我”的毁灭式打击,于是“我”急切给一切事物用自己的语言下定义:定义人、定义动物、定义被称为父亲的人。甚至在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的宣讲员并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是一种语言符号所指的“递交”,是死神之语。
合成技术在身体方面做到达成高度同质化,即选取最好的材料打造元身体,以植入相同语言模式的大脑作为元大脑,以批量生产的方式组合出一个个安全的个体,进而创造出“安全的人口”。这种安全等级全然超过了福柯口中以一个稳定常数为指标的安全性。如在人口层面,维持较低的患病率有益于一个族群的良性发展。较低的患病率并不是不得病,而是强调一种动态可控性。同时在统计学意义上,个体凝结为数字,即你患病与我患病不会在统计意义上产生差异,但会有其衍生影响(如隐性基因的遗传等)。对此,小说叙述者沉思道“我们将会以半机械人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崭新的宇宙里,独自一人,冻结在地下室里,在冷冻舱里。全部一个。”[13]54在合成技术的操纵下,不会有意外产生,只要确保一个,就能确保所有,即“一个即所有”。
面对“全部一个”的同质境遇,作者借“我”之口发出质疑:“如果没有其他人,难道你还存在吗?”[13]54这里的其他不仅强调他者数量性存在,更强调差异性存在。该种差异叩问了悬置于流逝的历史时间与静止的身体时间之间的新生命之存在性。阿甘本在讨论生命政治时从结构的角度剖析古希腊政治制度,发现“神圣人”以悬置的方式被排除性地纳入共同体实践中。神圣人(Homo Sacer)处于一种双重排除的拓扑结构中:因为它同时具有神圣性与污浊性的残留物[17] 。一方面,神圣人作为祭祀中被献祭给诸神的世俗之物,不被神圣世界纳入自己的共同体中。另一方面,神圣人作为从世俗世界割裂出的神圣化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像祭祀仪式前那样内在于世俗世界中。这种双重排除的拓扑学结构将神圣人悬置于一个例外空间中,即不归属于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任何一方,却因“被排除”的政治实践与二者均保持关联。
同理,在合成技术组装出的新型人类身上,流逝的历史时间与静止的身体时间同时存在,因而此种新型人类成为时间意义上的“神圣人”。身体和大脑被保存在不同的冷冻容器和保温桶中,于是出现了以下情况,即在生物性身体上,细胞、组织、器官不随时间流逝进行自然分裂、分化和衰退的过程,因而身体时间静止。同时,存于保温桶中的大脑能清晰记得冷冻期间自己的思考,所以历史时间流逝。正如“我”的继母玛蒂娜在成功参与该项目后在大脑中进行的撕扯。她一遍遍向自己确认“我是谁、我在哪、我活着吗、我死了吗”等哲学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意识与外在的历史时间同步,但冷冻的身体却因停止生命过程而处于静止。最终,那些从冷冻舱里出来的人将是非历史的人类,“他们将摆脱过去那些平直的,那些经过衰减的分分秒秒。”[13]105静止与流逝的时间在新型人类身上重组,将该项目的受试者永恒地悬置于时间的“例外状态”中,他们的生命成为一种处在历史外的生命,因而被历史放逐。
合成技术作为媒体技术和生物技术的2.0版本,本应打造拥有超级头脑和超级身体的超人,却通过直接促成语言之死、“他者”之死与时间之死打造出一座死亡之城。合成技术原本想将人改造成超人,既不摒弃人原本的自然属性,又可兼具数字机械等的数字属性,但是这种合成技术是对自身的一种裁剪。正如小说中承担顿悟功能的叙述者所言,后人类时代的人们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断精进,“我们已经赶在了我们自己的前面”[13]54,但除自己之外,周围空无一人。全部一人的死亡剧场彻底揭露后人类状况下生命政治造成的恶果:生命政治以增强获取优越生存境遇的能力为目标,却使人成为丧失生物性存在权利、游离于自然生命系统之外的“局外人”。
四、结语
“零K”世界所展示的是一幅由影像技术、生物技术与合成技术重塑、由“向死而生”迈向“不死之死”的人类生存警示图。小说亦展示了德里罗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即“当今世界人类面对着复杂的评估:是继续遵循自然选择的法则并将人类生命的不完善接纳为种群属性的内在部分,还是基于人类作为自主、能动的生物物种,通过技术性的自我优化创造更臻完美的生命形式?”[18]显然,德里罗倾向于前者。影像技术、生物技术和合成技术将人拆解,虽然其精准地从意识、身体及二者的结合三方面将人打造为具有超级感官、超级身体和超级意识的超人类,但人类也因此陷入“不死之死”的绝境。对死亡的恐惧固然会唤起人类对永生的渴望,但生命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它会终结。21世纪的生命政治关注人类不断增强的能力,即“控制、管理、制造、重塑作为活生生的人类具有的生存能力的能力”[12]4。将该小说置于生命政治视域内再做阐释,一方面有助于剖析作家德里罗对“不死神话”永生论的消极看法和其“向死而生”的生命自然终结论立场,另一方面亦可视为对科幻小说生命政治研究做出的脚注,对后续的科幻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GLAVANAKOVA A K. The age of humans meets posthumanism: reflections on Don DeLillo's zero K[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17,50(1):91-109.
[2] BARRETT L. "Radiance in dailiness": the uncanny ordinary in Don DeLillo's Zero K[J].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2018,42(1):106-123.
[3] 李思.“大脑中的幽灵生命”——论《K氏零度》的超人类主体及其限度[J].当代外国文学,2021,42(1):158-164.
[4] 孙杰娜.从景观生活到日常生活——景观社会理论视域下唐·德里罗的《K氏零度》[J].当代外国文学,2019,40(1):35-41.
[5] 叶华,朱新福.生命·生活·生态——《K氏零度》科技伦理反思的三重观照[J].当代外国文学,2021,42(2):5-12.
[6] VALA J L. DeLillo's poetics of survival: a case study[M]//ZUBECK J A. Don DeLillo after the millennium: currents and currenci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7:231-247.
[7] ASHMAN N. "Death itself shall be deathless":transrationalism and eternal death in Don DeLillo's Zero K[J].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2019,
60(3):300-310.
[8] LEO J R.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23:261.
[9] MARKS J. Michel foucault: biopolitics and biology[M]//MORTON S, BYGRAVE S. In foucault in the age of Terror: biopolitics and the defense of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88–105.
[10]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4.
[11] 吉奥乔·阿甘本.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16-117.
[12] 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13] 唐·德里罗.零K[M].靖振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14]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9:211.
[15]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61.
[16]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9:14.
[17] 张凯.西方文论关键词 神圣人[J].外国文学,2020(6):89-97.
[18] 林秀琴.当代生命技术与生命政治的联结——以罗斯生命政治论述为中心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8):62-68.
收稿日期:2024-07-13
作者简介:王瑜镜,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