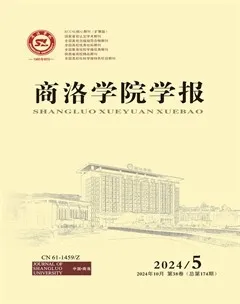OBE教育理念述论
2024-11-10唐叶焓
摘 要:OBE是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该理论最早可溯源至19世纪中叶Herbert Spencer提出的教育目标理论,其后又融合了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又经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即CBE,素质本位)和“精熟学习”理论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则由Spady率先提出。在四十余年的发展中,该理论对于“成果(outcome)”是以成绩还是以能力为标准,始终是存在争议的,包括其与goal、objective等近义词的相互关系。该理念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约是在2016年。就现有研究看,OBE教育理念在我国的研究似乎更注重“导向”而轻“成果”,尤其是对于“成果”多样性的鉴定,尚未有可视性和量化性的标准。这是OBE教育理念践行过程中面临的最为现实的挑战。
关键词:成果导向教育;学习成果;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77-07
引用格式:唐叶焓.OBE教育理念述论[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77-83.
A Discussion on OB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ANG Ye-han
(Faculty of Education, Xi'an Fanyi University, Xi'an 710105, Shaanxi)
Abstract: OBE stands for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mphasizing "outcomes" as the "guide." This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ory proposed by Herbert Spencer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t has since integrated utilitarianism and positivism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has evolved through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competence-based) and mastery learning theories. It was first proposed by Spady in the 1980s. Over fou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r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outcome" in this theory is based on grades or abilities, and ev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come" and its synonyms like "goal" and "objective." The concept began to receive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Chinese scholars around 2016. According to existing research, the study of OB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China seems to focus more on "guidance" rather than "outcome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outcomes", therexwOq1hIFuJEWFUIm/6fjoddQ97FRRPZsb0IaUtBYWPA= are no visible and quantifiable standards. This is the most realistic challenge facing the OB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Key words: outcom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practical exploration
OBE即Outcome-based Education之简称,又称之为“成果导向教育” “能力导向教育” “产出导向教育”。它是一种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注重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Spady[1]13率先提出了OBE教育理念。他在深入分析了时代背景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当时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市场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人口特征的变化及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演进,对原有的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在宏观社会背景的影响下,教育革新的理念应当是双重的:一方面,教育系统旨在培育具有扎实专业技能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应重视学生是否拥有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关键能力,这包括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主动和自发的终身学习习惯,以保证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会适应力。至90年代末,OBE教育理念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实践。该教育理念约在2016年前后也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并被作为工科类课程教育研究和改革的理论向导,其后逐渐延伸至其他的学科。特别是其教学设计和实施目标以学生所取得的顶峰成果为中心,反向设计课程并分阶段对其成果进行评价,尽可能地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学习阶段结束后的理想成果的教育理念,契合了我国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逐渐成为了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纵观OBE教育理念的探索与发展,无论是概念性的理论延展,还是成果性的实践应用,在守正创新的课程改革的新时代新要求下,都面临着实践性的应用成效和理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因此,对OBE教育理念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扼要回顾与反思是有必要的。
一、OBE教育理念的形成
OBE教育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性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格局基本形成,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后,引起了美国的深刻担忧,特别表现在嬉皮士文化对青年科技文化发展的反思与忧虑。美国的教育模式也因此受到了诸多批评,商业领袖和政治家随即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提出了培养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青年的口号[2]。随后,美国各州政府也开始在立法层面上明确学区必须实现的教育目标,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果,从而响应社会各界对教育改革的强烈要求[3]。这是OBE教育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这一理念的提出也是对教育改革呼吁的一种回应。与同时期的教育改革理论相比,OBE教育理念更强调个体独特性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双重符合,也由此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发展[4]。
虽然OBE教育理念的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Herbert Spencer [5]于1860年提出了教育目标的新概念。这是教育目标理论的原始形态,为其后的教育目标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至1924年,Herbert Spencer[5]在教育目标概念的基础上,强调了教学目标应以指导教学活动为核心,他将教育目标明确到了教学活动当中。再至1949年,泰勒[6]较为系统地强调了教育目标导向教学课程的理论。他通过探讨一系列基本问题明确了教育目标的确立与实现过程,涉及到了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经验的提供、经验的组织及目标实现的评估。可以说,泰勒为OBE教育理念之课程设计和评估提供了理论支点[7]。在此之后,布卢姆[8]及其团队依据目标分类法对教育目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为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个领域。其中,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对OBE的评估体系设计具有显著的理论指引作用[9]。如上有关教育目标的理论发展,不仅是教育目标概念的理性深化,而且是OBE教育理念的目标与认知、评估过程的理论基础。因而,OBE的核心原则根植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诚如Malan[10] 在总结OBE教育理念时所提出的综合性观点:其既是一种教育改革策略,又是一种教育哲学。这种哲学是在吸收并整合了历史上多种教育方法论精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体现了一种包容性的教育理念,旨在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教育体系。
教育目标的概念与理论的演进,为OBE教育理念的诞生、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Malan[10] 所定位的教育“哲学”看,OBE教育理念的哲学渊源与19世纪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演变密不可分。大致说来,这一演变历程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前,理性主义是高等教育流行的哲学思想,重点是培养逻辑思考与辩论的个体并以“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为教育目标。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特别是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兴盛后,高等教育的目标也随之转向培养有实际效用的个体,以及重点突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实用功能。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初以来,由功利主义向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转变之际,以杜威[11]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探索实践与经验导向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模式:反对将知识视为与客观世界脱节的抽象概念,主张知识应作为促进个体经验成长的培养工具;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计,注重学习内容与学习者兴趣和需求的契合度[12]。可以说,OBE教育理念从教育目标到教学认知、评估再到注重成果的导向,正是基于从思辨哲学向分析哲学的转向,特别是由功利主义向实用主义(或者说实验哲学)的转向。因此,OBE教育理念的发展是以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尤其是哲学观念的演进与转向。这对于其从目标概念向教学过程转变,以及教学评估和成果导向渐进性完成至较为全面地考量现代教育,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和意义。
OBE与CBE教育理念也是有关联的。所谓CBE即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也即“素质本位”教育。其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CBE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应用能力。英文是“competency”,意指有效完成任务的能力。虽然学者对“competency”所引申的教育理念内涵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但CBE教育理念的理论框架建构为OBE教育理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引导[2]。如Malan[10]指出,CBE教育理念的六种关键要素对OBE教育理念的系统发展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包括对学生技能掌握的明确规定与评估、灵活的学习时间框架、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标准化的成果评估、学习成果的认证及个性化的学习指导方案是OBE教育理念的重要指标。
除CBE教育理念之外,同时起源的“精熟(掌握)学习”(Mastery Learning)也被OBE教育理念所借鉴。“精熟(掌握)学习”作为20世纪60年代教育领域的另一种学习方式的创新,是由Bloom[13]提出来的。该理论是以核心假设为前提展开研究的:在明确学习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提供充足的学习时间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让学生达到熟练掌握学习内容的教育方式。通过强调学习结果的实现,精熟学习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教育评价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促进了教育实践向更加注重学习成效的方向发展[14]。“精熟学习”理论对学习目标的明确和对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视,为OBE教育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方法。
二、OBE教育理念的理论内涵
正是基于上述哲学思想与相关教育理念的奠基和发展,Spady[1]13率先提出了OBE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成果导向教育意味着,围绕所有学生在学习过程结束后能够成功做到的关键,来清晰明确地聚焦和组织教育体制中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首先要对学生能够做到什么有一个清晰的画面,然后组织课程、教学和评估来确保这个学习最终能够实现。”随后,Spady[1]19又对OBE教育理念的实践,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一是OBE教育理念的体系,务必确立一整套较为明确的学习和成果目标。这是OBE教育理念实践系统设计、运作的理论核心所在。其二是OBE教育理念的条件,务必创造条件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在各自适宜的步调下达成这些学习成果。这是OBE教育理念实践系统能够实施的前提核心所在。需要指出的是,Spady[1]10对“所有学生”的强调并非是单纯地回应对教育改革的呼吁,而是对OBE教育理念服务于受教育者甚至是服务于社会的教育目标概念深思熟虑后的回答。
在Spady[1]提出OBE教育理念之后的四十余年间,国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与探索。从理论的角度,对“成果导向教育”到底是什么及其含义给出了具有差异性的界定;从实践的角度,以“成果导向教育”命名的项目在方法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也有一些教育改革项目虽然采取了相同的方法,却依然在“成果导向”这一概念的定义方面有不同的理解[15]。如Malan[10]通过对成果导向教育的溯源及其视角下的教育模式的分析,将成果导向教育定义为一种教育模式(Educational Model)这一模式从过去的教育方法中吸取了精华的部分,将其融入到新的教育系统中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再如Borsoto[16]认为“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方法或者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确定好学生应该学习的预期结果,并以此来设计整个教学流程。Harden[17]在研究“成果导向教育”对医疗系统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时,倾向于将“成果导向教育”看作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不论在进行课程设置或者学校的系统设置时,都应将这一思维模式贯彻其中。因而,“成果导向教育”是一个在概念上易于理解,但在确切定义内涵时颇具挑战性的教学理念。尽管如此,其实施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确保所有学习者在完成学习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必要任务后,能够实现预期的学习成果,从而确保学习阶段中及学习阶段结束后的持续性成效。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在于其能否包容并激励学生以个性化的进度实现个人成就。因此,OBE教育理念的“导向”与“成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界阐释其理论内涵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何在实施成果导向教育的过程中,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充分发挥其获得成就的潜力,成为教育改革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这种对教育平等和个性化成就的追求,不仅是对教育公平的体现,也是对教育质量的不懈探索。据笔者观察并结合上述学者对OBE教育理念的认识,其理论性的研究和探索集中在了“成果(outcome)”概念及其“别名”之内涵的界定方面。
(一)“成果(outcome)”概念的界定
Spady[1]12对“什么是成果(outcome)”进行了初步阐释,并讨论了“成果”概念的内涵,大致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教育系统中如何明确“成果”、如今的“成果”和过去学校对学生的期待之间的异同,以及这样的“成果”是否具有现实性等问题。就此来说,Spady[1]13将“成果”的内涵界定为:在重要的学习经历结束后,我们想让学生展现出来的清晰的明确的学习结果。这一结果强调的是学生能够将他们知道的或者学到的内容进行实际的应用,而不只是表现在想法、价值观、记忆等的内部心理过程。因而,OBE教育理念之“成果”可以说是能够反映学生成功地运用知识、想法、信息进行实践的行动或是表现力。换言之,用学习到的知识去做重要的事情是超过知道本身的重要步骤,而一个定义明确的“成果”概念的关键就是描述成果时的动词的准确使用,这些动词明确地描述了学生在学习结束后要执行的过程。
继Spady之后的Killen[18]将教育系统中的“成果”类型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成绩衡量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它包括:考试成绩、课程完成率、就业率等的指标性内容。第二类则不如前者,他将这类“成果”转述成具体教学问题。如学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及是否因教育而改变。较为明显的是,OBE教育理念之“成果”似乎倾向于第二类。在此基础上,Rao[19]又将教育“成果”作了进一步细化,约略归为三类:一是培养方案的成果(Program Outcomes),这类成果一般是由学校统一定义的,并不由某一类学科而限定,从更广义的角度可以将这种成果理解为是世界各地教育的统一成果理念。如美国的全美学院及大学联会(AACU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将各校的培养成果分为批判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有效沟通、全球视野等。二是培养方案具体成果(Program Specific Outcomes),这主要是指不同专业及课程的成果。三是课程成果(Course Outcomes),这主要是指每一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做到的事情。这类“成果”需要通过特定的、可测量的动词予以明确,以保证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够进行成果展示。因此,教育“成果”的界定,不一定是指教学结果或者说效果,也可以是指教学过程中相对难以量化的学生表现行为。
(二)“成果(outcome)”相关别名的界定
OBE教育理念之“成果”即英文outcome,但与之相类的还有goal、objective等近义词,因而有必要界定它们在英文和教育语境中的应用场景,以便于我们准确把握OBE教育理念之“成果”的核心要义。
就教育语境而言,英文“goal”指代的是相对较为宏观的、总体性的教育目标,其为课程或学习提供相对宽泛的方向性。这种目标就定义其更多地是指教育者期望学生能够达到的“成果”或者说效果。但它的语义重心并不在于详细地说明学生应该怎样预期“成果”的方法或则是过程,同时其本身并不可以作为直接评估学习成效的主要依据[15]。我国学者多将“goal”理解为阶段性的教育培养目标,语义重心在于其指导教育活动的长远愿景。
相比较于goal,教育语境下的“objective”似乎更侧重于具体的、可衡量的学习或者说教学目标。较早提出这种概念的是泰勒[6],他着重强调了教育目的应转化为明确的学习者行为目标的观点,并使用“objective”以描述教师和学生的具体行动,以及预期的学习过程,通常包含行为、条件和标准等核心要素。事实上,由于其表述的复杂性,导致“objective”所要表达的意味并未完全达到预期设想。可以说,尽管泰勒[6]最初提出的目标理论与“成果”概念极其相似,但“objective”的含义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变得狭窄,其更多地被限定在具体的课程目标设置中。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Spady[1]60在表述OBE教育理念之“成果”时使用了“Outcome”一词。相对而言,Outcome的语义范围广于goal、objective。其不仅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做到的预期目标,同时也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结束之后应该能够达到的预期成(效)果,还可以强调更为广泛的学生的表现能力,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课程所包含的特定知识技能。反而言之,OBE教育理念对于具体课程的知识技能应该是围绕成果而发展的[12]。再者,“objective(目标)”和“outcome(成果)”必要时也可以互换使用,它们均与学习结果和教育目的有关联。这也为理解和使用OBE教育理念之“成果”提出了要求,即实践“成果”时应对objective、outcome、goal的教育理念“导向”有所区分,以保障“成果”导向与“目标”导向的各司其职。否则,OBE教育理念的“成果”导向很容易走向“目标”导向。
三、OBE教育理念的实践探索
Spady[1]13明确提出OBE教育理念后,其成果教育导向便作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点理念予以实施和实践。先后在肯塔基、密歇根、宾州、华盛顿等地展开了实验。Furman[20]较早关注了OBE教育理念在纽约约翰逊市的实践路径。该市在OBE 理念提出后不久便研发了Outcomes-driven development model,简称为ODDM,即“成果驱动发展模式”。这可以说是OBE教育理念向教育实践模型的过渡类型。以成果导向为核心理念,结合具体实际,提出了“14步”的课程教学实践,包括对学生进行预备知识评估、提供补救教学、进行全班教学、引导实践、持续的形成性评估来评价学生对单元内容的掌握情况、对于已经掌握单元内容的学生提供拓展活动、对未掌握的学生提供补救措施等。在总结性评估当中,学生根据是否掌握了单元目标被“认证”为已掌握或未完成单元,整个课程被重新设计为支持成果的“连贯的、主题化的”课程和单元。与此同时,ODDM还要求学校明确定义学生在完成课程时应达到的成果。这些成果应面向未来,旨在为学生在复杂、具有挑战性、高科技的未来取得成功做好准备。这一初步的实践模式为后续其他美国其他地区学校开展教育改革给予了重要的参考及实践范本。这种类型至今依然是亚利桑那州使用的主要教育模式。
OBE教育理念在美国中小学教育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引起了高等教育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兴趣。特别是在工程教育领域,其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应用OBE理论的范本。如美国工程与技术教育认证组织(ABET)自1995年起采纳OBE理念,推出EC2000工程课程认证计划,引领了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变革。《华盛顿协议》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南非等,亦相继采纳了基于成果的认证模式,应用于本科工程教育。该协议明确了工程专业需达成的四个层级成果:项目成果、课程学习成果、章节学习成果、章节学习小节成果,并从十二个维度规定了工程毕业生应展现的成果。
Volkwein等[21]率先研究了OBE教育理念在高校工程专业评估中的运用。2004年,他们开展的EC2000研究,对学生学习成果、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影响,特别是政策如何提升学习成效相实践。研究表明,自ABET将认证重点转移至学生教育成果以来,工程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及评估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改进,学生学习成果亦得到提升。至2017年,已有20个国家加入《华盛顿协议》,共同推进工程教育的国际认证体系。
美国的医学领域也从1998年开始倡导高校进行基于成果导向的教育实践。研究生医学认证委员会和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商定了六项认证的成果,强调医学类院校的关注点应转为学生的学习经验结束后,不同类型的合格医生所需要具备的素质,而不仅是学生的学习过程。
Harden[17]较早在医学专业实践OBE教育理念。他不仅强调了其对培养医学专业优秀学生的重要性,而且规划了医学教育课程的培养框架,并要求课程设置严格遵循六个关键步骤:首先是明确学生需求的评估,其次是课程实施,然后是设定目标与目的,接着是识别问题与需求,之后是制定教育策略,最后是进行评估和反馈。同时,通过对这一模式实施效果的研究,Harden[22]提出了三种监测模型,分别用三种动物的名称来命名:鸵鸟(the ostrich)、孔雀(the peacock)和海狸(the beaver)。鸵鸟型研究者认为成果导向教育是一时的流行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不愿做出改变。孔雀型研究者虽会追随潮流,开发成果导向教育的方案,但往往仅停留在向评估者展示成果的层面,而未能真正落实这些理念。与此相反,海狸型研究者不仅会根据成果导向教育原则制定具体的学习成果,还会积极将这些成果与学生的毕业要求相结合,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细致的记录和整理。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是1916年成立的非盈利性的组织,虽然这一组织也并非官方认证机构,但是自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了工商管理及会计等商学院专业的权威认证机构,自2003年改变评价标准后,也是以成果评估作为核心,不断推进课程改革。不可否认,成果导向教育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欧盟各国为了促进高等院校间的交流,于1999年正式启动了博洛尼亚进程。
总体来看,OBE教育理念在工程教育和商业教育领域的实践较为深入。在一项对美国六所知名高校共建的“学术信息检索”平台中有关“成果导向教育”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工程教育和商业教育领域依然是“成果导向教育”的主要研究领域,因为较有研究价值的1 737篇论文中,有69.9%的论文与上述两个专业有关,实证性论文占了23.9%[23]。尽管这些实证性论文中对于OBE教育理念的实施框架有不同的标准,但在实施原则上依然保持一致。一是专注原则,要求教师对学习成果有清晰目标,并指导教学活动;二是扩大机会原则,强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机会;三是高期望原则,要求培养体系提升标准以激发学生潜能;四是反向设计原则,指导教师从预期的学习成果出发,逆向规划课程和教学活动。基于这些原则所设计的OBE实践体系帮助我国学者在进行理念实施时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认识。
四、OBE教育理念研究的问题与挑战
从Spady[1]13明确提出OBE教育理念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学者对其产生较为普遍的关注大约是在2016年。根据常志英等[24]利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成果导向教育”(OBE)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自2013年起,国内OBE研究逐渐增多,2014年文献量达25篇,2016年后年发表量超400篇。申天恩等[23]进一步分析了560余篇相关论文,发现92.8%聚焦于工程教育领域,且研究者常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OBE等同视之。相对而言,OBE教育理念在我国工程教育领域的研究较为成熟,而在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尚在初始阶段,还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效验证。
就OBE教育理念本身而言,作为一种外来的教育观念,如何能够贯彻落实在各专业、课程的建设及课程的改革中,还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教育改革的认知问题。尽管不少学者在认识到OBE理念后,对其表示认同和认可。但是,在实践中,为了避免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全面的客观审视和繁琐的系统重构,使得OBE教育理念流与一种口号式的教育观念或发文章的理论噱头,导致研究成果远见性不足,未能真正认识与体现OBE教育理念的核心原则和原理。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基于OBE理念的课程或教学改革时,需要对现有体系进行全面客观的审视,并以明确学习成果为主要探究问题,构建一个聚焦于学习成果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其次是教育成果方面。很多学者在实施OBE教育理念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教育成果。同时,教育成果应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这意味着教育成果的设计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社会发展趋势及学生个人发展的需求。如宾夕法尼亚州在推行OBE教育理念时,投入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与教育界及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沟通,以确定毕业生展现教育成果的可视性和量化性。可见仅依赖学校或者教师自身的力量,似乎很难对“成果”进行界定,教育成果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全员参与通过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来衡量。最后是OBE教育理念实施的系统性。在未有可视或可量化的成果时,无论是理论推介还是过程实践,都是较为系统的工程,不仅包括教职员工、学生,而且包括使用成果的企事业甚至行政单位,是否能够投入到建设当中。就这三方面来说,OBE教育理念的“成果”是其理论能否有效实践的关键因素。
就目前我国学者对OBE教育理念的研究来看,似乎关注更多的是其成果导向之“导向”:第一,成果导向教育目前在我国的研究是以工程学科为主,但是院校有本科和职院的区分,因此结合不同学校的学生背景进行成果的合理化是有必要的。第二,人文类专业在成果导向教育的实施中需要探索出文科类专业的核心能力,因为工程类专业与文科专业的性质差异,导致工程类的设计方案只能在人文学科方向成为参考,并不能完全一致。第三,教师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教师是直接进行课程教学的人员,教师首先应当明确教育的意义,理解育人的价值,从而将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融入教学,以帮助学生达到预期效果[25]。第四,对我国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深入了解,成果导向教育的理念是“人人都能成才”,同时,成果导向教育的定义关注点并非学生所学的东西,而是学生所能证明的他们已经学会的东西,也就是说,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需要被充分了解,而不应只停留在教师想让学生学什么,如果能够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明确学习成果,并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这也是成果导向教育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从中不难看出,对于OBE教育理念之成果导向,学者研究和实践的核心是以知识“导向”学生所学的问题,鲜有讨论不同学科或者专业培养人才的“成果”多样性界定问题。这可以说是当前OBE教育理念研究的实质性问题,也是面临的现实挑战。
参考文献:
[1] SPADY W G.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Arlington, V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1994.
[2] MORCKE A M, DORNAN T, EIKA B. Outcome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its origin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Adv in Health Sci Educ,2013,18:851-863.
[3] MCNEIR 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tools for restructuring[C].Oregon School Study Council Bulletin, 1993,36(8):1-29.
[4] 王贵成,夏玉颜,蔡锦超.成果导向教育模式及其借鉴[J].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12):17-19.
[5] SPENCER H.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M].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1879:130-140.
[6] 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施良方,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7.
[7] PRIDEAUX D.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from objectives to outcomes[J].Medical Education,2000,34(3):168-169.
[8]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M].罗黎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1-42.
[9] HARDEN R M. Outcome-based education: the future is today[J].Medical Teacher,2007,29(7):625-629.
[10] MALAN S P T. The 'new paradigm' of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in perspective[J].Journal of Family Ecology and Consumer Sciences,2000,28(1):22-28.
[11] 简·杜威.杜威传[M].单中惠,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22-23.
[12] ORTEGA R A A, ORTEGA-DELA R A. Educators' attitude towards outcomes-based educational approach in English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6,4(8):597-601.
[13] BLOOM B S. Learning for mastery[J].Evaluation Comment,1968,1(2):1-12.
[14] 周显鹏,俞佳君,黄翠萍.成果导向教育的理论渊源与发展应用[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3):83-90,113.
[15] WILLIS S, KISSANE B.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R].Education Department of Western Australia,1995.
[16] BORSOTO L D, LESCANO J D, MAQUIMOT N I, et al.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and usefulness of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in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an asian univers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Research, 2014,2(4):14-25.
[17] HARDEN R M, CROSBY J R, DAVIS M H. AMEE guide No.14: outcome-based education: part 1-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based education[J].Medical Teacher,1999,21(1):7-14.
[18] KILLEN R, HATTINGH S 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 learning in outcomes-based education[J].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4,18:72-86.
[19] RAO N J.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 outline[J].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2020,7(1):5-21.
[20] CHASE FURMAN G. Administrators' perceptions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 case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1995,9(6):32-42.
[21] VOLKWEIN J F, LATTUCA L R, TERENZINI P T, et al. Engineering 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EC2000[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004,20(3):318-328.
[22] HARDEN R M. Learning outcomes and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is there a difference[J].Med Teach,2002,24(2):151-155.
[23] 申天恩,夏重鑫.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概念内涵、理论溯源与发展态势[J].教育文化论坛,2021,13(4):49-54.
[24] 常志英,崔维淼.国内成果导向教育研究主题及脉络演进[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5):59-67.
[25] 丁玉红.我国成果导向教育研究综述[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4(3):133-134,137.
收稿日期:2024-07-09
作者简介:唐叶焓,女,陕西商州人,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