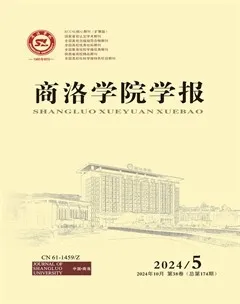论《秦腔》中的文学景观及其转化
2024-11-10靳转玉费团结
摘 要: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景观概念提供了文学解读的新视角。贾平凹对故乡棣花镇的书写,使其实现了从实体景观向虚拟景观清风街的转换。《秦腔》产生的影响又使虚拟景观清风街复现于现实,成为旅游景点。现实景观与文学景观的良性互动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彰显了文学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秦腔》;贾平凹;文学景观;棣花镇;清风街;现实景观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4)05-0016-05
引用格式:靳转玉,费团结.论《秦腔》中的文学景观及其转化[J].商洛学院学报,2024,38(5):16-20.
On Literary Landscap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Qin Opera
JIN Zhuan-yu, FEI Tuan-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Shaanx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landscape in literary geograph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Jia Pingwa transformed his hometown Dihua Town from physical landscape to virtual landscape Qingfeng Street by writing about it. The influence of Qin Opera makes the virtual landscape Qingfeng Street reappear in reality and become a tourist attraction or substantive literary landscap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realistic landscape and literary landscape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but also makes literature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 words: Qin Opera; Jia pingwa; literary landscape; Dihua Town; Qingfeng Street; realistic landscape
2005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出版,并于2008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自《秦腔》问世以来,学界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目前学界对于《秦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物形象、乡土叙事、生活流叙事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张继红等[1]认为,夏天义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代表,他的悲剧暗示了社会转型期农村所面临的巨大冲击。王春林[2]指出《秦腔》不论是叙述语言的选择,还是叙事的“去中心化”,或以傻子的视角展开叙述,都充分表达了作家对乡村世界凋蔽的无可奈何及为传统文化唱响的挽歌。吴义勤[3]认为,《秦腔》中,贾平凹对乡土的美学想象与文化想象都达到了极致,生活流式的叙述使乡村生活原本的藏污纳垢具有了“天然的美感”,在“密实”的叙述中,作家构建了自己的诗学及对乡村“中国之心”的独到发现与体认。欧阳光明[4]认为引生和狗尿苔“非理性的视角”及低下的“社会认知能力”有效还原了社会的“真相”,他们展示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沉沦。但目前还未有从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景观”层面解读《秦腔》的相关研究。文学景观一词源于地理学中的景观概念,曾大兴[5]认为,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文学景观作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角度。从文学景观视域探究贾平凹的《秦腔》,可以发现作品在唱响乡土挽歌的同时,又提供了一种新的乡村发展路径,由此可以看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现实价值。从文学景观视域解读《秦腔》,可开拓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一、现实对文学的影响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文学家的书写便带有了文学的色彩,由此成为文学景观。棣花镇原本就是兼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普通小镇,但因为贾平凹的书写,使其成为文学景观,具有了文学色彩。文学景观可分为实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拟性文学景观。其中,实体性文学景观指能够让现实中人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6]。
棣花镇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的西边,因盛产棠棣花而得名,它是丹江冲击而形成的小盆地,“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7]512棣花镇有一条主干道,为古时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因此棣花人习惯将其称为官路,街道两边的门面房相对而立。棣花地处陕南地区,民居多为独院,分为堂屋和厦屋,堂屋多为一明两暗的建筑样式。棣花镇既有塔、寺庙,又有钟楼、魁星楼和戏楼,民间进行宗教活动或祭祀活动的场所在棣花镇都可以找到。此地盛行风水之说,就连贾平凹自己也说:“在我的家乡,秦岭深处,小盆地被山层层包围,以前偏僻封闭,巫的氛围特别浓,可以说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巫的环境里,那里人信儒释道,更信万物有灵,什么神都敬……村里经常闹鬼,有各种精怪附上人体,村里没有医生,却有阴阳师,有了病,治病的方法很多,如火燎,锅盖,放血。”[8]棣花人都爱吼秦腔,逢年过节会请戏班子来村里唱。当然,棣花也像中国大部分乡镇一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由此,贾平凹对于故乡的未来深感茫然,他无法预知其发展前景,只能尽一个作家的绵薄之力将家乡的人事变迁记载下来,从而也使棣花镇的人文景观转换成了虚拟性文学景观,即“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6]。
《秦腔》中,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有名的老街,分东街中街和西街,中街两边都是门面房,房与房相对,夏家和白家坐落于东街和西街,他们是这两条街上的大户。清风街的民居也多为独院,房子分为堂屋和厦屋,堂屋为一明两暗的建筑样式,一般是长辈居住及用于会客,如夏天智常坐在中堂的藤椅上抽烟,厦屋则多为小辈居住,如梅花和孩子在厦屋看电视。清风街有老戏楼秦镜楼,戏楼的东边则是魁星阁,它的圆顶虽坏了,但翘檐和阁窗还是完好的,因为有魁星阁,所以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清风寺隔着土场和戏楼相对。土地庙在中街北巷口,庙里一直空着,君亭等人挖苦楝树时挖出了土地公土地婆的神像,将其放置在了庙里。在清风街,人们婚丧嫁娶都要来一段秦腔,夏风与白雪结婚时请了秦腔剧团,夏天智与夏风断绝关系时放的是《辕门斩子》,秦腔承载着清风街人的大喜与大悲。清风街人也相信风水之说,老人去世会请阴阳先生看“日子”,狗剩去世街上刮龙卷风说是他的鬼魂回来了。凡此种种,可以说清风街就是棣花镇的复现,贾平凹也说:“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7]518
棣花镇作为实体景观经过贾平凹的书写成为虚拟景观,这是作家在其现实地理景观之上又加入了自己对于故乡的特殊感情。他曾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7]517棣花作为普通小镇,经过短暂的繁荣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铁路和国道的修建迫使老街的人搬到了交通更为便利的国道旁,传统民居硬梁房也改成了二层小楼,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切都在向城市化靠拢。唯一衰败的只有那条老街,“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7]515-516曾经熟悉的老街不复存在,故乡也变得越来越陌生。由此使贾平凹产生了为故乡立碑的念头,他清楚地意识到,“故乡将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於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7]517所以作家写了《秦腔》,将棣花镇的人事变迁都移到了清风街,棣花镇的人文景观如民居、魁星楼、戏楼等在清风街也一一复现。
当然,棣花镇从实体景观转换成虚拟景观清风街,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棣花镇的复现。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虚构性,即使它取材于现实,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可能会对人物或事件等进行想象与嫁接,以满足作品情节与故事的需要。所以,即使“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真实,怎样的逼真,怎样的像模像样,说到底也是一种虚拟的真实,它充其量只可能与现实世界相当,却不可能与真实的现实世界等同。”[9]此外,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融入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即使小说是虚构的,但作家凝聚于其中的感情是真实的。因而不能将清风街完全等同于棣花镇。对于贾平凹来说,写《秦腔》是为了自己行将忘却的回忆,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只能尽一个作家的绵薄之力,将其过去的荣光记载下来,从而使清风街不同于棣花镇,也让虚拟景观迥异于现实景观。
二、文学对现实的影响
从实体景观棣花镇到虚拟景观清风街,充分说明了现实对文学的影响。而从某种角度来讲,文学又会影响现实,《秦腔》所产生的影响力使清风街复现,便充分说明了文学对现实的影响。
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10]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他指出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来源于现实,反过来又会影响现实。贾平凹写《秦腔》的初衷是为故乡立碑,但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使棣花从不知名小镇变成了文化景点,也让作家笔下的故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后来,商洛市投资修建了商於古道棣花文化旅游景区,围绕文化旅游,打造了以展示商於古道文化和贾平凹文学艺术为核心的文化景区。景区分为游客服务中心、宋金街商业区、贾平凹文学馆、清风街民俗文化体验区、生态农业观光区、商於古道文化演绎区等六部分。其中的清风街民俗文化体验区就是以《秦腔》中的清风街为原型建造的。这就使小说中的虚拟景观转换成了实体景观。清风街东面牌楼上有贾平凹亲笔写的楹联:“清风徐来,犹见商於汉唐柳;秦腔乍起,且醉棠棣宋金人。”街西面牌楼上则是白居易写的诗:“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花。”清风街全长200多米,街道两边是各种商铺。从东入口进入清风街,街头第一家商铺便是大清堂药铺,药铺门口还有赵宏生给小孩看病的雕塑,并附有解说牌:“赵宏生,贾平凹先生作品《秦腔》里的人物,清风街村民,帽盔柿子大个脑袋,赤脚医生,开大清堂药店,工于撰写楹联,清风街的文化能人。”清风街两边的商铺是各色小吃,小说中常出现的凉粉、浆水面、锅盔夹辣子等饮食在此处可以看到。走完清风街,走过二龙桥,便可以看到魁星楼和戏楼,它们都是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了修复。魁星楼为三层砖木结构,高18米,戏楼也为砖木结构,阶高四级,而戏楼对面则是二郎庙。此外,在贾平凹的故居前还有聚集在一起进行秦腔演唱的人物雕塑,旁边有解说牌:“秦腔,我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秦腔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为梆击节时发出‘桄桄’声)。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曾大兴[5]认为,虚拟景观和实体景观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虚拟景观可以变成实体景观,实体景观也可以变成虚拟景观。清风街是典型的虚拟景观实体化的产物。对于贾平凹来说,清风街的复现进一步证明了《秦腔》的成功,他创作了当代文学史上又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但未必可以证明清风街复现的成功。《秦腔》中清风街的地形呈“凵”状,东西两街的村子形状都像蝎子,夏家四兄弟、“白雪”家、“引生”家都坐落于此。而中街则有染坊、理发店、压面房、铁匠铺、裁衣店、纸扎房及饭店等各种商铺,土地庙就在中街北巷口。实体景观清风街则是一条200多米的长街,街道两边是各种饭馆,引生、夏天智、白雪等小说人物的家及“万家酒楼” “土地庙”等故事发生地均未出现,唯一出现的便是赵宏生的医馆。当然,魁星楼与戏楼得到了修复,但景区并没有刻意强调魁星楼和戏楼与小说的关系,甚至于在解说牌中也没有说明。也就是说,实体景观清风街虽是从《秦腔》中复现出来的,但与小说中的清风街差距甚大,它并没有按照小说中的空间布局来打造实体景观,整个景点并没有明确的景观规划与介绍,以佐证此景点是由虚拟文学景观转换成实体文学景观的。景区对实体景观清风街的设计规划是“清风街民俗文化体验区”,但整条街道上基本全是各种饭馆,民俗文化元素极少,即使小说以“秦腔”为名,且全书处处可见“秦腔”,但整个景点并未对秦腔大力弘扬,即使小说中多次提到了秦腔脸谱,景点也并无秦腔脸谱的讲解与售卖。也就是说,整个实体景观清风街的复现实质上就是借小说造势,希望借助作家贾平凹及《秦腔》的影响力来提升棣花文化旅游景区的知名度,吸引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前来旅游。换言之,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学景观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对整个景点的设计与规划脱离了小说文本,与小说的联系并不紧密。
实体景观清风街证明了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它来源于现实,又对现实产生了作用。虚拟景观的复现也充分说明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但如何处理文学景观的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无疑值得旅游开发者深思。
三、现实景观与文学景观的互动影响
文学景观是现实与文学互动的产物。唐晓峰[11]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制造出虚构的世界,有时,这种虚构的东西会跑到我们真实世界里来,产生新的文化地理内容。现实景观和文学景观的互动影响,使《秦腔》中的清风街复现于现实,使文学作品具有了物质实体,又带动了棣花的经济发展。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因作家作品的出名,从而使作家书写过的某个地方或文本中所描述的景观复现于现实成为文学景观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位于绍兴的咸亨酒店原本是鲁迅的堂叔周仲翔等人创办的一个普通小酒店,因为鲁迅在《孔乙己》《明天》等作品中多次提及,特别是在《孔乙己》中,它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因而也广为人知,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咸亨酒店重建,它与鲁迅纪念馆在同一条街上。咸亨酒店的空间布局基本就是以《孔乙己》中的场景为主来打造实体景观,在酒店门前就可以看到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台前还摆了桌椅。酒店里还挂着“三月六日,孔乙己欠十九钱”等字样。酒店重新开业后,吸引了众多的名人大家、文学爱好者前来观光旅游,一品鲁迅笔下的黄酒,他们也留下了不少的诗词画作,进一步提升了酒店的文化价值与知名度,也使咸亨酒店不仅只是酒店,也成为文学的殿堂,更是绍兴的一张旅游名片。又如,位于陕西蓝田县前卫镇的白鹿原影视城,即是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虚拟景观为原型而修建的实体文学景观。整个景点基本是依据小说建造的,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以及白鹿村里的祠堂、戏楼等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白嘉轩” “鹿子霖”等主要人物的家基本都转换成了实体景观。此外,《白鹿原》中的滋水县城也得到了复现,县城里的文昌阁、衙署、城隍庙等景观都一一转换成了实体景观,建筑样式也完全是仿古的。“白鹿原”的复现主要是为了影视拍摄,但它也兼具观光旅游、文化娱乐的功能,是一个综合性旅游区,它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景观,但却推进了小说影视化,影视化的《白鹿原》所产生的反响又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影响力及影视城的知名度。
复现的文学景观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资源,推进了文学与现实的良性互动。贾平凹写《秦腔》是为了缅怀故乡过去的荣光,同时也书写了以清风街为缩影的中国广大乡村的衰败,小说中秦腔的日渐式微,清风街的日益空心化,以及以夏天义夏天智为代表的老一辈的去世,都寓意着传统乡土中国的消亡。中国本是农业大国,所以清风街的衰落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唤起了国人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怀念。而2008年《秦腔》获茅盾文学奖又进一步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秦腔》产生的热烈反响也使普通小镇棣花广为人知。商洛也因势利导,修建文学景观清风街,打造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借助贾平凹的名气开发旅游资源,这使得只能依赖土地及外出打工的棣花人多了可以发展的其它副业,如住宿、饮食、交通经营等,带动了棣花的经济发展。
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使文本中的虚拟景观转换成了实体性文学景观,旅游开发既可以提升地方知名度,为其带来旅游收入,又可以使读者因文本景观的复现而形成与作家作品的精神互动,从而48IAnt8oigju/hMOiEgRZQ==获得物景观赏与精神追求的双重满足。但文学景观开发也存在一些很显著的问题——受众群体有限及如何兼具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等。除了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如《孔乙己》,受众面广且影响力持久外,现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品能达到鲁迅作品的高度,因而其它复现文学景观的受众面可能未必像咸亨酒店这般广泛,大部分复现文学景观的受众群体可能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或文学读者,其他游客也许不能体会景观丰富的文学内涵。这也就要求景点在建造开发过程中应适当增加对景观的相关介绍,如附解说牌进行介绍,以此增进普通读者对景点的认知。
复现文学景观作为文学实体化的产物,同时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这就要求建造者在开发过程中应努力建构起文学景观的空间布局与文本景观的多重联系,从而为读者打造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因为“我们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景观,目的不仅仅是要明确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从而开发那里的旅游资源。景观的魅力更多的是在于抒发作者心境,为故事的展开和人物塑造营造适当的环境,成为引起读者共鸣与神往的‘境’。”[12]实体文学景观建构得当的话,无疑可以使读者所期待的这种“境”成为现实。但由于实体景观清风街在建造过程中缺乏与文本的互动联系,使其缺乏文学性和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其旅游价值。这也为其它文学景观的开发提供了经验,文学景观的建造应基于文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因为文学景观重要的应是其文学价值,不能舍本逐末。
现实景观对作家产生影响,在其创作中转化成虚拟的文学景观。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又使虚拟文学景观复现于现实,由此完成了从实体景观到虚拟文学景观再到实体景观的一个有机转换。实体文学景观的出现也使读者与作家的沟通不再依赖于单一的文学文本,带给读者更多的阅读体验。
四、结语
文学景观作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下文学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秦腔》中清风街的复现证明了文学不再是虚幻的存在,它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作为新兴旅游资源的复现文学景观,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作家作品与读者的沟通提供了物质载体。目前,“文学景观”这一概念更多的应用于古典文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中,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景观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单就现当代文学来讲,作家笔下的文学景观俯拾皆是,如老舍笔下的茶馆、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古华笔下的芙蓉镇、莫言笔下的红高粱、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等。这些文学景观显示了浓郁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景,凝聚着作家独有的生命感受,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也显示现当代文学未来将会成为文学景观衍生的重镇。但如何使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景观如古典文学中的文学景观一般具有长久的现实生命力,这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继红,薛世昌.转型期农民、土地的深层隐喻——以贾平凹小说《秦腔》中夏天义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5(1):97-100,117.
[2] 王春林.乡村世界的凋蔽与传统文化的挽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6-64.
[3] 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秦腔》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6(4):74-82.
[4] 欧阳光明.论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视角[J].当代文坛,2012(4):33-36.
[5] 曾大兴.文学景观研究[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32(4):76-80,141.
[6] 曾大兴.论文学景观[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2):42-47.
[7] 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8] 贾平凹.文学与地理——在香港贾平凹文学作品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J].东吴学术,2016(3):22-25.
[9] 刘安海.文学虚构的再认识[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5(4):14-20,94.
[10]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
[11] 唐晓峰.文化地理学释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116.
[12] 王姮.虚构性景观的研究价值初探[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2(1):55-59,95.
收稿日期:2023-11-26
作者简介:靳转玉,女,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