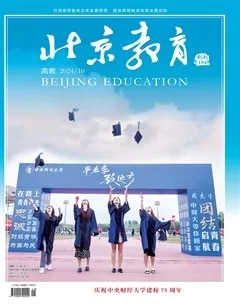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4-11-07张炜王帅徐沛鋆
摘 要: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创新要素的有序汇聚、创新要素的联动建设、创新要素的自组织运行三个阶段,即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动态调整,驱动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向新质生产力有序流动。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在宏观层面,应全面顶层设计融合式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在中观层面,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在微观层面,应完善产学研融通创新和重大现实场景驱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卡点、阻点。
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布局指导加快国家创新体系优化升级,形成优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有序流动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其核心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即“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
1.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从理论逻辑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会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系统当中的其他要素,引起联动反应,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驱动力。从历史逻辑看,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具有时空集聚的历史规律,科技创新尤其是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能够促进工具变革和效率提升,从而引发产业升级,是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变量。同时,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还具有模式塑造功能、资源整合功能、生态优化功能、风险防护功能等独特功能[3]。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科技创新,尤其强调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内在动力。
2.新质生产力以新型生产关系作为战略施力点和政策突破点。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通过全部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潜在的生产力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并由此产生新的生产力,因此建设全要素联动运行的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根基。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直接决定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其建设过程本质上是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的过程,通过创新要TPKGpbhNtI6sAtNNXUIu9A==素的创新性整合和配置,催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互动及质变,进而促进生产力跃迁至新质阶段。因此,建设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演进,应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施力点和政策突破点。
3.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核心建设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与新质生产力本质相通并耦合发展。一方面,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因素,同时新质生产力是面向先导性产业,重点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呈现载体,因此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新赛道、新动能和新优势,将加速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也伴随着生产要素跃升及创新性配置,能够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促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整体推进产业体系从传统走向现代,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更新迭代。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国家创新体系既包括各创新主体、环节、要素在创新环境中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空间维度,也包括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研发新产品,进而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的时间维度[4]。 这一体系的3Mc+o/4NGSiE3sJzkNoGzQ==效能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水平,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且与生产力动态匹配、持续演进。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逐步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5],其演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服务支撑新型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阶段。
1.创新要素的有序汇聚阶段(1978年—2012年)。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国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导下对科技体制进行系统化改革。这一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具有两条主线:一是促进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弱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特征,以市场促进创新资源汇聚。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以科技体制改革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87年,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系列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科研经费管理、科技人才激励等保障机制。二是重塑创新主体格局,促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市场化改革,培养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并开启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序章。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批科研院所转型或并入企业、具备独立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占比逐年提升。[6]从创新范式变革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参与到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中,并经历了“模仿创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自主创新”四种创新范式阶段。[7]由此可见,1978年至2012年,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市场化转轨与重塑的时期,各类创新要素实现有序汇聚,在改革开放初期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支撑了我国生产力飞跃式追赶。201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10,298亿元,发明专利申请授权21.71万件,分别比1995年增长28.5倍和63倍;并在高性能计算机、量子信息、载人航天、基因工程等众多领域取得巨大突破。三十五年间,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和10.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8%,为成功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市场和产业基础。
2.创新要素的联动建设阶段(2013年—202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国家创新体系改革全面发力。从生产关系变革来看,一方面,着力减轻体制机制束缚,以更为宽松的科技治理体系促进创新资源自由流动。[8]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以专业机构代替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具体项目;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为科研人员减轻“帽子”“牌子”束缚。另一方面,多元创新主体格局基本形成,创新系统内的主体多样性与特色优势并存。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行业协会等新型创新主体大量涌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从不到5万家激增到33万家,并且培育出华为、腾讯、阿里、字节跳动、中兴通讯等一批全球领先的创新型企业。这一阶段,自主创新成为主要创新范式,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021年,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时期,我国创新事业具有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并重,支撑并引领产业发展的特点。我国在太空、深海探测、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超级计算、第四代核电等技术领跑全球并赋能百业,在开辟新产业的同时,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成为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利器”。十年来,创新要素的联动建设显著促进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从1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2.2%提升到超过60%;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三十四位上升到第十一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6%;2021年,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40%。科技进步有助于培养质量和效益更高的新型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创新要素的自组织运行阶段(2022年以后)。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以促进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全面升级,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生产关系变革来看,新阶段的国家创新体系强调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融合”共同赋能新质生产力。[9]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向经济主战场”意味着产业链与创新链联动部署,促进科技与经济在各方面相互衔接、精准对接、耦合互动。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各级政府着力促进教育、科技、人才子系统协同发展,推动教育链、创新链和人才链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深度融合。创新要素的自组织运行是建设科技强国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2022年以来,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成就,如大飞机C919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行,国产大型邮轮制造实现“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等。2023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达到第十二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历了创新要素的有序汇聚、创新要素的联动建设、创新要素的自组织运行三个主要阶段,以服务支撑各个阶段的新型生产力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从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导科技创新活动到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提升;二是市场逐渐替代政府成为配置创新和生产要素的主要方式;三是国家创新体系内各创新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是生产力系统演化的内在动力;四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是产业实现后发追赶到超越追赶到领先发展的必要基础;五是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的最新形态。当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仍然存在人才供给羸弱、政府市场角色关系定位模糊、公众参与创新活动动力匮乏、前沿科技和基础科学领域竞争优势不足等问题,[10]阻碍了创新系统整体提质增效,因此亟须完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针对阻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瓶颈,结合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特征,我们提出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以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条实现路径:
1.宏观层面:全面顶层设计融合式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要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打造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法律保障”的政府角色。一是从政策制定方面逐渐转变为制定宏观发展方向,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和适度引导,赋予教育、科技、人才等子系统自行演化的充分空间。二是要建立政策衔接机制,不同部门联合发文,增强各类部门和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和贯通融合,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减少资源投入的重复和碎片化。三是应建立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创新评价体系,如将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高技术转化率、科研成果社会效益等指标的地位,并建立产学研用政多元化联合评价体系,同时评价体系应能够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动态变化进行灵活调整。[11]
2.中观层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中,密切协同产学研主体,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个子系统面向颠覆性技术进行提前布局。一方面,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加强创新型人才储备[12]。高校学科调整注重服务未来科技、经济、产业发展,既要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又要针对下一代技术的新发展方向,加强紧缺人才预警,提前进行学科布局。另一方面,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立跨学科、跨体制、跨领域的人才资源流动与使用机制。一是加强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与吸收引进,打造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队伍,营造自主可控的人才生态环境;二是健全多层次“揭榜挂帅”制度,激发各类人才及社会整体创新活力;三是探索先导产业领域的科技人才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和渠道,充分发挥人才“智脑”优势。
3.微观层面:全面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卡点、阻点。一方面,完善产学研融通创新和重大现实场景驱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市场化。一是完善市场化进程中知识产权相关制度,探索高校科技成果在企业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的新模式,建立充分保障双方权益的协议机制,降低企业转化高校科技成果的门槛和风险;二是构建多元创新主体面向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衔接多元主体间发展目标,鼓励高校将学术创业绩效纳入教师职称评审体系,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鼓励培养“双创”型的科学家。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颠覆性技术变革领域的资源投入,培育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重大战略性技术和产品攻关突破的创新生态。实施颠覆性技术变革行动, 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作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推动力,持续打造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强引擎”。
本文系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实践共同体的工程学习作用机理及其干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LZ22G030004)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2024-02-01)[2024-07-1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2]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3]张新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4(4):20-26.
[4]陈海若.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概念由来、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84-93.
[5]倪君,李瑞,梁正.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时代特征与治理逻辑[J].中国科技论坛,2023(10):1-10.
[6]贺俊,陶思宇.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70年[J].经济纵横,2019(10):64-73.
[7]于文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选择与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8(9):18-24.
[8]贺德方,汤富强,陈涛,等.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演进分析与若干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2):241-254.
[9]张志鑫,郑晓明,钱晨.“四链”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05-116.
[10]冯丽,杨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质增效的三维制度结构及其实施机制[J].学术探索,2023(3):37-45.
[11]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3-12.
[12]钟秉林.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的结构优化策略[J].北京教育(高教),2022(3):8.
(作者单位:张炜,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王帅、徐沛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卜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