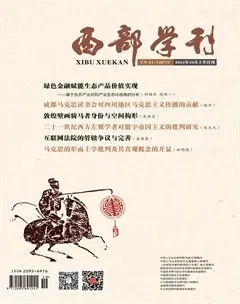从“一家两制”到“一家三制”:农民家庭城镇化的策略调整
2024-11-04王子愿
摘要:城镇化浪潮下,农村家庭作为城乡流动过程中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内外双重结构化困境。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农村家庭生产模式发生转变,即从“一家两制”转变为“一家三制”:男性在城市务工,女性在县城陪读,老人在农村务农。“一家三制”是农民家庭结合家庭发展需求、家庭经济需求和家庭伦理需求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家庭模式转变的实质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在生活城镇化阶段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让孙代在城市扎根而实行的家庭资源整合策略。
关键词:生活城镇化;“一家三制”;家计模式;进城陪读
中图分类号:C913.11;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9-0152-04
From “One Family, Two Systems” to “One Family, Three Systems”: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 Families
Wang Ziyuan
(School of Marxism,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 rural families, as the main undertakers of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mobility, are faced with a dual structural dilemma,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and to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family interests, the production mode of rural families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one family, two systems” to “one family, three systems”: men work in cities, women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studying in county towns, and the elderly work in rural areas as farmers. “One family, three systems” is a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peasant families in combination with family development needs, family economic needs and family ethical ne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models is essentially a family resource integration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peasa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stage of life urbaniz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 better life —allowing their grandchildren to take roots in cities.
Keywords: life urbanization; “one family, three systems”; 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 accompany studying in the city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1]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家庭观念、结构、功能随时代的发展发生着深刻变化。近几年,笔者在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中西部省区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家庭模呈现出“一家三制”样态:男性在城市务工,女性在县城陪读,老人在农村务农。回顾我国的家庭结构变迁与转型,每一次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农村家庭模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为了应对城镇化,农村家庭模式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运行机制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探索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既是我国的发展方向,也是现有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关注研究城镇化与农民家庭转型的关系,并涉及各个方面。学界关于家庭转型的研究主要以现代化理论为范式,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家庭转型朝着家庭结构核心化[2]、家庭关系离散化[3]、家庭伦理理性化[4]、家庭功能萎缩[5]几个方面进行。在我国家庭形态的研究方面,家庭现代化理论关注工业化、现代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力量对家庭性质的影响,但忽略了我国家庭转型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如转型中个体与家庭之间的文化互动、经济互动和政治互动。对此,学者们开始转向中国经验,在城市化进程中探讨具体的农民家庭是如何重组家庭结构和资源以应对发展压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来看家庭转型,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半城市化[6]到完全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农民进城的实践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从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或从浅度融入的就业城镇化阶段、加速融入的“半城市化”阶段和深度融入的生活城镇化阶段[7]。二是应对城市化转型而调试的具体家庭策略。我国农民家庭的转型具有复杂性和独特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点到点的线性转换,只有深入探讨农民家庭的内在运行机制,了解家庭内部代际互动、更替的再生产过程,才能理解农民家庭为应对城市化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而实行的灵活策略和弹性机制。当前,教育城镇化成为农民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学者从陪读来研究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
已有研究丰富了既有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揭示了我国家庭转型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存在两点不足。其一,研究主要集中于就业城镇化阶段,较少关注如何在城市扎根的生活城镇化阶段的问题,欠缺农民家庭进城之后的家庭分工与家庭转型的研究。其二,少量研究关注农民已进入到了生活城镇化阶段,并用“半工伴读”或“半城半乡”诠释其家庭分工与结构变化,但这些研究要么在分析城镇化策略,要么就是对陪读的单一研究,缺少教育如何内化到家庭并最终形成家庭转型的动力分析,也没有将家庭发展策略放在城镇化进程中进行解读。本文将生活城镇化阶段中西部地区农村出现的“一家三制”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分析农民家庭发展策略和家庭结构的演变机制。
二、“一家三制”的兴起及内涵
在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上,进城务工农民不是以个体的身份参与的,而是以家庭为行动单位,通过家庭策略来整合资源、规避风险,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城镇化的起步阶段,东中西部传统农民家庭先后开始发生裂变: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中老年继续在家务农。二十世纪末进入农村青壮劳动力多数进城就业的就业城镇化阶段,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呈现出“一家两制”的家庭生活模式:子代家庭共同外出务工,父代家庭在农村务农(兼在附近打工),照看未成年的孙代和年老的祖辈。2010年后进入农民家庭希望自己的后代在城市扎根的生活城镇化阶段。这一时期,有能力的农村家庭为达到婚龄的子女在家乡周边的城镇(主要是县城)购买房屋安家落户,但进城买房落户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要实现家庭生产生活的整体性进城必须融入以城市空间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这就需要有稳定的较高收入的正规就业。受教育程度和个人能力影响,父子两代已无法实现,他们希望通过孙代教育实现城市正规化就业,最终实现城市体面安居,这就对农民家庭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可以吸纳本地劳动力,农民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发育不足,就业机会缺乏且待遇有限,没有办法实现就地城镇化,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为此,中西部农民家庭调整了之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逐渐形成“以劳动力数量分工为基础的半城半乡”的生计模式,将家庭目标实现的希望由子代转向孙代,以孙代享受优质教育为核心来安排生计,家庭生活模式由“一家两制”变为“一家三制”:子代外出务工,父代留守农村,孙代在县城接受教育并由一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一般为儿媳)陪读。
可以说,“一家三制”是在2010年以后出现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一种新的农民家庭发展模式,以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家庭为运转主体组成三代直系家庭,以代际分工、性别分工进行劳动力分工的最优化配置,形成一个家庭三种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以期通过孙代的高质量教育来实现家庭的阶层流动和城镇化。相较于“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一家两制”,“以劳动力数量分工为基础的半城半乡”的一家三制具有明显不同的基本特征和建构逻辑。一是家庭结构弹性化,“一家三制”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应对小孩接受教育而产生的,一旦子家庭的孩子完成教育或者子家庭在城市能够立足,子家庭对母家庭的依赖度降低,“一家三制”就有可能往“一家两制”演变。二是家庭发展目标高质量化,原本维持型的发展目标已无法满足家庭城镇化的需求。三是家庭权力平等化,家庭内部不再有绝对的主导性权力,家庭关系趋于民主化。
三、农民家庭策略的调整机制
通过对“一家三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它本质上是多种因素驱动下的家庭劳动力重组,是对当前无法就地城镇化的弥补,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策略。一般来说,家庭策略是家庭成员主动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即家庭不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转型,而是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地应对转型社会压力与动力,并结合自己家庭的特性做出反应。从“一家两制”到“一家三制”正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结合发展需求、经济需求和伦理需求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一)发展目标与动态调整
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是制定家庭策略的关键,不仅影响家庭能动性的发挥,还影响着家庭发展能力的转化。不同的农民家庭其发展目标各有不同,进而会形成不同的家庭策略调控机制。整体来看,可以将家庭目标分为两大类,维持型目标和发展型目标[8]。
维持型的家庭发展目标,即实现基本的家庭再生产——家庭延续。在此目标下,子代结婚就是最为重要的家庭任务。当仅靠务农无法实现家庭发展目标时,以经济为导向的“一家两制”模式逐渐形成。随着城镇化阶段的变化,农民的家庭发展目标再次发生转变,不再满足于维持型发展目标,即在延续家庭之外,还要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和阶层跃升,从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当前阶段,农村家庭的发展型目标主要表现为农民的城市化,即农村家庭融入以城市空间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但进城买房落户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要实现家庭生产生活的整体性进城必须有稳定的较高收入的正规就业。这意味着以经济为导向的“一家两制”模式无法满足家庭发展的目标,农民家庭必须再次进行策略性调整,保证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孙代的教育分为幼儿园、小学、初学、高中四个阶段,农民家庭会根据子女的教育阶段及家庭经济能力的实际情况调整教育策略。为了小孩的教育,条件较好的农民家庭都已在城镇购房,陪读基本是从小开始。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陪读主要在初学和高中。随着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陪读越来越成为主流,陪读的性质由一开始的陪伴转变为教养。可以看到,在“一家三制”农民家庭中,年轻妇女是作为灵活的劳动力,是根据小孩的教育需求进行调配的,在完成小孩教育后重新回归市场作为完全劳动力。
(二)经济理性与家庭分工
家庭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存在的[9]。对于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在于对家庭劳动力的理性配置,从而最大化释放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广泛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而获取经济收入,老人因为身体状况、文化水平以及年龄等方面的因素而被全国劳动力市场所排斥,于是就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这是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家庭经济理性的策略性产物。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子代外出务工、经商获取货币性收入,老人留守在家从事简单的非正规就业以及照顾孙代。随着教育的重要程度和潜在要求不断提升,老人只能照顾无法教养孙代的问题凸显,这时年轻女性成为照顾孙代的最好选择。通过妇女陪读,农民家庭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获取经济收入,老人可以通过务农和就近务工继续创造社会价值,年轻女性既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在城镇非正规就业,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且还能保证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
农民家庭经济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也就是说农民不仅追求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同时还要维持家庭消费的最小化,从而保证正常继替和发展性目标的实现。在“一家两制”时,老人留在村中照顾孙代,可以自给自足,减少生活性的开支,家庭消费主要是建房和结婚。在“一家三制”时,陪读(特别是购房陪读)是农民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镇或县城购(租)房陪读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开支,除了购(租)房需要较多资金,日常生活支出也会远远高于乡村。儿子到城市里打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收入,儿媳在县城陪读的同时就近打工可补贴家用,留在村中的父代则会经常往返于城乡为陪读的亲属提供蔬菜、粮食等生活物资,以尽量减少在县城的日常生活开支。
(三)伦理价值与功能属性
“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传统家庭的核心精神[10]。在中国社会,家庭不仅是单一的经济或生活单位,更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农民家庭以家庭本位的伦理观为遵循,通过完成伦理责任实现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随着农村家庭的现代化,农民家庭的资源有限且发展压力大,农民只能通过代际合力来实现子代家庭的发展,家庭伦理主动嵌入了家庭发展目标,原本代际平衡的双向伦理责任逐渐转为父代对子代的单向伦理责任。可见在社会转型和家庭发展双重压力下,家庭伦理不得不跟随家庭发展目标的变化而转变。
虽然在现代性的形塑下,家庭伦理逐渐弱化,家庭功能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农民家庭模式的核心因素,但家庭伦理仍为家庭再生产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价值支撑。无论是“一家两制”还是“一家三制”,父代都没有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竭尽所能地为子代家庭的发展提供帮助,让子代能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及跨越式发展。在家庭再生KOeGbfgEinLfLeOnKXs1AllUBL3CUCB1ytJRL6jTvwA=产的过程中,以家庭发展目标为导向,必然导致父代伦理责任无限扩展,子代伦理反馈不断减弱。而家庭伦理的重构,则克服了这一过程中权力让渡和资源转移产生的伦理负担,实现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正当化。我国家庭的伦理价值是家庭功能得以维持的基调,家庭功能作为转型时期家庭制度的主导要素,除了保持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即传宗接代之外,还有促使家庭向上流动的美好期望。
四、结语
基于对农民家庭策略的考察,分析了农民城镇化的实践过程及运转机制,以此揭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如何通过家庭策略的调整来应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生活城镇化阶段,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面临着“进城”的巨大压力,需要对家庭进行经济、生活、伦理和责任等全方位的整合,进而形成代际合力,以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美好期望。“一家三制”正是应对社会变迁压力和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而实行的家庭资源整合策略。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家庭策略的调整更好地应对了城镇化进程,但无论是“一家两制”还是“一家三制”实质都存在家庭结构缺损、功能缺失的跨域生存现状,只有进行相应的社会制度改革才能有效健全农民工的家庭结构,提高务工农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16(2).
[2]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天津社会科学,1982(3):2-6.
[3]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J].古今农业,2007(4):1-3.
[4]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199-222,246.
[5]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J].浙江学刊,2005(2):202-209.
[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244.
[7]易卓,桂华.从“半工半耕”到“半城半乡”:农民城镇化的阶段与策略[J].江汉学术,2022(1):52-61.
[8]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6):75-84.
[9]吴飞.论“过日子”[J].社会学研究,2007(6):66-85,243.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0-81.
作者简介:王子愿(1989—),女,汉族,湖北荆门人,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政治文化。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