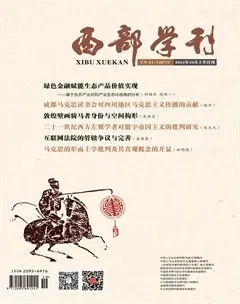从神话美学角度评析李贺之鬼神诗
2024-11-04黎书含
摘要:在李贺创作的二百余首诗歌中,鬼神诗占据了较大数量,是体现其幽冷瑰丽诗风的典型代表之作。李贺所作的鬼神诗许多都取材于远古先民创作的神话故事,一方面,这些神话作为创作素材进入到他的诗歌中,并经过重新演绎,丰富了李贺的诗歌题材,使得他的鬼神诗充满了神秘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神话背后凝聚的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进入诗人的精神之中,使其着眼于古往今来都在思考的生死之问,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构建出一个瑰丽奇幻的诗歌世界。
关键词:李贺;鬼神诗;神话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19-0118-04
An Analysis of Li He’s Ghosts and God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ological Aesthetics
Li Shuha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Abstract: Among the more than 200 poems written by Li He, ghosts and gods poems take up a large number, which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 dark and magnificent poetic style. Many of Li He’s ghosts and gods poems are based on ancient mythological stories created by ancient ancestors. On the one hand, these myths have entered his poems as creative materials and have been reinterpreted, enriching Li He’s poetic themes and making his ghosts and gods poems full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the primitive ancestors condensed behind the myth, has entered into the poet’s mind as a par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which has made him focus on the questions of life and death that have been pondered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gives play to his rich imagination to construct a magnificent and fantastic poetic world.
Keywords: Li He; ghosts and gods poems; mythological aesthetics
唐代诗人李贺一生坎坷曲折,身体衰弱,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原因使他在死亡的威压下时刻处于不安忧虑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贺所作诗歌对于生死、鬼神的关注与偏好较之其他诗人更为明显,神话色彩既作为素材点缀于诗歌之中,也因此成就了李贺的独特风格。
一、李贺鬼神诗中的神话之色
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唐代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人。古往今来,谈起李贺之诗,常用的评价总离不开奇幻、瑰丽、幽深等词,杜牧为其诗集所作之叙(《李长吉歌诗叙》)中,更是用了“虚荒诞幻”[1]来形容李贺的诗歌。虚荒诞幻的诗风,不仅与创作者李贺的人生际遇、创作主张相关,也与其所选取的题材有着紧密联系。
在李贺现存世的240余首作品中,提及鬼神的诗作有八十多首,占了较大的比例,亦是构建诗人独树一帜的诗风的重要部分。李贺将古代神话素材自然地运用到诗作之中,成就了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因而,本文意在发掘李贺鬼神诗中的神话之色,以及其与神话中原始审美心理体验的相似性,从新的角度体会其诗歌之美。同时,人们在找寻审美和艺术之源时,往往会追溯到神话、图腾和巫术,在荣格的人格理论中,这种远古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和精神,也暗藏着民族的审美精神之谜。故以神话美学视角来分析李贺的鬼神诗,也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审美之源起与流变。
作为原始先民的文化意识的载体,神话从未在历史中绝迹,而是在典籍、民间故事以及百姓的口耳相传中绵延不息。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得神话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与宝藏。
李贺在历史上被称为“诗鬼”“鬼仙”,除了有称赞其鬼才之意,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写作了许多带有鬼怪色彩的诗歌,例如《苏小小墓》《感讽五首》《金铜仙人辞汉歌》,等等。其中的精怪形象许多都源于神话传说,例如“狐”早在《山海经》中就已经脱离了普通的动物,具有灵气成为妖,“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2]7。李贺的《溪晚凉》《恼公》《神弦曲》等诗作中都出现了“狐”的形象,并继承了神话中“狐”有异能且恐怖的特点。李贺在创作有关鬼怪的诗歌时,保留了许多神话里的设定与色彩,这种延续性既是神话对人的塑造,亦是诗人对神话世界的诗意表达。李贺在诗作中赋予鬼怪形象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生命力,这使得他的鬼诗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感。
在神仙诗中,李贺对神话的引用更加丰富,《梦天》中的“老兔寒蟾泣天色”,《天上谣》中的“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都化用了嫦娥的神话故事。嫦娥曾出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淮南子·览冥训》中,前者说她是帝俊的妻子,后者称其为后羿的妻子,后世流传的故事和作品大多采用了后者的说法。《李凭箜篌引》中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则化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3]为了表现李凭高超的弹奏技艺,李贺进一步发挥,让箜篌发出的乐曲声震破了女娲所补之天,使得秋雨倾泄而下,借用并改造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以凸显李凭箜篌之乐的震撼力。如此运用神话典故,既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积淀,又使表达的意蕴更为神秘高远,给作品增添了一分绮丽的神话色彩。
除了借用神话,李贺在诗歌中还尝试组合创造新的神话。在《苦昼短》中,“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将《山海经》中“若木”与“烛龙”两个神话组合在一起。《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2]498关于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描述则是:“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2]499。因为两者均与太阳有关系,于是在李贺的诗中,用它们之间的关联将“若木”与“烛龙”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新的神话。李贺对于神话素材的使用并非直接照搬,而是根据诗歌创作的需要进行新的解读与组合。
追本溯源,李贺诗作对神鬼的关注,一部分原因在于其个人经历。李贺英年早逝,生前又是沉疴积身,相较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自身,投向想象的世界。正是因为李贺长期病痛缠身,他格外关注与生死相关的话题,借由对鬼怪神仙的想象,将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变为诗歌的创作,表现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了鬼神诗的独特色彩。
神话所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一个民族里的所有人,李贺像个孩子一样,用瑰丽的想象勾勒出他意识中的那个神秘的生死之境,他以人之身行走于自我和先民共同构建神鬼之梦中,试图找到自己的路。
二、神话美学视角下李贺鬼神诗的审美特征
神话美学,即古代先民用何种视角观察、看待世界,并以原始的艺术语言表现在神话之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构成了民族精神与记忆的重要部分。后来的人们继承前人留下来的宝藏,以不同的形式发扬它们,而原始的审美思维也就这样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
所谓传承,即流变之中也保留着相似之处:古人所关注的,也是今人所关注的;古人所思虑的,也是今人所思虑的;古人曾运用的手法,今人仍在使用。前文讨论的是李贺鬼神诗与古代神话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以神话美学的视角来分析,李贺鬼神诗呈现出两个主要的审美特征:生命的有限与超越,想象的创造力。
(一)生与死之论
李贺写鬼神诗,写的正是对生死问题的思考,生命如何以其有限性自处于无限的天地之间。这类诗歌在李贺的笔下,常常色彩幽暗、风格诡谲,营造出一种沉重幽绝的氛围,折射的亦是李贺生活中的现实一面。他用一种真实的、敏感的笔触描绘了自己眼中的生命体验,面对死亡和鬼怪,诗人没有刻画英雄般的无畏,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另一个世界正是如此神秘可怖,而自己的病体又使得他比普通人更早更近地看到了这一切。正因如此,时间、死亡与生命在其诗歌中是如此的真实可感。在《苏小小墓》中,死亡是“幽兰露,如啼眼”,是“冷翠烛,劳光彩”,诗人强调她在西陵下“风吹雨”等待时的凄苦,以及在鬼魂世界的孤独。冷、幽、暗的氛围透露出死亡的气息,但鬼和人一样,也是有情感和情绪的,诗歌在幽冷的意境中突出了哀愁之情,在无人的鬼之境极力塑造一个有情的鬼。虽然在情感上表现出焦虑恐惧,但诗人仍然选择了直面生死,他的鬼诗所描绘的人人死后都将去往的鬼之地,除了幽暗凄冷的氛围,仍然带有一丝人间的颜色。
有关人死后会成为鬼的想象,自上古便存在。《礼记·祭法》言:“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4]《墨子》中有杜伯死后化身成鬼,并射杀周宣王的故事。生命是有限的,面对未知的死亡,先民们想象构造出一个死后的世界来化解恐惧,这种思维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通过神话、传说慢慢烙印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崇义里滞雨》《示弟》《秋来》等多篇鬼诗都呈现出灰暗的情感与凄苦的氛围,如果说鬼诗是诗人现实经历的反映,刻画的是他对死亡的思考,表现的是幽暗凄冷的色调,那么神诗的风格便截然不同,更多表现了生的希望和期盼,从侧面反映出李贺的人生理想与希冀。
在畅想天上生活的《梦天》一篇中,前四句构建了一个美轮美奂、尽善尽美的天上月宫:“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云楼半开、月影朦胧的天宫中桂花飘香,不时还传来仙女漫步时鸾佩相碰的清脆之音。反观尘世,千年变更如走马,人世万物渺小而短暂。李贺对时间逝去不可追之规律认识得清楚透彻,故能写出“更变千年如走马”之句,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种种苦难,明白自身病痛、死亡之不可逆,才把希望寄托于神仙生活之中,用九天之上明丽的色彩和理想化的生活驱散真实世界的暗淡凄苦,让自己得到慰藉与解脱。但李贺并非要追求长生,相反,他写过不少批判神仙虚妄的诗歌,例如《苦昼短》中的“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浩歌》中“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这体现了李贺之神仙诗与其他人的“游仙诗”的不同之处,他描绘神仙世界时,并非将自我代入进去游仙,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和刻画,而且他在诗中常常怀疑神仙的存在。李贺借神仙世界来排解忧思,追求希望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清醒。
总体来看,李贺的鬼神诗表现出的时空意识、生命意识与古代神话思维中的审美传统是相互呼应的,神话为文学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资源。现实世界的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是线性的,具有不可逆性,人在时间面前无比渺小而短暂。然而,在诗歌艺术和神话传说中,时间变得立体起来,生命在其中巡回轮转,死亡只不过是新的起点,人、神、鬼都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相互转换。
古代先民在神话中描绘的和李贺在鬼神诗中想追求的那种“永恒”,并不是停滞不变的永恒,而是在不断运动,变换形态而前进的“永恒”。《山海经》北山经中,炎帝之女死后化为精卫鸟,衔草石填海;海外北经中,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大荒西经中更是有“颛顼死即复苏”[2]476。
换句话而言,虽然世间“更变千年如走马”,然而“沧海桑田”之后,或为人或为鬼或为神,不正是已经身在永恒之中了吗?万物终将归于尘土,而尘土又会构成万物,生命、世界正是由生生死死、变换不息的平衡而组成的。李贺鬼神诗中不只有其个人的生命意识,也暗含了神话时代关于生命观念的集体无意识。
(二)奇幻瑰丽的想象
除了对生死命题的思索,远古先民创作的神话还有一大重要的贡献: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们在探究审美意识与文学艺术的源头之时,都不免会追溯到神话,神话能够流传千年,深入民族的文化精神,其本身的故事自然是生动有趣的。无论是神话中各种神仙鬼怪,还是离奇的故事,都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虚构的作用。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既是一种能力技巧,也是一种先民通过神话留下来的原始思维和精神,代代流传,为民族之树的成长浇水施肥。
将中国神话与后世历代诸多文艺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即以意象塑造为核心的审美传统。意象性对中国审美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文艺创作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神话中独特的意象塑造方式通过审美意识等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文艺创作,使得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象尤其发达,促进了中华民族审美趣味、审美传统的形成。除了与对象有关,意象的形成与主体的想象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贺诗歌的境界幽深朦胧,使人遐思无穷,迷离恍惚,想象的世界奇幻丰富,意蕴多层,正是继承并发扬了源自远古先民创作的神话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构造出虚幻奇特的意象,提高了艺术的张力与审美的享受。
李贺诗作中的生动比喻即是其丰富想象力的体现。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忆君清泪如铅水”一句将思忆之泪比作铅水之暗淡沉重,借此,泪水有了格外的颜色与重量,巧妙地写出金铜仙人怀旧、惜别之痛。“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则将天地带入到人的主体之上,宣泄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对时间无情的感慨,含义多层,成为千古绝唱。在《梦天》中,诗人对月光的形容更是出奇,“老兔寒蟾泣天色”“玉轮轧露湿团光”,兔与蟾的泪水是对神话的联想发挥,“玉轮轧露”描绘的是明月飘过云雾的场景,展现了诗人想象之虚幻奇妙。还有《听颖师弹琴歌》中,称赞颖师美妙的琴声和高潮的技艺时,李贺以“双凤语”“敲水玉”来描绘琴声,将原本不可感的琴声变得可以想象,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李贺在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出一种反理性的美学倾向,有意打破客观9IKEyL3G5niVW93dUkZ1BQ==世界的固有面貌,用神话一般的笔触和个人审美经验构建出一个变形的世界。在描写水神、海神的作品中,他试图营造一个经过变形、折射的水世界,好比隔着波动的水面去观察世间。这须得依托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zYREr3DloXv4ScSNN6fSpw==无穷的想象力,才能在反映描摹对象的同时,依据诗人的主观意向与创作需求而做出调整改变,以求达到奇幻瑰丽的印象式呈现。
例如《帝子歌》一诗中,“凉风雁啼天在水”一下子就勾勒出一个颠倒错位的世界,诗人对于现实的失望与失落借由湘神与帝子的故事含蓄道来,脱去陈词俗调,将情绪变为色彩,成为绮丽想象与神话梦境的一部分。较之客体世界的有序与无限而言,诗歌世界的变形与颠倒正反映了主体意识的创造性,彰显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在意象表现上突出了李贺诗歌的神话色彩,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与精神震撼。
李贺的鬼神诗以强大的想象力,对生命的追问求索,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幻想与真实的界限,无限趋近远古神话中世界的模样。在这里,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一切看似光怪陆离,却正隐喻着人们就是在混沌中寻找自我与光明。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将自我的情感和认知对象化,促进审美意识的发生,同时也在审美体验中加强了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
三、结语
对李贺创作的鬼神诗进行美学研究,从其中的神话之色出发,发掘它们的审美特征,凸显李贺鬼神诗所蕴含的丰富的审美价值,为李贺诗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灰暗凄苦的鬼诗也罢,流光瑰丽的神诗也罢,李贺用他的生花妙笔勾勒出绮丽神秘的鬼神之境,为自己,也为更多的人搭建了一个精神的家园。李贺刻画梦却不沉迷于梦境,虽然他身体衰弱,但却一直深刻地思考并批判现实,正如神话背后是先民们蓬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李贺的鬼神诗传达出其精神的勃发与坚韧,引导着后来之人不断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贺.李贺诗歌集注[M].王琦,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
[2]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3]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479.
[4]郑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91.
作者简介:黎书含(2000—),女,汉族,重庆荣昌人,单位为长安大学,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