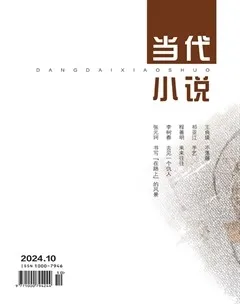丰溪三号(短篇小说)
2024-10-31杨婧
清晨,他醒后,恍惚了一番,没有觉察到往日那种黏人的灼热,反倒是曙光清透,朝阳照在高原上显得明亮清爽。在哪儿,他想不起来,也许是在路上。
外屋隐约传来脚步声。他依然闭着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那人的手脚因繁重的劳作而变了形。那人靠近他,看了看还在睡梦中的他,随着脚步声消失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也许很久,一种酸酸甜甜的气味把他唤醒了。他听到盘子被端上桌的声音,便迷迷糊糊起身,下地,走到外屋。桌上有一盘棕黄色的杂粮煎饼,一盘亮晶晶的土豆丝,一笸箩青白相间的小香葱,一碗黑乎乎的烧辣椒酱,两双筷子,桌子旁还有一位老人。
哦,是了,已经在家里了。
他洗了把脸,手掌托住一张煎饼,铺匀土豆丝,把蘸了辣椒酱的小香葱卷进去。辣酱里的香菜葱花还很鲜嫩,想来父亲是为了迎接他回家,临时腌制的。他咬下一口,一股久违的粗糙的辣感在口腔弥漫开来。这辣酱曾是父亲为哄他吃饭自创的:用明火将一把二荆条辣椒表面烧煳,捣成泥,再放上酱油葱花香菜。他就着这种辣酱,一顿可以吃下两碗饭。
窗外的阳光明亮,更显得屋内氛围凝重。父亲嘬着烟斗不言语,邱实有些无措。
父亲是他此行最大的反对者。邱实此刻不知如何开口,慌乱中忘记了当时是如何自己说服自己的。
父亲吐出一口灰蒙蒙的烟圈,说:“人往高处走,你不该回来。”邱实囫囵吞下口中的食物。父亲不等他回话,接着说:“你想歇就在家歇两周,然后回去上班。”
此刻,邱实所做的那些背景调查,包括农业供给侧改革、各项宏观利好政策等似乎统统站不住脚了。他有些讨好地对父亲说:“我也不是自己种地,我是带着大家种。”
老人不由分说地将烟斗在桌沿上敲了敲,桌子上的碗筷跟着跳动起来。等烟灰磕干净了,他又说:“两周。”
秋天的山村,空气中有种特别香甜的气味,尤其在熹微的晨光中,这种气味更加明显。这是从山林中溢出的混合了各种花草果木气味的芬芳。饭后,邱实走出家门打算四处看看。
村子并没有什么变化,比以往更安静了。
他走到一块岩石边,望向坡底那条废弃的石径。谁也看不出,那曾经是一条清澈的小河。离开小溪沟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日后竟会如此想念这条小河。
小时候,河里有鱼,岸边随处可以捡到鸭蛋。夏天,他躺在河里,随着水流从村头漂到村尾,鱼儿贴在身下游走,他的心绪随着头顶的白云悠然飘荡于群山之间。
后来,他在川西的大城市读书,毕业后又在开发区找到一份工作,每天跋涉在乌泱泱的人群之中,顺从且卖力。他的心里总有种异样的感觉,越融入都市中,这种感觉越明显。终于有一日,他想起来,自己曾是河里的一条鱼。
邱实的老姑正在小菜园里栽葱,抬头看见邱实从大门进来,指着拦猪圈的那方矮墙说:“今儿怎么不翻墙了?自打你会走路,从大门进这院子的次数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老姑说话时像是在敲一面铜锣,把圈里的猪吓了一跳。
邱实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子,亮出手里的笔记本,嘿嘿一笑,说:“公事嘛。”
老姑拿着两棵葱,走出菜园子时已经剥净葱皮,掐掉了葱头。她在围裙上蹭掉葱鼻涕,转身从里屋取出一袋鲜榛子。
这期间,老姑的嘴巴没有停下来,一直在试图找一个合适的词语夸奖邱实,却没有满意的。她的声音忽高忽低,一边说一边否定自己,于是院子里沸沸扬扬,像是有好几个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
老姑说:“你捯饬捯饬真是人模狗样。”又说:“唉,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那就是人五人六。这好像也不是个好词。总之一表人才。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最后,她在邱实身旁坐下,说:“我那大嫂子没福气啊,没看见她小子长大了的样子,真精神!”
邱实俯身,摘掉叶子取出榛子。用牙一嗑,满嘴清香。鲜榛子肉肥汁多,吃起来像在吮吸奶汁。
他老姑说:“我这里有啥缺啥你都知道,不用走访。”
邱实说:“我知道,啥也不缺,就缺个姑父。”
他老姑乐了,说:“邱实,你回来当村支书的事也不算是个小事,怎么不提前跟你老姑打声招呼呢?那天说新书记要来,是个没结婚的,我还特意打扮了去的。这事儿闹的。”
老姑接着说:“这些年呀,我就想再找老伴儿的话,怎么着也得弄个官太太当一当,可乡镇上的这些书记没一个死老婆的。”老姑双手一摊,好不遗憾的样子,“没人给我腾地儿,那就放宽点条件,最不济也得是个村支书吧?可现在——”老姑白一眼邱实,“不想啦。”
邱实在一旁笑得露出了牙花子。
老姑将小溪沟的人家唠了一遍。谁家有老人,老人得了什么病,是谁在伺候;谁家有孩子,上几年级了,难不难管教;谁家媳妇在城里做着保姆;谁家爷们已经当上了工头;谁家不用去了,屋塌了地荒了,不会再回来了。
老姑时不时把头扭向她话中人住所的方向,手里的活却一刻也没停。叶子一片片落下,飘到台阶下的一堆叶子里,榛果被老姑一粒粒攒在手里,然后一起装进塑料袋里。
老姑终于念叨完,停了一会儿,又看看邱实,问:“那你爸咋想?”
“咋想呢?”邱实收了笑容说,“不认可呗。”
老姑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想想也是,咱也能理解。你从小他就舍不得让你摸一把锄头,你高考考了三年,他供了你三年,就盼着你以后再也不用种地了。好赖考出去了,请了全村来吃酒席。你这样回来,这不相当于那啥嘛!”
老姑又问:“那你就非得回来?”
邱实低着头不说话。
成立合作社开会的那天,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村委空前热闹。座位不够,人们就把企划书垫在屁股下,坐在地上。
企划书上,合作社的目标定得很长远。十年之内,由现在的四十亩土地发展为二百四十亩,创建小溪沟的自主品牌,建立农业合作示范区。
来开会的这些人,邱实不是喊爷爷就是喊叔叔。整个小溪沟,论起来,大家都沾亲带故。邱实祖上随着闯关东的队伍迁徙至此,聚族而居,后与当地满蒙人家结亲,逐渐开枝散叶。邱实看着屋内屋外的乡亲,觉得他们长得有些像,一个个身材魁梧结实,脸上却带着一种不相称的卑微。邱实是长大之后才明白,他们是因为世代务农的艰难,渐渐地把怯懦守旧刻进了骨相。
那种怯懦和守旧也支配着邱实,此时就在作祟。邱实不想提远大的目标,他不敢。他能想象得到他们听到那远景时,联想到痴人说梦而露出的鄙夷的神情。光是这一点,他就无力招架。
邱实决定只讲眼前要做的事情。
“明年开春,我们用征集到的四十亩地种‘丰溪三号’。”
人们把正在唠的嗑搁下,没有听清的人相互询问了一下。很快,他们就统一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是在瞎闹,质问说:“有那么多亩产高的红薯,为什么偏偏种这个?”
“因为‘丰溪三号’味道最好。”
“再好吃你卖不出去也白瞎啊。”
“不用担心销路,我们可以……”
“你知道那薯有多难伺候吗?亩产又低,卖多少钱才能保住本?”
“只要能保证品质,一定有利润。”
“邱实,你爹收了那么多年红薯,你多少该知道点。同样的红薯,面儿上看不出差别,价钱差出好几倍。谁会收那贵的?这种薯从来都是少量种,自己吃。”
邱实不肯让步,说:“咱们种就要种最好的。现在不是吃不饱饭要拿红薯果腹的时候了……”
可是已经没有人再听他讲话了,他们开始自娱自乐。邱实庄重地站着,在混乱中,他听出了大家对一个已走出大山却又回乡种地的人的真实看法——他爹可真是养了个“大聪明”。
邱实不想放弃“丰溪三号”,认为种其他品种的薯是走不远的。他们说得对,城里人没有吃过好东西。离土地那么远,会有什么好吃的呢?吃的都是打药的、催熟的、没有滋味的。
农村穷则穷矣,可是吃的食物新鲜健康。猪是喂粮食长大的,谷子地施的是农家肥,收的小米十分钟能熬出一层米油。“丰溪三号”这种蜜薯,在盛产红薯的小溪沟也是人人称赞。把它扔进灶膛,满院子飘香,拿出来时,薯皮上流出的糖像蜂蜜一样闪着亮光,薯肉入口即化,吃完后就连流出的汗水好像都是香的。
他要卖农村人自家吃的东西。
可此时,面对满屋子爷爷叔叔们的异议,他那些堪称宏图的志向显得草率甚至可笑。他心里有些慌乱,不知如何说服这些顽固的乡亲们。
这时,角落里传来一个沙哑含混的声音,问邱实:“再说了,你算过没,四十亩地需要多少种薯?”
这个问题让屋里安静下来,他们面面相觑,像是在思索一个真正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一个数字在人群中传开。
“四千斤。”
爷爷叔叔们的反驳也落到了实处。他们说本来种这个的人就少,上哪找那么多种薯,简直是瞎耽误工夫。“看来是要摔个大马趴啊!”他们最终带着一种很自信的语气戏谑地说,“找去吧,能找着就种。”
邱实的心里却不似刚才那般愁云惨淡,反而明朗起来。四千斤,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字,相比于他自回来之后就一直对抗着的那种无形的意念,这个数字多么让人充满希望。
入冬前的这些日子,邱实在丰县十里八乡奔波。燕山山脉从河北平原一路北上,与内蒙古高原接壤。丰县地处燕山北麓,地势起伏大,气候多变。从坝下叠嶂的山峦绕行几十里盘山公路,可到达坝上广袤的草场。白天的阳光把人晒得暖暖的,入夜后气温骤降近20℃。将燕山分为东西两界的潮河源自丰县,河水浩渺,支流潺潺,于茂密的植被和静寂的峡谷之间流淌。为寻觅种薯,邱实有种走千山涉万水的感觉,再次感慨丰县景色之壮美,好似一颗明珠。
收薯的人提供的“丰溪三号”不足所需的两成,邱实一度逐门逐户询问。有时,到了人家家里,发现那些薯并不符合种薯标准,不是有损伤就是品种不纯;有时,随着人们的指引,寻到庄稼地里,人家许给他百十斤,可先要等人家把地里的活忙完才行。邱实就等着他们干活,帮着他们干活。暴晒在太阳底下,他的皮肤被庄稼叶子划伤,伤口被汗水浸渍。如此几番,他很快变得粗糙黝黑,身上出现许多细细的划痕。
邱实并不觉得辛苦,相反,他乐在其中。只是每当傍晚时分,天将黑未黑之时,田野笼罩于一片阴冷的灰色之中,他就会心生一种无力感。那是一种似乎所有希望与意义都正在消失的时刻。白天蓬勃的熟麦味道、甜玉米味道变成一种残香,旷野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寂寥,回家的路也变得无比漫长。那些曾富有生命力的生物与人一起淹没于黑夜之中,就连雄伟的山峰也只剩下寥寥几笔的黑影。人失去了所有的参照物,刚才还紧握在手的希望仿佛也正在流逝。
每当这种时刻,邱实就更加理解父亲。理解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住进祖坟边上那座小屋子时的心情。父亲想要走出去,认为男儿应志在四方,但事实上,父亲也不太确定应该在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只是知道外面有广阔天地。恢复高考后,父亲一直无法申请到考试资格。他一边申请,一边被驳回。如此几番,父亲便消沉了。父亲找了个地方要了却此生。选在祖坟边上,是考虑家里方便给他入葬。听说他试过一些方法,可是人在想死的时候偏偏很难死掉,最后白白遭罪,落下一身毛病。后来,祖母把瘫痪多年的祖父用一辆板车拉到父亲的身边,对父亲说:“你要死就带上你爹一起,我一个人顾不了那么多人。”祖母走后,祖父躺在板车上望着父亲掉泪,说不出话,只是哇哇地乱叫。父亲这才拖着病体,重新扛起家庭的重担,同时也做好了在无尽的农事中蹉跎一生的准备。
邱实曾是父亲重生的希望。
每每想到这里,邱实的心劲儿就随着暮色一起变得苍茫。他想让父亲知道,如今的广阔天地就在这大山之间,外面不缺他一个人。他在公司递了辞呈之后,次日就有人同他交接工作。可在这乡里不一样,似乎只有他也非他不可。若想真正开创一番事业,以邱实的出身、资历,以及他能获得的资源来看,只有回来。他认为自己依然志在四方,只是起点不一样。
两周过后,父亲与邱实有过一次深切的谈话。父亲劝他:“咱这儿不是那种有钱的村,山间全是一小旮旯一小旮旯的土地,不能像大平原一样规模化种植,麦秸都得自己扛。没人看得起这地方。你看看村里,都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你知道为啥?外面工地上不收六十岁以上的人。但凡胳膊腿能动弹的都走了。你回来,当的是无人村的村书记。”
邱实说:“等我干好了,我把他们都招回来。”
父亲拿起邱实的计划书,说:“还要干这种赔本买卖,你知不知道人家都在笑!”
邱实说:“笑就笑。等我帮他们赚到钱了,他们就不笑了。”还说:“红薯的存放不是问题,我能把‘丰溪三号’卖遍全国,还要卖到国外!”
父亲此时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骂道:“简直白日做梦!”
邱实却又说:“我还要把小溪沟的河修好!”
然后,邱实就搬到老姑家去住了。老姑接过邱实的行李时叹了口气,说:“犟种生的也是犟种,都随根儿。”
邱实住在老姑家的西屋。东屋原本是一间大房,后来被隔成了一间小房和一个小厅。当时,那是为迎接家庭新成员做的改动。
几十年前,就在那间小厅里,老姑生下了唯一的女儿。
据说当时老姑父还在地里干活,老姑挺着大肚子,突然疼起来了。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老姑大声呼救,无人回应。她是独自把孩子生出来的。
老姑父进家后,看见了满屋的血污和已经没有呼吸的小女儿。
在那个年代,孩子落地夭折倒也不算是稀奇事。老姑都说不清楚自己是何时有的这个孩子,只觉得每日头晕乏力,去卫生所拿了些解暑药。后来,她的肚子慢慢大起来,才知道是怀了孩子。不知是解暑药太过猛烈,还是生产时哪里出了问题,导致孩子没有存活。后来老姑再也没有怀过孩子。再后来,老姑父辞世了。
老姑家墙上常年贴着画,窗台上养着花,为的是让屋里显得不那么冷清。邱实回来,老姑由衷地感到开心。邱实收红薯,老姑跟着出主意。可全县十一个镇、十五个乡、三百多个村子里,总共有多少家收薯的?谁实在谁耍滑?坝上村子哪个值得跑一趟?这些问题,老姑也答不上来。她就去邱实他爹屋里,套她大哥的话,每每总有些收获。
可那天老姑从她大哥那里回来后,却红着眼眶。邱实追问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姑劝他爹别跟孩子置气,说他也是在干正经事情。他爹却来了脾气,嚷道:“要是你的孩子,你能不生气?”
老姑回家之后跳着脚骂她大哥嘴上缺德,之后就坐在炕上抹眼泪,再不言语。一直到傍黑,才又回去找她大哥,撂下一句话:“我的孩子要能活着,她愿意干啥都行,我指定不拦。”
入冬前,邱实完成了很多工作。寻找种薯的间隙,他几番奔赴县里和市里,与帮扶小溪沟的企业接洽;请来专业机构把土壤送去北京检测,以便调配出适合小溪沟土质的肥料;把地里现存的几座大棚修好后,铺上了滴灌设备。他打算冬天把这些大棚归还农户使用,种青菜萝卜草莓都行,等到开春后再用这几座大棚培育薯苗。
钱到账后,他立即支付了农户来年的地租。播种前付钱,一亩地按七百元算;秋收后付钱,一亩地按八百元算。一开始,邱实费了好大工夫才租来四十亩地。可最近,很多人主动找他,说地烂在那里也是烂,租给别人也是租,你需要就拿去种;还有人来问他合作社里用不用老年工,说重活干不了,但能除草能翻土能看棚能烧饭。
从乡亲们的转变来看,局面大有欣欣向荣之势,但邱实IR+YYaNL7PEjXU2P5w2biw==清楚这并非完全是他自己的功劳,他只是及时地普及了惠民政策而已,真正关键的还是“丰溪三号”。他开始深思,为什么非得是“丰溪三号”?
邱实祖上把这薯装在牛车里,从广阔的齐鲁大地迁徙至冀北山间,历经数年。沿途,此薯与其他几种薯杂交,才有了今日难得的风味。他要把薯从小溪沟推出去,不在于它们是祖辈历史的见证,而是这是邱实能想到的小溪沟可以量产的最好的作物。可是,就连那些已经对他表示认可的人们,再次听到“丰溪三号”时也会露出不屑的神情,就像在说,你撞你的南墙吧,反正我捞到碗里的是菜。
收薯始终不顺利,他也开始担心再执拗下去会山穷水尽。邱实虽然住在老姑家,可每日都还要去父亲屋里坐坐,请安问好,看屋里缺什么,下次回来补上。
父亲虽然不与他搭腔,却也不赶他。有时,他遇上高兴的事,就跟父亲说一下进展。有时,心情低落,无处诉说,他也会到父亲这里来。在父亲这位沉默的聆听者面前,邱实有一种从容的感觉,能把脑海中的一团乱麻渐渐捋清。
邱实说他懂父亲的感受。父亲年少时经历的匮乏和荒芜与他在城里体会到的拥挤和过剩看起来相反,实则本质是相似的。它们都变成了他们胸中郁积的块垒、风穿不过雨打不透的憋闷。下班后,他躺在出租屋里,像是正在缓慢地坠入深潭,醒来之后床上总有一个洇湿的人形印记。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无所适从。记得第一次听人谈起报考乡镇公务员时,那种振奋几乎让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随后,他发觉生活中铺天盖地的都是回乡的召唤。他对父亲解释:“我继承了你的志向,只不过要回到你所在的地方。”当他觉得自己正在孤军奋战时,心中的忐忑变成了一声声的叹息。有一回,他对父亲说:“爸,也许你是对的,我不该回来。”接着又说:“可是我也不知道还能去哪。”
那日,回到老姑家吃晚饭,一进门,他就闻到了新鲜泥土的腥味。邱实寻着味道来到南屋,拉开灯,看到了地上那些堆得像小山尖一样的标准种薯。足足有二百斤。
邱实又惊又喜,问老姑这是从哪里来的。老姑支支吾吾的样子,邱实感觉似曾相识。邱实小时候第一次吃的这薯就是他老姑“偷”来的。当时,老姑还说:“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叫偷呢?我去你大爷爷地里薅红薯秧子喂猪,你大爷爷说随便薅。那我就顺便薅了点薯。你就说好不好吃吧!”
邱实问她:“又是偷的?”
他老姑说:“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第二次,他老姑拉来了更多的薯。邱实心里犯起了嘀咕——他山间地头跑遍了,哪里还有这么多存量?难不成人家看见他后都把薯藏了起来?问老姑,老姑只“嗯嗯啊啊”说不出来什么。邱实思来想去,小溪沟大概只有一人会这样帮他。
冬日清冷的阳光洒遍山野,山林肃穆晴美,如大雪初霁般清亮。邱实一大早回到家里,父亲不知何时已经出门了。邱实在房前屋后踅摸一番,没见着红薯的痕迹,倒是发现父亲床头上放着几张在附近区县加油站加油的票据。
待中午时他再次回家,父亲依然未归。邱实一时不知该往哪去,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那条通往山里的小路。秋日里将小路淹没的草木如今已然凋敝,道路清晰地裸露出来。冬日里的山好像沉睡了一样,偶有不知名的鸟儿啁啾,清冷的回声在山林间荡漾。这座山是父亲年少时砍柴经常登的山,他说他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最熟的是那一株明开夜合。它知道父亲所有的心事。
这座山头,他从小跑到大,可在离开家乡后,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大山的孩子。他路过纵贯南北的太行山,在飞机上俯瞰过壮阔的秦岭,见过桂林山水的唯美如画、巴蜀山路的奇崛险峻。听着身旁人们的赞叹,他想不起家乡的山有什么特点,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并非名山胜川,但也清逸秀丽,一直那么肃穆地站在时光里。
沿着岭上的窄道,来到小溪沟的大后方,可以俯瞰整个村落。他看到趁着冬日安养生息的各家各户,看到邱家祖坟所在的那座山头和山脚下那间废旧的小小的砖房,看到曾经清澈的小河留下的浅浅沟痕。
他恍惚了一下,仿佛看到那沟痕闪着莹莹的光亮,像有溪水流过。冬日的山野草木萧疏,最大限度地反射着太阳的万丈光芒。他好像能看到亮晶晶的溪水汇成河流,能看到河里游着红的黑的鱼儿,还有他。
邱实在山顶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小心地坐稳。阳光灿烂,寒风凛冽,他眯着眼睛流出泪来。再过不久,夕阳会把天边映红,晚霞会像金色的液体在天际潋滟流动。他望向村口,他知道,不久会有一位老人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从那条土路拐进来。
那是一位倔强的老人,他会带着货箱里精挑细选出的“丰溪三号”,带着比他的倔强更加深沉坚实的东西驶进小溪沟,驶向一直等候着他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