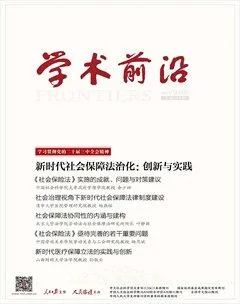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前瞻
2024-10-30李雄
【摘要】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探索和改革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要树立战略眼光并推动“破窗性”变革,确立新发展目标,厘清底层逻辑,理顺基本保障和福利性保障,重新划分各项社会保障角色,重构相关主体权责关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在基本保障层之基础上,不断丰富福利性保障层的项目和内容,拓展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新境界。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发展 经验与挑战 前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8.004
引言
社会保障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文明成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且重要构成部分,也必定会打上中国制度与文化的烙印。[1]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斗的百年历程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民生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民生建设,特别是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当然也要看到,在我国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日新月异等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同时,从现在起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保障将承担起更加重大的使命与责任。
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抓好这个关键窗口期,以更高的站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符合国情的价值理性,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有必要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历程中,洞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内在基因、基本规律与中国逻辑,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保障的理念、路径和方法等,把社会保障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建设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在城乡规划、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障可持续性为重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这些社会保障方针和重点工作既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任务和关键支撑,也为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保障的顶层设计描绘了宏伟蓝图。一方面,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这是一个重要发展,为基本社会保险并轨改革提供了制度经验和实践基础。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于2015年全面改革,使其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统一,旨在缩小两者保险待遇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又是一个重要发展,初步彰显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分类改革发展的重要思想。我国于2014年正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其覆盖范围、缴费与支付、基金管理与运行等统一管理,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层面的城乡统筹;随后又于2015年在全国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2016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其覆盖范围、统筹方式以及保障待遇等方面予以规范,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层面的城乡统筹,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定型,距离城乡统筹目标又前进了一步。[4]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充分彰显了社会保险应有的“大数法则”价值理念和制度优势。2018年,我国正式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22年又加大对个人养老金的关注与相关制度建设力度,促进了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的完善。同时,我国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完善。社会救助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具有“兜底性”功能,秉持“体面生活”“需要就是权利”等理念,主要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专项救助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等。2014年,我国在国家层面首次将不同社会救助内容统一管理。同时,2016年我国将农村设立的五保户制度与城市设立的“三无”人员救助制度合并,形成了城乡统一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此外,我国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健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老年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作出新调整,将机构养老的支撑定位改为补充定位,并将医养结合融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我国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等文件,落实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扩大了儿童福利范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相比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制度层面型构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具体诉求。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新发展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等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2017年,我国开始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管理试点工作,以此优化医疗保障结构并提升经办效率。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将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统一管理。2019年,我国正式将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压力,我国于2016年开始在上海、青岛等地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2020年在总结第一批试点工作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在天津、福州、汉中等14个城市开展第二批试点工作,为全国范围内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社会救助方面,在继2014年顶层设计首次统一管理社会救助内容、2016年建成城乡统一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基础上,我国于2021年在低保审核办法修订文件中删除涉及区分城乡低保的提法,统筹城乡低保制度。在社会福利方面,我国于2021年出台专门针对“十四五”时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赋予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新内涵,突出老年人医疗、康复、养老等普惠性养老服务。在社会优抚方面,面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专项社会保障不断增强。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统一管理转业、复员、退休、退役等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绘制了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蓝图,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相比党的十八大突出解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等重点问题,以及党的十九大强调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党的二十大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的系统集成和高质量制度体系建设。同时,2022年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总结与发展要求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总的基调是: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把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总钥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社会保障建设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既要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相关政策,又要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积极创新,不断挖掘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的制度内涵。
具体而言,“覆盖全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要求,[5]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直接体现,要求社会保障项目都能惠及需要的人,包括将更多的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纳入社会保障,应保尽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统筹城乡”既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延续,也是提升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基本要求,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城乡分割难题,缩小社会保障城乡差距,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我国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层面的城乡统筹和基本医疗保险层面的城乡统筹的基础上,继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使这两种基本社会保险在收支上更趋合理和可持续。
“公平统一”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在统一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不仅要在参保资格、待遇标准、经办服务等方面统一,而且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中各项制度的整合统一。[6]同时,促进社会保障公平统一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大数法则”优势,尽可能提升统筹层次。我国在2018年正式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这为基本社会保障与补充社会保障分类分层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安全规范”是cZRGeYAvM7bxqPXhzCeQAPGcU1P6eaWqMjYSXsLFPyE=党的二十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提法新要求,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结和提升,也是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保障。规范是安全的前提,要求加强社会保障合规建设和法治建设,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政策统一、经办统一、管理统一、信息统一、责任统一、待遇标准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7]我国在2014年顶层设计首次统一管理社会救助内容、2016年建成城乡统一的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基础上,于2021年在低保审核办法修订文件中删除涉及区分城乡低保的提法,统筹城乡低保制度。立足于社会救助制度的这些改革发展成果,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就是要在从分散到统一的基础上,基于合规和法治要求,不断规范社会救助体系,提升其安全效能。
“可持续”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保障代际关系问题,要求处理好个体与整体、效率与公平、当前与长远等主要关系,特别是要合理减轻困难人员参保负担与扩大社保基金委托投资规模,实现财政收支动态平衡。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如何处理好正在参加社会保险的年轻人与正在享受养老待遇的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在经济、心理、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平衡,有必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建立友好型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新机制。党的二十大提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就是一个重要发展,是对我国分别于2016年和2020年开展的两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总结和提升。“多层次”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功能与建设方略,这不仅体现为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兜底保障功能的社会救助体系、具有中坚力量的社会保险体系、具有锦上添花意义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具有专项保障功能的社会优抚体系,也体现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建构的重要方略,坚持实事求是和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项目和保障层次。比如,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是所有人的基本保障外,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是所有工作中人的基本保障,健全企业年金制度和职业年金制度以及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构建多层次补充保障体系,增进社会福利。[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主要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发展、谋福利、谋幸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全面建立劳动保险制度,改革开放后更是将社会保障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制度安排。[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加强顶层设计引领,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统筹管理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成立国家医疗保障局。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初步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不断健全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优抚制度。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保障工作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开展了很多重大制度改革,开辟了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新境界。
坚持人民至上。社会保障关乎千万家庭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为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难愁盼的问题始终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HVWBq0FZHNNovpWV1WHvpuecWEjGlQh5U4nQLQwJ+is=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三个类别的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9.99亿人,占应参保人数约90%。推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57亿人,参保率达96.9%。[10]截至2023年末,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66亿人、2.44亿人、3.02亿人,比2012年分别增加2.78亿人、0.92亿人、1.12亿人。[11]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待遇不断提升。其中,2023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比2012年增加一倍,月平均失业保险金水平从2012年的707元提升到2023年的1814元,月平均工伤保险伤残津贴从1864元提升到4000元。[12]另外,全国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人月均665元和人年均5842元,军人抚恤待遇以年均10%的幅度持续增长。[13]兜底扶贫成效显著,从2015年到2019年,我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减少502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7%降至0.6%。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5575万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14]总之,这些成就极大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坚持依法治理。综观世界,社会保障涉及面广而复杂,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法治化建设不断完善。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定型和稳定。[15]随后,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则为军人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2012年和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分别两次修改,以积极老龄化基本理念为指导,确立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确立了我国生活救助与专项救助相结合的社会救助体系,标志着我国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基本形成。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促进了社会福利法治建设。同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则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为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除了上述法律法规外,国务院还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丰富了我国社会保障依法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夯实了建设法治社会保障的基础。
坚持稳中求进。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把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总钥匙。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我国城乡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稳中求进。我国根据优先需要原则,着力开展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工作,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居民”两大制度平台,推进方法上坚持渐进改革,待遇衔接上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办法的做法,较好平衡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比如,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金虽然连续16年提高,但近年趋向小幅提升,开始朝着建立正常调整机制的方向迈进,一些福利待遇虽然逐年有所提升,但重点是补齐短板。在反贫困上,实行社会救助与扶贫有序衔接。[16]另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多年存在的城乡分割、群体分割等局面逐渐得以改善。在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推动下,现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格局基本形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国家医疗保障局主管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护理保险等,民政部主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慈善事业等,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退役军人优待抚恤和安置等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主管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等等。
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基本态势
新时代新征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共同的价值理念、形势评估和问题判断,准确研判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面临的基本态势。立足我国国情,结合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新形势新趋势,抓住“人要么有就业、要么有社会保障”这个核心逻辑,分析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基本态势。
人口形势及其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人口构成中国的基础国情,任何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都要首先明确中国当前及未来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风险。[17]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
我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基本情况。按照人口转变理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营养健康等不断改善,生育观念发生转变,人口再生产模式将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任何国家一旦完成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将在低位徘徊,人口增长率也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18]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60余年来首次出现人口总量下降现象。[19]
同时,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有四个因素值得同步关注:其一,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相互强化。研究表明,人口负增长不仅是人口规模问题,往往伴随着老龄化,而且人口负增长周期及强度与老龄化程度呈正相关。[20]比如,从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负增长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从2000年的1.26亿增长为2020年的2.64亿,到2050年则可能达到4.80亿,预计占我国总人口的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的20%以上。[21]其二,人口负增长与劳动适龄人口负增长相互强化。2010年后,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逆转,劳动适龄人口在2011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从2012年到2022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出现双降,年均减少约580万人。[22]其三,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理解当代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支点。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提供了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排序中,比例最高的是离退休养老金,占老年人总数的34.67%;排名第二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占老年人总数的32.66%;第三位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占21.97%。同时,城市70%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养老金,农村75%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各省份老年人生活来源差距明显,上海、北京、天津社会养老水平最高。[23]其四,老年人健康状况。除了主要生活来源,老年人健康状况也是把握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障的另一个支点。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口中有54.64%自评身体健康,32.61%的老年人基本健康,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占12.75%。[24]
我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主要影响。从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相互强化看,首先,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相互强化提高了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我国在2011年开始出现劳动适龄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攀升,2011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66%,到了2021年则突破30%,这意味着平均3.3个劳动力赡养一位老人。[25]其次,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相互强化加重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比。最后,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相互强化凸显了我国当前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从人口负增长与劳动适龄人口负增长相互强化看,这种相互强化对社会保障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用工成本攀升,机器替代人力劳动不断加速,社保缴费主体不断减少,进而制约社会保障“大数法则”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看,如何提升老年人离退休养老金的公平性,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和生活不能自理问题等,对我国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保障新模式、依法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提出了现实诉求。
就业形势及其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在对人的保障上,就业与社会保障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具有紧密关联性。《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新人口形势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我国就业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建设产生了现实而长远的影响。
我国当前就业的基本情况。首先,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与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且主要矛盾是就业结构性矛盾。人口规模缩减与劳动力供给减少,将对用工成本、社会保险、投资、消费等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制约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同时,新增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经验和职业技能,大龄劳动者在观念、技能等方面难以匹配新技术新产业发展需要。同时,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日益突出,[26]这将导致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改善速度减缓,进而加大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双方匹配的难度。另外,从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看,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诸多影响,人类社会正在产生生产方式变革的潜在新节点。[27]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范围正从生产向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扩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蔓延,从体力型岗位向技能型岗位拓展,机器替代人的现象逐渐增多。[28]“机器换人”现象越来越突出,尽管制造业用工总需求没有下降,但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29]特别是部分标准化、程序化、模块化的中低端岗位被机器取代,人工智能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放大了信息化的就业替代效应。
其次,灵活就业不断发展,新就业形态日益壮大,非正规就业不容忽视。灵活就业是指用工条件的自由组合与就业方式的灵活化,[30]与新就业形态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后者是指借助算法等新技术支撑的平台就业。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正成为灵活就业的新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31]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职工总数为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我国职工人数的比重已超过20%。[32]除了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非正规就业也不容忽视。非正规就业通常指与非正规部门相对应的就业形式。国际劳工组织在《1991年局长报告:非正规部门的困境》中指出:“非正规部门是指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当前,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在非正规部门劳动。
我国就业形势对社会保障的主要影响。为有效应对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有效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需要积极作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面临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动态平衡、如何发展当代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等重大课题。首先,社会保险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该制度适用的一个前提是有劳动关系。工业社会是一人一生只做一份工作,平台经济时代是一人同时做多份工作,[33]“共享员工”“人机协同工作”等不断涌现,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多元、碎片和复杂,就业边界日益模糊。如何依法界定就业保护与社会保护中的劳动,如何依法界定劳动关系,如何重新审视劳动关系的含义和边界,对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提出了新要求。其次,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放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导致青年就业和老龄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影响其收入,进而影响参保积极性、参保能力和参保人数,最终从整体上制约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最后,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失业保险的价值理念、制度功能、待遇机制等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建设驶入“快车道”,特别是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体系最大也是最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厘清底层逻辑,既不能简单查缺补漏,首先要知道“缺什么”和“漏了谁”;也不能描摹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而是要始终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总开关”“总钥匙”。
社会保障目标定位尚不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领域尽管开展了很多改革创新工作,一些具体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整体和全局看,我国社会保障至今缺乏清晰的目标定位,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保障建设一直无法取得系统性突破的根源所在。例如,党的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到底是城乡独立而同步建设,还是城乡合并而一体建设,尚不明朗。从目前基本养老保险涉及的三类人群来看,主要还是制度全覆盖,人的基本养老需要层面的全覆盖远未实现。又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人们普遍关注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等依然存在应保未保的情形,而且基本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直接制约了社会保险“大数法则”优势的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等制度缺失对我国人口结构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再如,社会保障政策定位尚不明确,相关主体责任失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提高个人责任在社会保障中主体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34]社会保障政策缺乏与人口政策协同的理念,不能适应人口政策的需要。[35]同时,囿于社会保障目标定位不清晰,高质量社会保障指标体系亟待建立。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整体上看,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主要以社会保障现有项目为导向,侧重在某个具体保障项目上以点延伸,造成社会保障覆盖面依然有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性不强等问题。就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来看,现有社会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前提CMUIJwqAN+1MMuULeUvZPw==,除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面向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企业职工外,其他社会保险主要面向企业职工,一些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非正规就业人员等难以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仅对城镇灵活就业人员、非正规就业人员等覆盖有限,而且没有覆盖在农村就业的劳动者。202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不含参保离退休人员)共34917万人,仅占全国就业人员的46.8%,占城镇就业人员的74.7%。[36]从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看,首先,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亟需平衡。从应然层面看,社会保险坚持权利义务相结合,社会福利则是在社会保险这个核心保障基础上的“锦上添花”,社会救助是兜底性社会保障。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三者关系与各自保障功能并未明显区分开来,不仅出现低层次保障超出高层次保障,其中以社会救助发展不充分与过度保障并存为典型,[37]而且最需要的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等却成了明显的短板。其次,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有待协调。基于社会风险分类,基本保障的对象是所有国民,保障内容涵盖养老、医疗、生育、社会救助等,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所有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其他如社会福利、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为补充保障。目前,以职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保险可谓一险独大,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建设缓慢。在该情形下,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相对安全的保障,那些低收入者则面临系统性社会风险。最后,相关主体权责亟待廓清。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三者边界不清晰以及基础保障和补充保障失衡的共同影响下,相关主体权责不清就成为必然,这不仅造成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分工不清晰不合理,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依然模糊,中央政府与用人单位责任偏重,地方与个人责任相对较轻。[38]就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性来看,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特别是基础性立法明显滞后。比如,社会福利法和长期护理保险法缺失,社会救助法律位阶亟待提升。有学者甚至指出,我国虽有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但单项社会保险法缺位。[39]
社会保障实践效能有待提高。一方面,从社会保障对象的识别来看,作为社会保障的支柱性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涵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这对于那些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劳动关系难以识别的劳动者而言,无疑是不利的。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是9.79亿人、2.09亿人、2.58亿人,[40]对比全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社会保险参保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网络主播在国家层面正式成为新职业,对于这些群体,如何确定其有无劳动关系,以及如何确定其是否具有社会保险参保资格,既是一个理论难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他们当前更需要具有普惠性的职业伤害保险。调查发现,有56%的骑手希望能够参加社会保险,获得较高保障。[41]另外,社会保障对象的识别机制有待完善。另一方面,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来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2015年全面改革,旨在使其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目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在待遇上依然存在差距,养老金的公平性有待提升。[42]我国在2018年正式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但也只是限于其中的基础养老金。我国在2016年和2020年分别开展两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长期护理保险至今尚未进入法制轨道。另外,作为事关我国人口总量与结构的儿童福利制度和家庭福利制度亟待确立。
明确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43]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保障面临的方向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建设高质量社会保障要有战略眼光,推进“破窗性”改革和重大制度建设,首先要明确高质量社会保障发展目标。
确立发展型社会保障目标。发展型社会保障的基本含义是:一方面,社会保障首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社会保障应当秉持人本主义,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就业能力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实现从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化,把保障人权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全面纳入社会保障各项制度的考虑和设计。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还要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保障要坚持把人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积极回应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足够的激励和动力,而不是简单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同时,发展型社会保障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特别是被保障对象的参与。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自立观念与权利意识的崛起,也是因为发展型社会保障必须始终立足于权利本身,还权于民。[44]确立发展型社会保障目标的主要理由是:以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面临的“社会福利危机”为鉴,从被动的收入保障向“积极的社会政策”转变,重视人力资本作用,提高劳动者技能,通过实现更好的就业来满足各种需求;[45]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是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46]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主要经验的升华,是积极应对人口形势、就业形势变化等基本国情的客观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人的发展是根本和第一要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将人口规模优势转为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如何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凝聚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社会保障在价值理念和目标定位上积极转型,确立工作福利理念,树立被保障对象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最好的制度是能够激励劳动的制度,最理想的效果既不是“福利最大化”,也不是“发展最大化”,而是劳动与福利的协调、经济发展与福利增进的均衡,[47]等等。
确立共享型社会保障目标。共享型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是:一方面,共享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共渡难关和共同发展的一致信念和生存法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结晶。对于社会保障而言,共享强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是社会保障“大数法则”的集中体现,也极大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共享型社会保障基于底层逻辑,在区分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的基础上,强调在基本保障层面优先实现全民共享,建立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共享型社会保障还强调补充保障层面的分享,避免因为补充保障差距过大而产生新的贫富差距。发展型社会保障是共享型社会保障的基础和保障,后者则是目的和动力。确立共享型社会保障发展目标的主要理由为: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当代社会保障提出的新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48]是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本质要求的内在要求;是顺应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革新趋势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需要,等等。
建立健全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建设发展型社会保障与共享型社会保障的目标需要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支撑。我国已基本建成由政府主导的法定保障与市场和社会主导的补充保障共同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但尚未建成目标定位和底层逻辑清晰导向下的制度体系,且法定保障目前还是以制度全覆盖为主,离实际需要尚有距离。因此,要建成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应在发展型社会保障和共享型社会保障目标定位的导向下,厘清底层逻辑,重新认识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内在关系,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意义重大的改革,重新划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应有角色,重构相关主体权责关系,遵循社会保障基本法则,分层建立健全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基本保障层。基本保障针对所有国民,具有“刚需”“强制性”等特征,但如何确定基本保障,要统筹考虑人口、就业、经济、低收入群体规模、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障项目整合与城乡统筹等情况。总的原则是从基本生活保障开始,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保障具有基本人权属性,坚持所有国民的基本保障平等。基本保障涵盖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救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享有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所有军人及其家属都能够享有的社会优抚。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进一步扫清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加入基本保障的障碍。如此,才能真正以全民“基本需要”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消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制度覆盖与基本需要覆盖、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等之间的各种“鸿沟”,破解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等基本社会保障建制难题,有效构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彰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人民性和公平性。
关于如何推进基本保障层的相关制度建设,我们可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目标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筹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台。在路径选择上,有观点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已经建立了基本养老金与职业年金,如还需要,可自行通过市场解决,政府不宜再锦上添花。企业职工已经建立了基本养老金与企业年金,需要尽快优化和落实。[49]该方案仍面临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在基本保障上的各种差异问题。另有观点认为,需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升为非缴费型养老金,由中央财政筹集资金,向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按统一标准发放。[50]该方案仅针对城乡居民,是否涵盖城乡劳动者和所有国民,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基于基本保障彰显的“需要即权利”理念,可直接整合现有的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三种基本养老保险,统一为国民基本养老保险,以此建立全国统筹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台。为使新旧制度平稳过渡,尽可能减少改革成本和风险,前期应进一步降低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缴费率,建立激励机制,特别要激励非工资劳动者参保,把基础养老金待遇与个人缴费收入及缴费年限挂钩,这对于乡村振兴以及《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背景下调动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参保积极性至关重要。还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的财政补贴责任,不断提升待遇水平,重视过渡期制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后期目标是建立非缴费型、普惠性全民基础养老金制度。
福利性保障层。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社会保障侧重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旨在增进人民福祉和提高生活质量。福利性保障可以是普遍性的,也可以是选择性的,取决于特定社会政策目标。如果说基本保障极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人民性与责任担当,福利性保障则需要足够的想象力和“中国智慧”。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福利性保障层建设需要不断创新,在基本保障层之基础上,通过做加法,建立健全类别多样、多层次的补充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在保障项目选择上,立足我国老龄化人口态势,加快发展儿童福利和家庭福利,承认“家庭劳动”,[51]推进试点与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与互助性养老服务相结合,加强对农村养老服务政策倾斜;准确定位长期护理保险,将其作为家庭责任的分担机制而非替代机制,[52]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工作,后期则需要把长期护理保险适时上升为全民基础保障项目;拓展企业年金的适用范围,重构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的含义与界定标准,使企业年金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弱化工资在参保标准中的地位,突出个人和家庭的综合收入作为核定参保基数,等等。在保障待遇的标准上,尽管福利性保障更多以市场机制为驱动力,但也要注重合理适度,避免福利性保障层面差距过大而影响公平和共同富裕。同时,政府要加大数智社会保障建设,实施精准治理和便捷治理,加强国民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数智能力建设。[53]
结语
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窗口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根本性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要树立战略眼光和“破窗性”变革: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确立发展型社会保障和共享型社会保障目标,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科学的目标导向。把坚持人民至上既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根本立场,也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依靠和强大动力。厘清底层逻辑,区分基本保障和福利性保障,重新划分各项社会保障应有的角色,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权责关系。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在基本保障层基础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丰富福利性保障层的项目和内容,拓展高质量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新境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法治化保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FX129)
注释
[1][49]郑功成:《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论纲》,《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2]林卡:《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演化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政策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0期。
[3]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2022年第8期。
[4]刘晓梅、曹鸣远、李歆、刘冰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成就与经验》,《管理世界》,2022年第7期。
[5]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6][42]崔开昌、吴建南:《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价值引领与未来进路》,《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7]吴江:《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2022年6月29日,https://www.cntheory.com/jjsh/202206/t20220629_51451.html。
[8]顾海、吴迪:《“十四五”时期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与战略构想》,《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9][11][12]王晓萍:《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求是》,2024年第9期。
[10][13][16][38]郑功成:《面向2035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1期。
[14][34][40]宋凤轩、康世宇:《“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展望》,《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15]杨思斌:《我国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四十年:回顾、评估与前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7][21]胡湛、彭希哲、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18]原新:《中国人口转变及未来人口变动趋势推演》,《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
[19][50]陈宁、鲁冰洋:《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
[20]原新、范文清:《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交汇时代的形势与应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22][2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如何看待我国就业形势》,《工会信息》,2020年第2期。
[23][2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2期。
[26]中国新闻网:《聚焦毕业生 “慢就业”:先锻炼能力还是先丰富阅历?》,2016年12月14日,https://news.cctv.com/2016/12/14/ARTI1jko6Gjudv09NoXVxAHJ161214.shtml。
[27]刘伟:《人机环境系统智能与生产方式变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9期。
[28]李亢:《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就业现状与对策》,《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
[29]莫荣:《努力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经济研究参考》,2022年第7期。
[30]杨燕绥、赵建国:《灵活用工与弹性就业机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31]岳昌君:《以就业优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大学生就业》,2022年第21期。
[32]杨思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研究——从地方自行试点到国家统一试点的探索》,《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16期。
[33]佟新编:《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第273页。
[35]曹信邦:《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政策协同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36]左学军:《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视角》,《求索》,2022年第6期。
[37]邓大松、张怡:《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评价指标、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39]郑尚元:《新中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回眸与展望》,《求索》,2020年第6期。
[41]施红等:《外卖骑手的意外伤害、风险感知及保障需求》,《中国保险》,2020年第8期。
[43]习近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求是》,2024年第14期。
[44]李雄:《中国社会法立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45]张浚:《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二元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定位》,《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46]王晓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10月23日,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23/1023/c58278-40100981.html;魏礼群:《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笔谈)》,2024年1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MwNDc4OA==&mid=2247485569&idx=1&sn=4a1bf8271982f4a45fae6498cbb40048&chksm=ebaa033adcdd8a2c1d62b0f593bf6b931eeed8483511ea95ae5375d0ec73305c4e56e495da63&scene=27。
[47]景天魁:《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彰显中国智慧》,《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6期。
[48]余澍:《现代化、社会保障与制度文明:历史轨迹与中国道路》,《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51]父母为培育人力资本所付出的对整个社会同样具有生产性的贡献,在老年时也应像职业活动一样得到认可。基于该设想,将来应当为标准养老金领取人设置一个养育年限,即只有在同时完成职业活动和养育活动的情况下,才有资格领取标准养老金,不提供“家庭劳动”的人领取标准养老金的年限应有限制。参见[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8~149页。
[52]谢冰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护理保险的理念与路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53]杨立雄:《数字化转型与“创造性破坏”:社会保障数字治理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5期。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