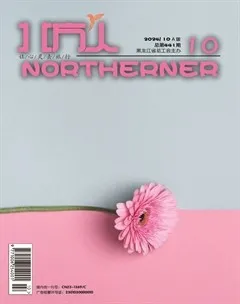一个中国妈妈的异国教育观察
2024-10-24潘轩
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鸟,因为没有天敌,这种不会飞的鸟在当地生活无虞。2024年2月,周轶君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2》时,在当地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宿命:丰富的地理资源让新西兰人免于生存的压力。
她去新西兰的Swanson小学拍摄,发现课间长达35分钟。孩子们被放到“没规矩操场”,没有老师、家长在旁监督,孩子们放野归山,爬树登高,举着木棍打来打去,在坑洼的沙地上不戴头盔玩滑板。
在一旁观察的周轶君感到惊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跑过去问一群正在疯玩秋千的孩子:“好几个人在上面会不会塌?”一个孩子自信地回答:“不会!”虽然看上去危险,“但只要人群里有人说害怕,其他人会立刻停下。”她观察。
“没规矩操场”只有一条潜规矩: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这个底线之上,成年人不干涉孩子们怎么玩。“限制性的东西被拿走后,孩子变得特别有主意,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周轶君说。
2018年,拍摄第一季《他乡的童年》时,周轶君刚刚成为母亲,对这个角色的焦虑,让她走上了探索各国教育状况之路。2023年9月起,周轶君再度出发。这次她去了因地理资源匮乏而极度内卷的新加坡、重视感性教育的法国、追求教育透明度的德国、地广人稀的新西兰以及聚集着很多中国陪读家长的泰国。
在新西兰的一家幼儿园,角落里散放着“零碎旧料”,比如废旧轮胎、货物箱的木底座、缠电线的电缆盘等。孩子们调动创意和想象力变废为宝。比如一个隐形眼镜盒,就被制成“放大镜”,被孩子拿在眼前到处看。周轶君观察,新西兰重视在教育里培养动手能力,是新西兰人“岛民性格”的一部分。“新西兰是一片非常年轻、孤独的大陆,邻国都在特别远的地方,第一批岛民来就要解决很多问题。”她说。
导演任长箴不觉得自己在拍一部聚焦各国儿童教育的片子。新西兰“牛羊比人多”,重视动物福利到了极致。她记得他们去新西兰拍摄一个兽医院,当地研究的冷冻技术可将病牛病羊的尸体用于医学解剖,而不必做活体动物实验,任长箴受到巨大的感动,“看到了一个文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
“教育不只是针对低龄小孩的,哪怕你已经50岁了,领受到一个好的、让你成长的东西,仍然叫教育。”任长箴说。
为什么要在教育里讨论爱和幸福
新加坡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墙上赫然挂着“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的标语。这个国土面积761.1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怕输”心态弥漫整个社会。
新加坡推崇精英教育,课外补习氛围浓厚。教育的“分流战”从小学的PSLE考试——小六会考即开始打响。内卷和危机教育催生了新加坡的经济活力,新加坡也将培养人才视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02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新加坡学生全部排名第一。
不过,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在接受周轶君采访时却反思,这种教育体制带来了优等生同质化问题。学生所有的成长空间都被卷进积分制的系统中,留不出空间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所谓的天才,是被机制筛选出的,而非原生态的天才。
周轶君发现,法国人很爱说话,热衷自我表达,天性里带有散漫的底色,这些都能在他们的基础教育里见到端倪。任长箴则表示,在法国的基础教育里,她看到了关于认知常识、认知情感的培养。
周轶君去巴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旁听课外哲学课。课开始前,哲学老师首先教孩子们学会提问。有孩子举手:可不可以去上洗手间?老师说,这并非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有标准答案。
老师手里拿着一个苏格拉底玩偶,5~7岁的孩子们想要表达见解,就拿着苏格拉底发言。那节课大家谈论的话题之一是幸福。老师让学生用橡皮泥捏一个能让自己感知幸福的东西。有人捏了一头牛,认为它温顺、不伤人,与人为善是一种幸福;有人从反向思维出发,捏出乌云和雨,认为下了雨没法出门,让自己不幸福。
周轶君发现,法国人思考问题的尺度可以非常小。比如谈论爱时,如剥洋葱般层层展开:什么是爱?爱的反面是什么?爱一个人和爱一双球鞋有什么不一样?她体察中式教育塑造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框架很大,但难以细下去。
在另一节面向9~10岁儿童的哲学课上,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你的爱还存在吗?有孩子说,爱是你自己的决定,你决定爱,就可以继续。讨论恶,有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刚出生的婴儿不停地哭,吵得大家都不能睡觉,但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作恶。
“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周轶君说,旁听时她不再追求标准答案,发散地随着孩子们的思维东晃西晃,“你发现他们的词语都不是咱们说的泛泛而谈,不是俗套的话,不是在学大人说话。”
如果人们羞于谈论爱、谈论现实中的私人情绪,就会让它们更加朦胧。“我们一说情感、感觉,都有点说不透。我们都这么大了,成年人了,但没法把高兴分成30个层次去聊,也没法把沮丧分成好几个层次去聊。”任长箴说,“生而为人,这个东西很重要。”
直面禁忌,允许犯错
周轶君曾经看过一本法国的儿童哲学书,主题之一是懒惰。她当时心想,书里再怎么分析,最后的结论总归还是要落到人不应懒惰上。结果却出乎意料:它最后的结论是一幅画,一个法国人躺在沙滩上,说,懒惰是OK的。
“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恶的、不好的东西,回避比较多,不太去探讨它。”她说,“卢梭研究教育,认为艺术起源于自恋,历史起源于暴君;很多东西起源于恶。他会做非标准面的研究。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
在周轶君走访的几个国家中,德国的教育不惧怕直面“恶”。在柏林的市中心,排列着2711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周轶君和柏林郊区一所小学的师生一起前往纪念碑参观,她问起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老师回应:与其让学生从社交媒体、假新闻中获取资讯,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
“在其他文化中,那些禁忌而隐晦的内容,在德国人心中是透明的。”周轶君说。
这种透明也延伸至性教育。德国教育政策有4项全国性的要求,其中一条是进行性教育。同时,德国政府还会为14~22岁的女性提供免费的避孕药物。一系列的举措让德国成为整个欧盟早孕率最低的国家。
在德国一座小镇的小学,一个班实行混龄教育,没有老师统一制定的教学进度,学习材料按照深入程度划分不同板块,进度全由学生自行把控,老师在一旁帮助。周轶君带着愧疚询问老师:对孩子的高度信任来自哪里?会不会有孩子抄袭已过关孩子的参考答案?
“我认为信任来自不要总将孩子们相互比较。如果对全班学生说,这是你们的测验,你们要同时在这里完成同样的测验,他们自然会相互比较,通常这就是学校测验的目的。”老师告诉她,“但是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如果没有,我们会帮助你。我为什么还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呢?测试是单独的,而非公开的。”
没有什么教育一定是好的
走访了5国,周轶君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说哪一种更好更有意思?真没有标准。”
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状况,就像很多面镜子。周轶君说,镜子里面看到的不应该只有差距和悲哀。“有些疯狂是应该停止的,但是也有一些文化里的发愤图强、希望更好是不可改变的。而且那个东西一定错了吗?也未必。”
她以新加坡和新西兰为例,它们各自需要怎样的公民?新加坡可能紧迫需要精英管理人士,而新西兰更需要的是理解当地的地热资源、动物资源,懂得种植水果的人。周轶君总结:“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国家对于公民的需要不一样,在很多方面的培养也不一样。”
去新西兰采访时,一位华裔国会议员告诉周轶君: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好与坏定义为年轻人有多激进、多拼、多有钱,新西兰榜上无名。但如果把它定义为年轻人虽然胸无大志,但有自己安稳的家庭、好的人际关系,那新西兰榜上有名。
任长箴没有孩子,也没有把各国教育方式拿回家试试的需求。在她看来,这些教育思路“只有特点,没有优点”,能效仿到什么程度,完全因人而异。
“比如德国的混龄班,在中国怎么能实现呢?咱们一个班里50多个孩子,就这么几个老师,当然得按一个标准,最后把好生选拔出来,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我绝对没有一个观点说,拍了外国的教育,就觉得中国的教育都不靠谱。”任长箴说,“但是我觉得,在选拔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培养的因素?比如加一点哲学课,培养一点感性的东西。”
(摘自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