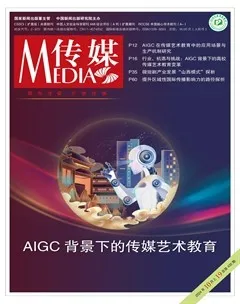《山水间的家》的空间叙事与文学绘图
2024-10-24罗奕郭昭
《山水间的家》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第一季每期平均收视率1.299%,位列2022年央视晚间时段首播文艺节目单频道收视率第一,全季首重播观众累计触达人次超6亿。2023年,第二季电视观众总触达18.3亿人次, 荣获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节目”。据中央广电总台总经理室数据,第五期节目CSM全国网数据达0.74%,收视排名全国综艺类节目第1位,全网播放量近2亿次。“家”是该节目的关键字眼和表达核心,是具体又抽象的空间形式。本研究旨在探讨节目如何完成对“家”空间的进入、勘探、标记与编织。
一、“家”的探访:《山水间的家》对空间的编织
美国文学空间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塔利提出,“文学绘图”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强调绘图者通过制图的形式来表征叙事或文本中的社会空间,以及个体或集体与社会、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它巧妙地将地图绘制与艺术创作相提并论,特别是聚焦于通过“叙事”这一手法展现的创造性表达。文学绘图不仅是文学空间研究的核心要素,也为其他艺术叙事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多个层面探讨了叙事空间性的深层含义和价值,进一步强调了叙事方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文学绘图的过程中,故事叙述者像制图师一样,因此又被称为绘图者,他们在作品中创造出对世界的表征,承担着多重身份,他们既是空间的勘测者,也是诗歌的吟咏者,他们通过勘探与吟咏将故事缝合在一起,“将相互独立的空间表征精心编织在一起,吟咏者创造出一幅地图,这反过来又形成了一个扩大化和多元化的新景象”。《山水间的家》通过对空间的编织形成文学绘图,其创作者具有勘测者、吟咏者、绘图者等多重身份,带领观众前往乡村冒险,勘测空间,叙述故事,并最终将分散的空间编织起来,赋予秩序,构成具有整体性的文学绘图。
节目中的“家”是“他者的家”,是不同于城市空间的乡村空间;“家”是具体的空间形式,主持人进入到“异域空间”,完成对未知空间的“探险”,因此节目是一部影像版的“冒险小说”,空间是其最重要的元素,节目在进入、勘探、标记和编织乡村空间的过程中完成对家的探访。
节目通过进入和勘探,展现与城市相异的乡村空间。在节目片头,主持人穿过一扇虚拟的门,完成人类学家范热内普所谓的“过渡仪式”,进入到“山水间的家”,门作为空间的区隔,区分了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而“过渡仪式”则将乡村空间标记为“阈限”和“神圣空间”。节目中,主持人进入乡村空间后,不断勘探多种空间:有浙江省鲁家村、湖南省石堰坪村、湖北省莫岭村、广西壮族自治区怀洪村、江苏省礼诗圩村、安徽省西递村等24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观空间,也有各个乡村中的房屋、农田、广场和博物馆等微观的空间。节目通过“并置、碎片、蒙太奇、多情节”等方式,将这些分散且独立的空间作为重要元素,构建桔瓣式的空间形式,每一个空间都作为一个“桔瓣”而存在,从而使其空间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延展,甚至空间本身成为叙述的重点,并实现对空间性的强调:一方面利用视觉心理学的“图底原则”,反转了作为前景的人和作为背景的空间之间的图底关系,将空间置于叙述的前景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在房屋、农田、广场和博物馆这些微观空间的转换组织叙事,推动了叙事的发展;最终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节目中空间的意义构成节目本身的意义。
节目通过对空间的标记,完成对乡村空间的描绘。在第一季中,节目组所选择的空间以散点的方式存在和并置,展现空间内所发生的碎片化事件。这些空间看似零散,甚至相互排斥和遮蔽,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但节目通过主持人的行走路线,勾勒出行动轨迹,将这些零散的空间串联起来,并为它们构序:从东南到西北,从房屋到田野,从广场到博物馆……当两个距离很远的乡村缺乏原本关系时,节目除了借用蒙太奇手法实现两个空间的不断切换以外,还通过身处两个不同乡村的主持人的视频连线,让乡村间发生关联,在空间并置中强化主题。当单一乡村中两个不同的空间缺乏原初的关联时,主持人的行动、空间的转换和叙事的推进都需要动力,而“走,我们去那边看看”等主持人的话语则成为叙事引擎,这些祈使句是对碎片化的事件和零散性的空间的连缀与缝合。最终,空间在节目中被选择、布局和描绘。
节目对乡村空间的整体编织由“主题—并置”的叙事模式来完成。“主题—并置”叙事模式是一种空间叙事,主持人每到一处场景,便在某个空间中完成某个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并不构成“叙事性联系”,且众多事件中“并没有哪一个是中心事件,也不存在什么全剧的高潮”。节目是由众多“子叙事”所构建的“主题—并置”叙事,每一集是一个单独的“子叙事”,和其他“子叙事”(集)并置;而在每一集内部又由两条叙事线构成,这两条单独的“子叙事”又并置;从而使“不仅整个文本是由‘子故事’构成的,而且其中的‘子故事’也由更小的‘子故事’构成”。但从整体而言,这些看似独立的“子叙事”,由统一而明确的“乡村振兴”主题作为“粘合剂”统合起来,形成一个叙事的层级结构,完成空间叙事,从而消弭碎片化,构成系统性的整体。
二、“家”的呈现:《山水间的家》对空间的表征
节目是对“家”的呈现。节目通过对空间的编织,形成文学绘图,其借助后者将“家”具体化为家庭、家乡和国家,并通过“目光的停顿”实现空间向地方的转化。空间在节目中完成了表征,成为具体可知、亲切可感的“家”。
1.节目借助文学绘图将“家”具体化。节目名称中的“家”是一个符号,其单一的能指却指向多重所指:既是微观层面的“家庭”,又是中观层面的“家乡”,同时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由于“家”的所指都是抽象的,它们必须通过具体化的空间来呈现,因而节目通过对空间的标记和编织,将不同的空间纳入作为整体的“绘图”之中,空间构成整体,并在整体中获得意义。
首先,通过影像元素呈现厨房、卧室和院子等空间,并通过空间叙事将这些零散的空间连缀起来,构成作为整体的“房屋”,用具体的“房屋”表征抽象的“家庭”。在探访浙江省杭州市东梓关村这一期节目中,航拍镜头展示了农民住上了崭新的回迁房。在探访安徽省西递村时,房屋里的客厅成为展现家庭的重要空间,村民家的客厅摆设着充满传统文化韵味的老式合欢桌,意味着“团圆美满”的美好祈愿。每一期都会展示主持人暂住的卧室,卧室内空调、电视、网络一应俱全,卫浴设施干净整洁。同样,厨房作为展现家庭重要的空间,每一期节目中主持人都会和村民共同完成一桌美食,在一碗一筷之间,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农民生活的富足。
其次,节目通过镜头语言复现农田、河流和道路等空间,并通过空间转场将这些分散的空间串联起来,描绘作为整体的“家乡”,用具体的“田野”表征抽象的“家乡”。主持人走进重庆市璧山区将军村的田间地头,被田地里以稻草为材料的《今年夏天》《迷宫寻宝》《七塘打雷了》等艺术作品所吸引,不禁感慨现代艺术气息也能和乡村结合得天衣无缝,成为艺术乡建的典范。
最后,节目运用航拍技术展现地图、博物馆等空间,通过并置将分散的空间勾连起来,构建作为整体的“国家”,用具体的“地图”表现抽象的“国家”。通过层层嵌套,零散空间实现整体化的呈现,家庭构成了空间的基底,家乡形成了空间的中介,而国家组成了空间的框架。空间叙事为“家”赋予形式,形塑了空间结构,拾掇具体的、细微的空间,将它们缝合在一起,并嵌入到“文学地图”中,抽象而宏观的空间得以显影,通过具体的空间达成可知可感,“家”由此具有美国建筑学家凯文·林奇所谓的“可读性”。
2.节目通过文学绘图将“家”地方化。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区分了“空间”和“地方”两个概念:空间是开放的、危险的,地方是稳定的、安全的;空间和地方虽相互关联,但地方相对于空间而言,更具有情感性。空间向地方的转换有两个条件,一则有赖于地方将自身同其所属的空间区分开来,让其自身具有更强烈的意义感和情感,其核心是人与“这段空间之间建立了联系”;二则“地方”是任何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稳定的物体,正是人的目光在空间中的停顿制造了人与空间建立联系的契机,停顿的目光为后者赋予意义,而停顿本身也被赋予意义,从而将空间转换为地方。
为了在桔瓣式的空间中完成空间叙事,节目由央视主持人、明星和文化学者组成的山水小分队在探访不同空间的过程中让空间转换为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成为观众可亲近的地方,并与之产生联系。首先,主持人通过和村民一同在农田中插秧、在博物馆中游览、在农家小院里吃饭等,不停地制造各种空间中的停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占用了空间,并通过视听语言让主持人的凝视和观众的凝视合二为一,构建观众和空间之间的凝视关系,观众的目光在这些空间中停顿。其次,节目中停顿空间的意义赋予是三位主持人共同完成的:央视主持人串联不同的空间,明星利用自身流量吸引观众,而文化学者则通过讲述空间的历史故事、诗词和习俗来赋予空间意义、时间以及情感。在走进河北省安格庄村时,当他们目之所及“太行巍巍,波光粼粼”的自然美景,撒贝宁感叹:“这就是《千里江山图》。”在探访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时,文化学者杨雨和朱广权分别用“说是清溪没有溪,田睦道上草萋萋,山边大树迎风啸,村外机车逐鸟啼”和“清溪村里清溪流,田成道上绿油油,山乡巨变第一村,欢迎大家来旅游”两首诗歌,作为清溪村践行绿水青山,走上了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前后乡村发生巨变的对比。
三、“家”的召唤:《山水间的家》对空间的征用
总台通过节目的传播完成了对观众“家”的召唤。节目通过征用空间,将其塑造为存在空间,进而建构个体的处所意识,消除空间迷惑感;在此基础上,存在空间询唤主体意识,将个人询唤为建设家庭、家乡和国家的主体。
罗伯特·塔利在论述文学绘图的功能时,认为文学绘图通过向读者呈现关于地方的描绘,使他们进入某种想象的空间,亦或称之为存在空间,并向他们提供各种参照点,使读者产生处所意识,促使他们走出但丁的“暗黑森林”的路线图,从而消除空间迷惑感,据此可以熟悉并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节目中征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把空间和事件被赋予时空秩序,建立方位感和时间感,最终构建“存在空间”。“家”是存在空间中最原初和最核心的要素,因为“不管对什么人来说,‘家’这个词就是他个人世界中心的直接体现……建立作为个人世界中心的‘家’的观念,可追溯到幼儿期,最初的观念是把家庭与住宅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要从这个‘世界’走出去,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节目中,“家”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存在空间:它是具体的空间,也是抽象的概念,节目通过影像手段和符号语言让两者相互缝合,构成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所言的“真实并想象的空间”。
“家”的这一双重属性使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节目所进行的空间叙事与文学绘图都是一种“表述”,叙述就是绘制,它绘制了作为整体的“家”的“地图”。整体性的“地图”不仅强调了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将个体纳入空间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激发了个体的“脑海图景”,强化了个体与空间之间的联系性。由此,节目构建起观众的处所意识,消除观众的“无地感”和“非家感”,最终克服卢卡奇所谓的“超验的无家可归”,“家”成为归属,也成为整个世界的参照点。
由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可知,作为意识形态的空间能够实现对“想象关系”的生产。换言之,空间能塑造个体同社会环境之间的想象关系。节目征用、创造和呈现众多笼统又具体的空间符号,其中“风景”和“河流”是节目中出镜率最高的两类空间符号。
“风景”是笼统的空间符号,镜头多次通过航拍等方式展示乡村的优美风景,包括无垠的田野、连绵的群山、挺拔的树木。当自然被审美眼光和镜头语言转化为风景,自然由此被社会化和情感化。反之,社会化和情感化的风景能对个体施加微妙的影响,引发情感的奔涌和意义的生成。艺术理论家W.J.T.米切尔“要把‘风景’从名词变成动词,它提出,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
“河流”是具体的空间符号,河流是一个具体的空间,也是乡村空间的边界,更是如画风景的重要元素。受众在接受访谈时说到,“每次看到小桥流水的诗意画面,都能唤醒我对故乡的记忆和怀恋,从而激发起我的‘恋地情结’”。每个人的故乡都可能有一条大河,它是家乡的表征,亦是国家的能指。这两类空间符号在节目的反复使用能够唤醒个体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意识,塑造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在个体的处所意识之上激发其主体意识,将个体询唤为家庭、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者。
四、结语
空间是节目中的重要元素,节目采用“主题—并置”叙事模式,完成空间叙事,构建桔瓣式的空间形式。节目中,主持人对空间的进入与勘探、标记与编织,绘制整体性的“文学绘图”,零散空间实现整体化的呈现,通过层层嵌套让“家”被具体化为家庭、家乡和国家,家庭构成了空间的基底,家乡形成了空间的中介,而国家组成了空间的框架,并通过“目光的停顿”将“家”情感化。最终,“家”作为存在空间构建个体的处所意识,进而激发其主体意识,将个体询唤为家庭、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者。
(作者罗奕系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教授、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郭昭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本文系厦门理工学院高层次人才社科类项目“共同体视角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图景及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YSK24008R)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