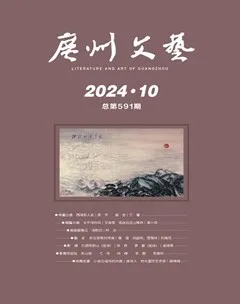“南北文学观”:一种认识装置的形成与反思
2024-10-21林峥 李静
李 静:林峥师姐好,很开心与你一起参加《广州文艺》的“南北对谈”。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受了学术训练,师姐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中山大学任教,而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比起你穿越南北的经验,我的工作生活都在北方,如此看来这确实是场“南北对谈”,很期待我们之间的“视差之见”。具体到近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南方”“新东北”“地方性”确属热门话题,对此已有诸多精彩发挥。我们的谈话,或许可以不再重复此前常见的论点,不妨把焦点放在“认识论”与“学术史”的层面,做出一些更具前提性的追问。比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南与北”或“地方性”这样一种认识装置是如何生成的?为何这类认识装置会成为“一时之选”?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南北之分由来已久,而根据方维规老师的梳理,文学史编纂中的“南北文学观”模式可以追溯至丹纳的“环境论”,并经由日本汉学家的文学史书写影响了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参见方维规《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南北文学观”的缘起与回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这样一种从“地理与文化”出发的实证主义话语模式,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史观与文学观。因此,如今看来南北二分的文学观念看似保守刻板,却在其起源时刻充满突破性。不知你能否从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角度,为如今的南北文学观继续增添某些历史脉络?如今我们为何继续调动“南北”这样的认识装置呢,其对话对象、实际作用与突破性何在?
林 峥:谢谢李静师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曾有同行评价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北上得到学术训练,又回到南方,兼得南北,此前我还未曾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确实有趣。南北气质的不同其来有自。我记得顾炎武对于南北学者之病的评价,说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即点出南北治学风格的不同,虽然笔无藏锋,倒也切中要害。在现代文学上,“京海之争”更是奠定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格局,鲁迅那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比之顾炎武,辛辣过之。当然,“京派”与“海派”的争论,最初由沈从文发起。沈批评一班“玩票白相文学作家”“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南北的趣味分野确实存在,北京更受新文化人的青睐,比如徐志摩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屡劝她从沪来京,说:“北京实在是比上海有意思得多,你何妨来玩玩。我到此不满一月,渐觉五官美通,内心舒泰;上海只是销蚀筋骨,一无好处。”包括谈到金岳霖等友人看到陆的画,都为之有才华却在上海浪费了感到可惜:“他们总以为在上海是极糟。”而上海的文人除了作为“海派”应战的现代派以外,也包括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创造社诸人,以及后来发展成为左翼作家的群体,他们与上海为何会相互选择、双向奔赴,都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其实民国的“南方”除了上海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城市——广州。广东自近代以来屡得风气之先,是革新、革命的象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诸人都曾经为此怀着极大的憧憬奔赴广州。到了今天,“南”与“北”的界限进一步往外延展,比如“北”从民国时期的北京到了东北,“南”从上海到了两广、海南、香港、澳门甚至南洋等。我觉得也有一个从“中心”到“边缘”视角的拓展。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代表意义都远大于一个城市,北京是帝都、首都,更多代表中国,上海则更多象征着全球、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超越北京、上海,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地区,是有价值的。我知道目前对于“新东北”“新南方”的概念,学界尚有争议,但我还是很肯定它作为一个认知装置,有助于我们打开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观察视界。
李 静:从你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南”与“北”的划分真是一个相对化的、从具体历史情景中产生的认知装置。顺着你的时间脉络,我还可以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再补充几句。“新南方写作”特别强调方言、民俗等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异质性,认为其中蕴藏着突破均质僵化的写作秩序的能动力量。但若返回当代文学的创生阶段,创造带有普遍性、真理性、高度透明化的人民文艺才是终极目的,地方性与方言土语是需要被批判性地吸纳其中的。换言之,“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在新与旧、都市与乡村、现代与民间、民族与阶级等关系模式中,文化的地方性不可能获得建立自主性的理论根据”(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30页)。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并不突出地方性,而是要创造“文化同一性”,亦即一种从延安文艺经验出发的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文艺。其中,“北方”较之“南方”肯定是处于中心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化热和寻根文学的影响下,“文化的地方性”获得自主性,严家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便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包括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等多种著作。近年,青年学者张永新也关注类似问题,尝试分析赵树理评价史中“地方色彩的发明”。他指出80年代以降大众化与民族化诉求边缘化之后,才导致地方性视角的凸显(参见张永新《“地方色彩”如何“发明”:1940—1980年代赵树理评价史中的地方性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因此,在地方性视角的淡出与凸显背后,有大历史存焉。不知对于如今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热潮,你如何理解其成因,与全球化语境有关吗?据我所知,你也是新一代学者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位,不知在你的经验中,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又应当如何理解?
林 峥:不敢当,我比起真正在海外受到成体系训练的学者,还差得很远,只能就我的一点浅见谈谈。我同意你的观点,“北方”往往更多象征着正统、宏大叙事、自上而下的整齐划一性,而“南方”或者说“地方”其实是隐隐带有一种与之相颉颃的,自下而上、非主流的多元异质性。其实“地方化”(localization)本来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相对立的,全球化即意味着一种同化、泯灭一切地方差异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过程所伴随的同质化、去地方化的力量,不断消解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学者们对此有所反思,提出一种“全球地方”(glocalization)的理论,即质疑单一、同质的全球化和现代性,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持和凸显地方特色。如此,地方(local)与全球(global)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我觉得除了“全球地方”的理论之外,“全球南方”也是一个相关的、带有爆破性和能动性的概念,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南方”带有一种革命性,去挑战和突破原本以西方或者说北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趋势也是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契合的。这些理论思考也贯穿我近期对于珠三角城中村文化的研究中。所以“地方”或者说“南方”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
李 静:“批判性的理论视野”,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性。大家在言说“南”与“北”时,除了地理的、实体的、历史化的南北,更指向背后的文化观念与感情结构,对此需要综合考量。还是说回全球化与国际化,“全球地方”“全球南方”的理论视野很重要,而其具体实践方式也非常关键。比如说,我注意到围绕“新东北”“新南方”的讨论有着国内外学者的合力,可以说是跨越文化语境的“地方性”生产过程。比如王德威教授主编的《东北读本》《南洋读本》,以及此前的《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等多部作品,与国内学者形成对话。不知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学术生产方式?你认为国内外学者之间关于“新南方”“新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探讨有什么差异与共性吗?在进行跨文化学术交流时,你觉得不同学术语境中关于“地方”的理解有哪些不同呢?
林 峥:确实,就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新东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很有意思,“东北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由一群东北籍的作家和学者合力打造的。其中主要是80后的作家、评论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贡献了作品,刘岩、黄平等人将之提炼命名,他们共享20世纪90年代父辈下岗的晦涩沉痛的青春记忆,实际上是在作品内外共同完成了一种黄平所谓的东北子一辈为父一辈赎回被夺去的尊严。后来祖籍东北的北美学者王德威、宋伟杰教授等也加入进来,主编《东北读本》,这背后有一种深切的家国情怀,而且也拓展了“新东北”的边界,就我所知,《东北读本》的视野恢宏,贯通了近代、现代和当代。当然,对于“新东北”与“新南方”的界定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我了解到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南方”的命名和阐释就多有分歧,海外学者对于“新南方”之“南”到底指向哪里有异议,认为最初提出的“新南方”概念其实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若合符契,提出应当关注“南方”之“南”,比如,是否该涵括中国台湾、南洋,由此可以看到,学理的背后其实也存在不同政治视域的认知差异。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互动对话、哪怕是分歧争议都是有意义的,如果真能在学理的层面各自辩驳,有助于形成一个生机勃勃、往来流动的跨文化学界交流氛围,能有效生产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议题。
李 静:“不同政治视域的认知差异”,我觉得这个概括很精辟,往大一点说,如何言说南与北,关涉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文化这一重大问题。南北文化的差异当然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中的基础问题,比如许纪霖教授就曾召集“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学术研讨会,我们很需要将跨学科、长时段的研究纳入讨论视野。这里想说的是,长期以来一说到“南北”,固定的地域想象便浮现出来,比方说,北方文化崇尚实学、风格质朴,而南方文化飘逸恣肆、充满想象力。正如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里写道,“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而“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不外乎“优点相师”,即北人南相或南人北相。如今一谈“新东北”,人们会自动联系到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而一谈及“新南方”,就会强调其异质性与想象力。那么在你看来,这是一种过于“自动化”的刻板印象,还是研究地理与文学关联的必要途径?据我所知,你正在开展的研究也会涉及对广东城中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研究,那么你觉得地域文化特征会帮助你打开更多思考维度,还是会造成某种“前理解”,进而限制了研究的展开?能否结合你的具体研究谈谈呢?
林 峥:我明白你这个问题中隐含的批判和解构意味,我也完全同意南北之别不是那么固化的,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过就像我在最初谈到的,南北地域的气质性差异,也确实是存在的。我个人在“新东北”和“新南方”的热潮双峰并峙之前提交的国家社科项目,讨论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城市乌托邦想象及其得失,其中囊括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珠三角城中村两个个案。当时我的想法是,东三省的衰落与珠三角的崛起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体之两面,有点像美国的“铁锈带”(Rust Belt)与“阳光带”(Sun Belt),我所要讨论的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工人阶级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打工者(农民工)也形成某种呼应。那时候,“新东北”已蔚然成风,“新南方”尚方兴未艾,我觉得有些东北的前研究对于我更深地理解文本颇有启发,同时也让我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区别于前研究,做出我自己的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个人的想法是,目前对于“新东北”和“新南方”的讨论主要还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我想以城市、空间为主体入手,打破文学的边界,探索一种出入于文学、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方法,当然,这样难度也很大,因此我目前最先写就的,是珠三角城中村的部分,主要是从五条人乐队的个案切入讨论,东北的研究珠玉在前,还要再好好积累探索。
李 静:或许在各个“地方”带来的差异性图景中,才能够更好地定位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新意。前面我们对“南北文学观”追根溯源,接下来我还想继续追问“地方/地方性”“地域”“区域”“文学地理”等一众概念的缘起,以及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差别。目前多数情况下,对这些概念的运用还显得比较随意,对于同一概念的理解也有可能言人人殊。比如在对比“区域”与“地域”时,刘川鄂教授指出前者偏于行政区域划分,后者则偏于文化传统的分界(参见刘川鄂:《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但相比之下,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区域》辑刊,在卷首语中指出其所使用的“区域”是指“一个体现着混杂、交往、跨界和多重认同的空间概念”,是一种“跨体系社会”。这显然超越了行政区域的概念,用前面的话讲,把“区域”视为批判性的理论视野。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些概念的使用,对这些概念的追根溯源是否必要?对于“新××”的概念发明,又该如何看待?
林 峥:我个人认为,这些对概念的使用(比如“地方”“区域”等)和发明(比如“新××”)最终还是要落到阐释上,也就是概念的使用和发明是否真正对我们理解研究对象是行之有效的,而避免落入一种空疏浮泛的学术生产。近期对于“新东北”“新南方”的一些反思和批评的声音,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总体来说,我还是支持和赞成这一波“新+地方”的热潮。尤其是“新东北”,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时我的触动,很久没有在年青一辈的当代作家笔下看到这么打动我的文字了!而在读黄平的论文时,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力透纸背的深情。新东北作家的创作确实折射了某种历史与现实的合一,能引起当代读者的广泛共鸣,作品本身是立得住的,而评论家的助推力,又使得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浮出历史地表,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当然,也要警惕概念的泛滥,如果没有立得住的成体系的作家作品,没办法提炼出作家作品之间真正的内在共性,纯粹为了学术生产而制造概念,我觉得一时的繁华热闹都是过眼云烟,做学术还是要志在“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研究。
李 静:我的理解是对于当代文学经验,我们当然需要创造新概念去描述,乃至激发、催化某些创造的潜能。但也不容忽视,对于地方性讨论热潮,已有不少学者给出“冷思考”。地方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其中分寸不好拿捏。上面征引的刘川鄂教授的那篇文章中,便引用方维保教授的观点,指出当前省籍文学史的繁荣根源于地方主义情结与地方行政力量的规划,从而导致了对地域性的夸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或许由此而生?也有学者提示,切勿让地方文学沦为政绩展示。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地方性视角的正面价值应当如何发挥呢?
林 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其实现在这些“新+地方”背后既有学术生产的驱动,又有行政力量的介入,甚至也包括影视流量的利益等,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我还是那句话,良性互动我乐见其成,但也要警惕,尤其希望作家自身的创作最终不要过多被这些外在的利益牵扯,保守初心,继续写出真正能打动人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