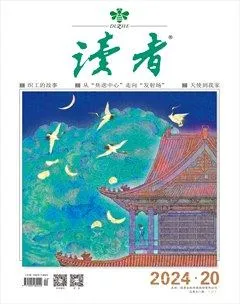那些年,射击都教了我什么
2024-10-14蒋在

你需要在30秒之内调整好呼吸,并扣动扳机,如果失败,必须放下你的枪。
这是第一天训练时,射击教练对我们说的话。
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难面对的不是脱靶,而是在30秒之内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的呼吸。那种压倒一切的寂静伴随着心跳声,还有身边的选手轻盈地扣动扳机后,将枪支前端架在海绵垫上的声音,都令我感到泄气。放下枪需要做好心理建设,因为它意味着刚刚做的——站好,举枪,呼吸,将脸贴在枪上,看瞄准镜,等等,这一套完备的动作的无效和失败。没有射出子弹就放下枪,约等于投降。
我也曾尝试不要放下枪,什么时候调整好呼吸,就什么时候射击。事实证明,持枪超过30秒,手腕就会出现难以觉察的抖动;靶纸上的落环甚至好几次都不在环数内。那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挫败和失望。
时至今日,回望这项运动,如果说它真的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我想就是,什么时候应该放下手里的枪,不管有多么地不舍,都必须放下,以便下一次更好地拿起。
在准备贵州省射击锦标赛时,我不得不暂时停下一切其他运动,全身心地准备比赛。那时候我每周还有网球课,但后来在训练中发现,挥拍这一动作在无形中影响了我手腕的稳定性,网球课不得不终止。
平时训练时,我们需要在场馆排队领枪。门边坐着一位男老师,负责登记姓名和取枪、还枪的时间,以及枪支的型号。仓库里有几把老式步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老式的峨眉EM45B型气步枪。它的装弹方式、重量和外形,都和比赛用枪不同。
我的训练服是深蓝色的。我们没有多余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的身形选择一套适合自己的服装,在比赛服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拿错。我的训练服上有一些褶皱,用白色和蓝色的线条装饰,穿上身后干净利索,像个即将登月的宇航员。
衣服闻起来很像装枪支的布袋,有着粗麻和尼龙布料浸进油里又晾晒干的味道。那或许是混合着汗味的一种既机械化又庄严的气息。就像训练馆里写着的“为荣誉而战”,总让看到的人为之热血沸腾,好像穿上那身衣服你就不再代表自己了一样。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也是缘于人类基因中对竞技的热爱,对拼搏与自豪感的向往。
过去人们相信奥运会的传承是因为人们将这种竞技的形式,当作一种“虚拟的战争”,人们在此种厮杀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不过是在“游戏”的范畴。然而,细读《荷马史诗》会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盛事的延续,是因为它是葬礼上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人类以竞技的方式向神展露人的力量,安抚逝者不安的灵魂,并通过比赛来重新凝聚人们因逝者离去而涣散的内心。
在所有运动中,我最喜欢射击。射击是一项孤独的,和自己竞技的运动。每一刻你都比上一刻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调整好站姿,那套重达五公斤的射击服让人在其中难以晃动,就像负重前行时腿上绑的沙袋,你会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拖着你下坠,仿佛要把你的双腿钉在地上。我必须穿着单薄的衬衣,才能与这套沉重的衣服产生某种联结。接着是肩膀,我要通过肩部的支撑和余热去感受和温暖那块冰冷的金属。
低下头,闭眼调整呼吸和心跳。装弹后,你要全身心地去感知这把枪的存在,甚至要尽力去想象它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个器官,你必须懂得如何运用它,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对其他运动员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体悟:乒乓球拍、羽毛球拍,或者剑,他们是不是也将手里的物体想象成自己身上的某一器官,感受到它的温度和跳动,才能更好地驾驭它?
枪弹射出的速度很快。但我在听到那声清脆的子弹穿过靶纸的声音后,才能松弛地放下枪。
比赛那天,我在一开始就没有调试好。我根据瞄准器或许有些朝左的偏差,微调了我的射击范围。结果,比赛正式开始的第一发子弹,我只打出了5环的成绩。当看到这个数字时,我就知道,比赛已经到此结束。我只感受到在空旷的射击场里,每个位置都站着一个正在瞄准的运动员,偌大的场馆里几乎没有嘈杂的说话声,只有不停地放入铅弹、扣动扳机,以及靶纸被打穿的声音。
我感受到比赛的残酷。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那些数字磨灭。最后那场比赛,20发子弹我只打出175环的成绩。还没有等成绩完全公布,我就离开了比赛场所。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成绩在省里根本排不上名次。
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起气步枪,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梦想就此破灭。之后的日子,在每一次人生的抉择关头,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我都记得教练给我说的那句话:调整好你的呼吸,30秒之内,发射出那枚铅弹,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必须放下你的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自己能成就的事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早年的射击经历有没有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滋养,如果有的话,我想一定是学会在人生的长跑中,如何调整呼吸。
(彭慧慧摘自《文汇报》202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