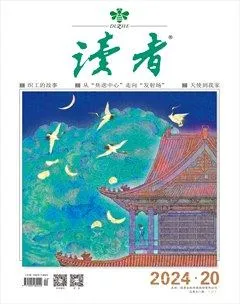从“焦虑中心”走向“发射场”
2024-10-14吴晨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全新阶段,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中国“从0到1”的高速发展时代,那么全新阶段则是“从1到100” 的多样性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单纯的“教育改变命运”“努力带来成果”的线性思维有可能已经不再适用。
在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数字时代的大转型中,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在本科以上学历的就业者中,创新与创意将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也将从体力工作者转变为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动手能力与专业素养并重;服务业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人际沟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从业基础。此外,团队协作、沟通技巧,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都将是未来劳动者的必备技能。
规模与多样性
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不但是第一个不再面临翻天覆地变化的世代,而且是一个从贫乏转向富足的世代。因此,他们会把这种富足当成理所当然。
但“70后”仍有的贫困记忆,继而引发的财富不安全感与当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勾兑,强化了“卷”是唯一出路的路径依赖。惯性加持的“卷”与“00后”新认知之间的冲突无法回避。
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需要审视规模与多样性这一组经常被忽略的关系,才能找到跨入全新发展阶段的门径。
怎么理解规模和多样性?讲一则“故事新编”:秦二世时,陈胜、吴广率领戍卒前往现在北京密云的渔阳。结果他们遭遇连日大雨,道路不通,被困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无法按时赶到目的地。陈胜、吴广面临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问题是,陈胜、吴广为什么会面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要从秦国向秦朝变化背后的规模倍增说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土面积成倍增加,但推行的仍是旧历。秦国规模小,地理和气候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律法中关于戍边的规定是合理的。秦王扫六合之后,帝国内部地理与气候的多样性倍增,因洪涝和其他极端天气而导致的误工、误期却完全不在执法者的考虑范围之内。陈胜、吴广起义的现代化解读是:国土规模增大,复杂程度剧增,导致原本在秦国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在幅员辽阔的秦帝国显得灵活度不足了。
规模和多样性是推动创新的关键概念。我们习惯于规模效应,却容易忽略规模扩大之后带来的多样性倍增,这就需要规则有灵活度,能够与时俱进。
理解多样性也有助于理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许多人会简单地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解为:要么完成跨越,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员;要么跨越失败,成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那般。用这种非黑即白、不进则退的方式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忽略了中国存在和面临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仍然显著;城镇化进程远没有结束,仍然有大量机会吸引乡村的年轻人进城;改革的红利远没有用尽。无论是鼓励更加便于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改革,为新一代进城人口建立更为公平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解决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都存在着巨大的政策发展空间。
其次,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与许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高科技发展领域,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前30年的追赶和进口替代与当下的创新发展有什么不同?答案是,当下须走出路径依赖。追赶阶段的发展有明确的对标点,目标确定:学习最佳经验,争取弯道超车。创新发展的阶段则不同,一种情况是,未来的目标不确定,你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另一种情况是,技术已经领先,这就需要学会引领,构建影响力,建立全球标准,让更多人追随。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我们放弃赶超的线性思维,拥抱“从1到100”发展过程所需要的开放心态和多样性思维。
再次,中国成长阶段的跨越是建立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上的,贸易、金融、资讯和人员的交流,使得中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许多跨越失败的国家。坚持全球化和开放给中国完成跨越带来的助力不可小觑。此外,全球化让我们可以吸取更多失败的教训,而不再需要自己去试错。
从1到100
上一代人在竞争和赶超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认为,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然而,他们忽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外部持续稳定的全球化与中国“从0到1”的高速发展。大潮托起努力的人,但这样的大潮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需要重新站在“1”上思考“1到100”的多样化发展路径。
担心被落下,希望高人一头。其背后既是对过去贫困生活的记忆犹新和缺乏安全感,也是对那种跨越式增长、爆炸式增长的怀念和渴望。两种预期都需要调整。
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全新发展阶段:发达、成熟、稳定和正常。但要达到发达、成熟、稳定和正常并不容易。更加富裕的发展阶段的一大特点是普通人的收入大幅提升,而直观影响则是人力成本的同步上升。发展不均衡的新兴市场或许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最好的基础设施、最便宜便利的服务,但这只可能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可能是最终的稳定形态。要么通过改革和发展变得更加富有,但也必须承担富有所带来的高人力成本;要么就得承受某种程度上持续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而这种状态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
发达,是指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发达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充满创新活力的市场体制;成熟,是指心态的成熟,不内卷,也不焦虑,当然,这也意味着慢条斯理、按部就班,成事的速度也相对缓慢;稳定,则意味着告别高速发展,不再有爆炸式增长的机会,当然也不再会有对财富安全、阶层坠落的担心;正常,则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金钱与金钱之外的意义的平衡、事业与理想的平衡。
从“1”出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成熟?答案是,不再将零和游戏的竞争放在第一位。第二,如何稳定?答案是,提升更多人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收入的大幅提升,也意味着我们要改变那种“既便宜又便利”的幻想。第三,如何正常?答案是,让普通人觉得即使按部就班也能活得不错,用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视角去审视社会的发展。
告别焦虑
从宏大叙事回到个人视角,我们也必须回答当下最棘手的问题:如何告别焦虑?
我们可以用一个四象限图来形容每个人的处境。象限的横轴左边是确定性,右边是不确定性;象限的纵轴向上是个人的控制力强,向下是个人的控制力弱。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期,大多数人处于第三象限,虽然个人的控制力并不强,但是发展具有高度的确定性。我们把这一象限称之为“乘客”。经济研究中也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状态——搭便车者,也就是你不需要为变革付出多少代价,却可以享受到变革的红利。换句话说,只要你付诸努力,就一定能收获成果。
当下普遍的焦虑源自我们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从横轴的左边滑向右边,发展的不确定性爆棚。在第四象限,发展不确定、个人的控制力又很弱,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焦虑中心”。许多人为了避免焦虑干脆躺平,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更大的努力在既有的领域做出成绩来,结果二者都不满意。
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向纵轴的上方努力,进入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用计划代替期待,分清楚哪些是可以掌控的,哪些是无法掌控的,然后抓住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多下功夫。这种改变的努力将帮助我们从第四象限上升到第一象限,虽然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能创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小环境,第一象限又被称为“发射场”。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回到第二象限这个舒适区——自己的掌控力强,外部发展的确定性也高,但那需要假以时日。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微小,集体行动并不会缺了我一个就做不成。其实,从“焦虑中心”走向“发射场”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有的时候把推动集体行为的临界值想象得过高,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想法要得到广泛传播,只需一部分人开始行动就可以了。
(宣 玮摘自《经济观察报》2024年8月12日,本刊节选,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