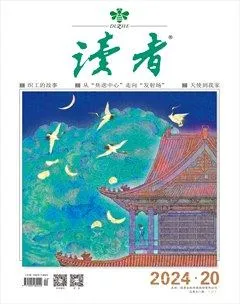我是怎样的钱理群
2024-10-14钱理群

读英国作家詹姆斯·罗斯-埃文斯《九十岁的一年》,看到“我已经摆脱了自我,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这句话,我眼一亮,心一动,觉得一语道破了老年人生的本质。这也是我的养老学思考和研究的核心。
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存在,一直是戴着面具的。从童年、少年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就戴上社会为你设计好的面具;到了青年、中年、老年阶段,你的职业、身份、地位就更是一个卸不下的面具,你能说什么、做什么,都有规定,绝不能越轨。内在的自我始终被遮蔽、压抑,不被承认,以至自己也不知晓。你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单位的管控,成了养老院里的一个普通居民,直到此刻,你才开始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让你本质性的存在显现出来,由单一自我变成多重自我,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这不仅是重新寻找、发现与坚守的生命过程,还是自我人性的重新调整。如今,我要把自己曾经有过、却阴差阳错没有实现(或没有充分实现)的个人兴趣、爱好、向往、自我设计,一一发掘出来,施展开来。
首先,这是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远比人们描述和想象中的“钱理群”要复杂得多的钱理群。人们所写的“我”,有许多反映了我的某些侧面,但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钱理群”,或者说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钱理群”,有自己主观融入的“钱理群”。而真实的钱理群是复杂的、多元的。
这是作为社会性、时代性、政治性存在的钱理群,既有与社会的周旋,又维护了自己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还具有冷静、克制,以及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性。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站在平民立场,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却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属于鲁迅说的“真正的知识阶级”。
这是忧国、忧民、忧世界、忧人类、忧自己、忧自然、忧宇宙、忧过去、忧现在、忧未来的钱理群。越到晚年,我越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自己有关,时刻不忘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是坚持老年理想主义与老年现实主义的钱理群。人们称他为“当代堂吉诃德”,又说他有越来越浓8IfvRadsYoTNtmQmjslKDdNLkvpMWou0Aa0eNY8NiW0=重的“哈姆雷特气”。钱理群永远走在鲁迅的阴影下,执着地以思想家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自觉承担起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下中国,特别是年青一代精神资源的历史使命。
这是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中间物”定位的钱理群,因而会不断质疑、反省自我。
这是沉湎于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永远胡思乱想,又喜欢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胡说八道、畅怀大笑的钱理群。
这是自称“自然之子”的钱理群,本性上更接近大自然。只有在大自然中,我才感到自由、自在和自适。处在人群中,则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真正让我动心的,永远是那本真的大自然。
还有一个老顽童钱理群。中国有两个成语,最适用于人的晚年——返老还童与入土为安。但这又不是指简单地回到童年,其中有老年的阅历与智慧。把老年的智慧和童年的真诚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提升。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就是在任何时候,特别是重要转折点,都能保持与发扬儿童的天性,对未来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因此也就有了不竭的创造力。
这是具有艺术天性的钱理群。我经常关注千姿百态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阳光映照下所显示的线条、轮廓、色彩等形式的美。我就是鲁迅笔下的腊叶:“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
钱理群还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我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在上海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上得了奖而被电影厂看中,在《三毛流浪记》里扮演了“阔少爷”的角色;后来又加入少年儿童剧团,为刚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慰问演出。此后也一直参与表演,直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北大教授还在百年校庆组织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这样的表演习性也渗透到我的工作和思维中。我的课具有表演性,很有吸引力;我喜欢作大概括、大判断,带有某种夸张的成分,也因此被批评为不严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不失为一种特色,或优势。
或许,我可以这样坦然回答“我是谁”。这样的追问,从青少年开始,到老年临终,才能得到一个完整、可信的答案。
(严 明摘自《财新周刊》2024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