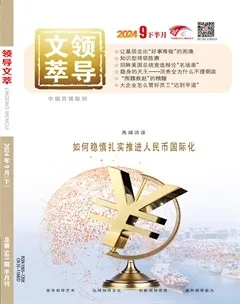为什么会从共治天下走向君主专制
2024-10-13许纪霖
“周秦之变”以后所建立的秦汉之制,是不是君主专制制度呢?
许多人会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一直到辛亥革命,持续了两千多年,其实这是一个大错觉。
民国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我们对传统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他写了一部《国史大纲》,提出中国的政治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汉唐两宋,是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后一段是元明清,才出现真正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历史上竟然还有过君主与人家分享天下?是合伙人制,还是委托管理?
共治是如何形成的
从西周开始,中国政治就是“家天下”,天下江山不是姓刘,就是姓赵,国家的所有权当然是天子的,不容他人来共享合伙。
不过,治理天下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在治理术上,儒家与法家不同,儒家是官治,法家是吏治。“官”与“吏”在中国的差别大了去了,就像西方政治中的“政客”与“官僚”不同一样。“官”有自己的执政理念,而“吏”只是官僚的工具。所以,儒家的官治需要博雅之学,有一套天理人道,提供合法性价值,而法家的吏治只是治理之术,按照上面交办的,完成职责面已。
秦始皇以为天底下只要皇帝一个人英明伟大就够了,他讨厌有想法的儒家士大夫,喜欢听话、好使唤的法家小吏,秦朝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国家法令当作教材,奉衙门小吏作为老师。
结果如何?秦朝二世因法家的苛政而亡!
汉朝皇帝一看,明白了,光有行政学那套治理术不够,还得有政治学,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汉武帝开始,转向重用儒家。所谓重用,乃是邀请儒家士大夫来共治天下。江山的所有权还是我的,但委托士大夫来管理。
汉武帝本人还是儒家、法家杂用,用董仲舒的儒学,也用桑弘羊的实干。但他设立的五经博士制度是一个大变化:汉初的人才有三教九流,只要能打天下的,都能够拜相入阁;独尊儒术之后,只有通晓经典的儒家士大夫,才有机会往上发展。于是,中国政治特色的文官政府就此诞生。公元前就建立理性的文官政府的,世界上就数中国最早。
什么是“文官政府”?从制度上来说,乃是将朝廷明确一分为二——内朝与外朝。外朝的头儿呢,就是宰相。宰相原来是皇帝的私臣,皇族内部的家事与天下之国事,公私不分,都得由宰相这个大管家来打理。
但汉武帝之后就不一样了,国事与家事分开了。宰相率领文武百官执掌外朝,独立于王室;重大决策由皇帝拍板,政府管理由宰相实施。皇权与相权的划分,有点像现代的企业管理,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宰相的权力很大,君主的命令必须经由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所以历史上常常有宰相拒绝副署、将皇帝诏书退回的事情发生。
门第与清议
汉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学学秦始皇,乾纲独断,一人说了算,多么过瘾啊!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为啥?除了治理天下要有专门技艺之外,最重要的是到了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又重新崛起。外朝的背后,有君主奈何不得的门阀势力支撑啊。
永嘉南渡以后的东晋,君主是什么?只是各路门阀的共主,做什么事都要先看看贵族们的脸色。比较起君主,宰相就要厉害多了!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王谢”,说的就是六朝最有名的两个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王与马,共天下”,王家竟然与司马皇帝共享天下啊!后来崛起的谢家,也十分了得,决定中原文明命运的淝水大战,就是“风流宰相”谢安一边下棋,一边打赢的。
到了唐代,不要看唐太宗李世民威风八面,玄武门之变中敢对自己的兄弟下毒手,但他在丞相魏徵的犯颜直谏面前,只能耐着性子,点头称是。原来李世民所属的关陇门阀,在门第上还不及魏徵背后的靠山——山东的世家大族。再说呢,李氏王朝又是鲜卑族出身,在汉族士大夫面前,天生有自卑感。一个讲究门第的贵族社会里,专制君主的戏份是有限的,你门第低,牛不起来啊。
现在问题来了,到了北宋,贵族势力被削平,皇帝是否可以从此一人说了算呢?也不行。门第衰落了,但另外一种力量,“清议”却兴起了。
所谓“清议”,就是士大夫的舆论。我以前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有双重权威,都代表天命。一重是政治权威,那是属于天之子皇帝的,这叫“政统”。“政统”之外,还有一重是“道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
这个“道统”不在皇帝这里,而掌握在儒家士大夫手中。用今天的商业语言,叫“拥有最终解释权”,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命,不能由皇帝自己说了算,必须由掌控天命解释权的士大夫通过舆论来评点。这就是清议。
宋明理学将天理与人心打通,给予士大夫极大的底气,用“道统”去抗衡“政统”。因此,宋代士大夫从王安石到司马光,从范仲淹到朱熹,个个都是品格刚正,敢怒敢言,很有一点道德骨气,另外一面呢,北宋的君主很少有昏君的,大都开明大度,对士大夫礼让三分。这要感谢宋太祖留下的好传统。宋太祖自己是行伍出身,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卷土重来,使了一招,“杯酒释兵权”。既然不用武将,那么只能重用文官,以文官制约武将。
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要提拔某个人,太祖不喜欢,拖着不批。赵普不高兴了,批评皇帝说:“赏罚分明是古往今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个人好恶来定夺?”太祖还是不理,走开了。赵普急了,追上去,不罢不休。太祖自知理亏,竟然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
太祖曾经为宋朝立下一条规矩:不杀大臣和言官。因此,宋代士大夫的气焰是比较嚣张的。宋朝的君臣,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大都符合儒家的仁君贤相标准。
共治的先天性缺陷
既然士大夫与君主共治这么好,那么,我们就真的回到宋代行不行?不要说回不去,即使回去了,这个共治也有天生的大缺陷,那是它的致命伤。
这就是共治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英国《大宪章》是中世纪英国贵族与君主签订的契约,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大宪章》后来成为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最早源头,它对贵族与君主的共治构成了硬约束。
但是,汉唐两宋的共治,却是软约束。为什么硬不起来?因为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不要以为君权与相权之间,是温良恭俭让,和谐共生。不,任何一个朝代,都充满了紧张和斗争。究竟谁说了算,要看士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意志较量。假如君主意志比较薄弱,掌控不了局面,那么宰相的权力就很大。倒过来,如果人君非常强势,即使有宰相,也接近君主专制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内朝和外朝的制度化是汉武帝确立的,但由于汉武帝性格太强势,相权根本不是皇权的对手。皇帝对丞相动不动就训斥谩骂,甚至处死。公孙弘之后的六位丞相里,有三位获罪自杀,两位下大牢死去,以至于有一位叫公孙贺的将军,前方与匈奴打仗非常勇敢,但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时,却吓得号啕大哭!
共治好则好矣,却是建立在人治的沙滩上。皇权与相权之间,不是现代的法权关系,而只是君臣的伦理关系,主动权始终在皇权一方。士大夫之于君主,只有伦理的软约束,缺少的正是法权的硬约束。政治是否开明,依然要拜托偶然性——老天爷给天下赏赐一个好皇帝。
这就是人治之下中国政治的悲哀,哪怕有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克服不了这个先天的制度性缺陷。而按照君主制的自身逻辑,只要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它总是要往独裁专制的不归路上发展。
(摘自《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